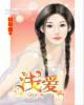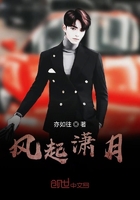第一次认识罗兰,是在一本叫做《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的书里。那本书中收了罗兰的一篇散文《寄给梦想》。还有一帧她本人中年时的照片,穿着连衣裙,似正在很认真严肃地说着什么。文章前面附有作者简介,说罗兰原名靳佩芬,河北省人,早年曾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学习,那段生活对她的性格、兴趣、生活以及写作都有很大影响,她的文章中的许多题材都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事情。出过多部散文集。
这篇《寄给梦想》却是写她的一位朋友,一位知识女性,为人妻为人母后,时时尽着主妇的职责,又时时感受着生活琐碎的纠缠与牵绊。于是日日向往着挣脱,向往着要在幽寂的深山里置一简朴小屋,与满山绿意和一涧泉水相伴,唯一床、一桌、一椅、一点简单的器物,然后做喜欢做的事,不问世事。然而细忖这又终归只能是梦想,因为现在是怎么也没空去的,将来老了,有空了,大约也便不敢去了。文章细腻生动,描摹现代都市中知识女性的心态很确切,很宽容,行文洗练清丽,读着便不由得去对号入座,从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淡化一点很多的无奈。
这次赴京参加“海峡两岸妇女读物与妇女形象研讨会”,报到那天就听说罗兰女士已经来了,她的跟她分离了三十几年的海峡这边的妹妹跟她在一起。晚饭桌上,我看见面容酷肖的一胖一瘦两位老太,都穿着黑毛衣,平底鞋,衣饰非常朴素。同来的台湾女作家们走过,都要很尊敬地称呼一声“罗兰老师”,那位瘦瘦的便微笑致意。实在看不出她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
以后的几天,她们姐妹始终形影不离。在会上,在外出参观时,罗兰有时会细心地为满头花发的妹妹整理衣角或是别在胸前的代表证,轻轻咕哝着说这才像个妹妹。清晨我们刚起床,就见罗兰姐妹已在宾馆的庭院里散步,有时两人会在一棵树前站下,端详着说上半天;集体活动时罗兰姐妹有时也避开大家,在一边慢慢地走,轻轻地说,她们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罗兰说小时候在家乡,家里她和妹妹最好,她当时在小学教音乐,也教过妹妹。望着她们总在一起的背影,有人感慨说我算明白什么叫分离和重逢了。
罗兰女士是温和的,沉静的,有时透着严肃。她在台湾主持“警察”广播台的“安全岛”节目有32年,每次自己编排好内容,大致是教育人们不要犯罪、生活要有安全感等,夹杂着放些音乐。
除星期天外,每天都有,每次55分钟。罗兰的语音很动人,如歌吟般,透着良好的音乐素养,她在电台主持节目的效果可以想见了。
但我以为,真正使罗兰女士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她本身作为文化工作者的强烈责任心和数十年坚持不懈为之做出的努力。大会开幕式上,她代表彼岸女作家发言,在充分肯定大陆、台湾妇女都很勤劳节俭、奋发向上后,她认为女性在争得自身权利的同时,也要多想想自己的责任,比如对社会的责任、教育孩子的责任等,搞写作的,更要以社会责任挂帅,不要以商业利益挂帅,要成为社会的清洁剂而不是污染源,她为大会提供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女作家的社会责任》,从一个方面强调了她的这一观点。当她旁征博引地反复论证着这一思想时,我们都清楚地感到了老太太为自己立下的为社会尽责的人生目标。
北京的会议使罗兰女士十分高兴,她在最后的联欢会上表演了天津话小品,台湾同行们吃惊地说,从没见过罗兰老师这样轻松活泼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