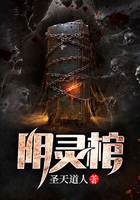星期五下午,街上就开始隐隐地上浮起一种兴奋的情绪,超市永远都没有间断的促销,广场上周末大家乐刚搭好浓艳的舞台,推着婴儿车悠闲的父母和背着大书包匆忙的初中生。我慢慢地走着,我想着您,您在那么荒凉那么偏僻的一个土坡中,在那么阴冷那么幽深、我无法看到的一个地方。夕阳绚丽地铺排在脚下的路面上,我抬眼看,西天边很美,听说天国是有这样的华丽的,您居住的有这个景致吗?还是只有苦苦的睡眠呢?
第二天,坐上了您曾经已很熟悉的那辆公交车,我身旁的孩子,是您从他小得托在手掌上那年起,一寸一寸,喂养成今天一个壮实的小小伙儿,成了一个渐谙世事的娃娃,他靠着窗,朝霞那么明媚地映着天真的小鼻头和清澈的眼睛,他只是一动不动。我不知道他都想了些什么,为何神色如此黯然?为何睫毛不停地抖动?我带着他这就去那里看您。
那时,您、我,还有娃娃,我觉得这是一个谁都不能缺少的、笑语翻飞的集体,我们曾在夜半惺松着眼睛,为哭闹的他冲香喷喷的奶粉,我依赖您那双粗糙有力的双手和丝毫也不犹豫的翻身而起,依赖您细心地把尿布洗烫得洁白柔软,和那炖得又嫩又甜的鸡蛋羹。
我的生活依赖您渐渐长满老年斑的手臂,和渐渐蹒跚的腿脚。
那些平静又快乐的生活啊,是缘于下班,远远地看见您和娃娃在五楼阳台上等待,一个脸儿黝黑苍老,一个脸儿娇嫩白皙,两张脸都乖乖地趴在深灰色的水泥窗台上,张望,那么高,你们看见了我,两张脸都绽出笑,这笑啊,瞬间让我掉进了一种叫做满足叫做感恩的巨大幸福之中。我轻捷得像一只灵巧的、吹着口哨的燕子,每上一个台阶,快乐就连续不断地攀升一点,陡然间忘掉了那还没有稳定下来的工作、没有晋升的职称,忘掉了包里其实只有很少的一点钱;当然,还缘于出门,您和他分别在我的左右,一个那么老却那么慈祥,一个那么小却那么活泼,此时,我没有任何缺憾!那时,我刚做了这个缠人娃娃的妈妈,我真傻,我只是为娃娃买回了鲜亮的鸡蛋和舒适的衣衫,我没有在意您的床板又硬又凉,没有在意您的饭碗里是不是昨天的剩饭。妈,我真是很莽撞。
我觉得,您不会在意的,不是吗?从我很小很小到现在,您不是从来都把我当做您手心里的宝吗?食品柜里不是从来都有一个角落,秘密地存放着香的面包、甜的桃子?像存放着一个幸福的心事。您还在贴身的衣袋里,摸出几张温热的钱,兴冲冲地为我买回那件印着玫瑰红色喇叭花的短衫,我也只是很无谓地笑笑,我忘了您已是一个需要照顾的花甲老人,我抑或也会这样认为,不着急,还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到那时,妈,您就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堂屋那个正中的圆椅上,别动,不必再摸索着洗净厨房的碗筷,不必再为了一袋面粉而精打细算,不必为了翻盖老屋而彻夜难眠,也不必担心外甥女工作的无着落和侄儿婚姻的不如意,这一切都会变得很好,您什么都不必担心,您只需看着我们像一群反哺的羔羊,只需享受到操劳后的宁静与安适。
但是妈,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到了,您不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只有在星期六的清晨,拎着一份伤感的心情,走向一个黄土堆,妈!
这是一段漫长又陌生的路,低垂的柳,高昂的杨、胡乱扭结的杂木和寂寞鸣叫的蝉。回家的路原本不是这样的,那一条路上印着您的脚印,花椒丛旁有您的气息,门口有您伸着脖子的暖暖张望,院子里有您转来转去的忙碌,厨房里有飘着香的烟雾。妈,您知道我是回来看您的,我们坐在北屋的小木凳上,您红肿的手裂着口子,我生气又心疼地拿起它们放在我的手中,您有些拘谨,缓缓地抽了回去。抽回去就急忙起身翻找出几块中秋的月饼或是过年的灶糖,我就努力使劲地吃,要不然难以补偿您又苦又长的惦念。告别的时候,我没有深情地轻轻地拥抱您越来越削瘦的肩头,我只顾收拾那一兜鲜美的韭菜、带土的大蒜,还有沉甸甸的红薯,只是很随意地挥挥手,我知道,您已是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但我想,会有机会的,今后。
今天,我和娃娃来看您来了,我们只是在您的坟头坐一坐,这也太仓促潦草了,您还不知道娃娃今年那非常出色的考试成绩,不知道他第一次军训磨练后,比以前黑了瘦了结实了,看吧,您一定既疼爱又欢喜;您也不知道今年我的身体为何如此虚弱、精神如此恍惚;还不知道您的孩子们是怎样哭天抢地地挽留您,妈!
可是啊,妈,我痛恨自己,就是千百次地看望,千百倍的愧疚,也与事无补,我只有在这个夏日的清晨、在这个寂寥的荒坡,静静地坐着,一语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