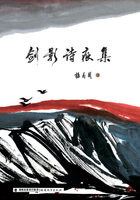壹
“小莽苍苍斋”是田家英的斋名,田家英之所以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小莽苍苍斋”,是因为对清末“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倾慕——谭嗣同的斋名为“莽苍苍斋”。田家英解释说,“莽苍苍”是博大宽阔、一览无际的意思。“小”者,以小见大,对立统一。关于田家英,《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已有翔实的介绍,这部书是一部回忆性的纪念文集,将逄先知先生的回忆文章的题目用来当了书名。由逄先知的这篇《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长文,对给毛泽东当了十八年秘书的田家英其人其事就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950年3月,逄先知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第一次见到田家英,从此就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并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直到1966年5月离开中南海。因此,他笔下的毛泽东和田家英,用胡乔木在该文《校读后记》中的话说,“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写得也很好。”“基本上采取客观叙述的体裁,间或夹入少许评论和抒情的文字,”写出了从1948年到1966年期间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之间的工作关系——
既表现了后者如何在前者的指导之下热情地、辛勤地工作,并在政治上迅速地成长,也表现了前者如何对后者的工作严格地要求,亲切地关注和真诚地信任,而在1959年特别是在1962年又如何由信任变为不信任……他们两人关系的恶化,没有任何私人的原因,完全是一幕政治(就这个词的高尚意义说)的悲剧。
当年正是由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才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正是从这部纪念文集里,我知道了田家英嗜好读书和收藏清人翰墨。在感慨田家英其人其事之余,更对他的“小莽苍苍斋”的收藏心向往之。
逄先知回忆说,田家英有逛旧书店的癖好,他们常常在晚饭之后去琉璃厂,每次都是抱着一捆书回来。有几次,毛泽东有事找田家英,卫士还把电话打到了琉璃厂的旧书店。田家英酷爱碑帖字画,收藏了上千件清代学者的墨迹,其所收作品之富之精,在个人收藏界堪称海内一大家。
不过,田家英最能体现其收藏价值的,恐怕还不是这些清人书法,而是毛泽东墨迹。譬如:1949年4月23日晚,解放军攻占了南京总统府,消息传到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毛泽东当即在宣纸信笺上用毛笔写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首诗,细心的田家英及时地保存了起来。此事毛泽东似乎忘记了,直到1963年田家英编辑《毛泽东诗词》时,将当年的笔迹交毛泽东核实,毛这才想了起来,“忘了,还有这一首。”
田家英居住的中南海永福堂正房西屋西北角靠墙码放着一排柜子,里面全是田家英收藏的清人字轴。柜前有一张长方形茶几,上面摆放着与茶几几乎同等大小的长方形蓝布匣。不管是秘书、勤务员或是家里的什么人,从来没有动过它。因为它的主人田家英对此物格外看重,也格外精心。偶有贵客来临,他才肯拿出展示一下。多数时间是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独自欣赏。这就是被主人称之为“小莽苍苍斋”收藏的“国宝”——毛泽东手迹。打开蓝布匣,是一册深蓝布面裱成的套封,上面用小楷写着“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下面署款“一九六四年三月家英装藏”。另一件用锦缎装裱的套封,上面题签《毛主席诗词手稿》,共十首,大部分诗词是人们熟知的。蓝布匣中保存最多的还是毛泽东书写的古代诗词,有李白、杜甫、杜牧、白居易、王昌龄、刘禹锡、陆游、李商隐、辛弃疾等人。毛泽东书写古诗词大都是默写,像《木兰词》、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这样的长诗,也是一挥而就,很少对照书籍。由于只是为了练字或是作为一种休息,毛泽东并不刻意追求准确,书写中常有掉字掉句的现象,有的长诗,像《长恨歌》,甚至没有写完。
田家英收集毛泽东的手迹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当面索要,再有就是从纸篓里捡。毛泽东练字有个习惯,凡是自己写得不满意的,随写随丢。有一次,田家英从纸篓里捡回毛泽东书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对夫人董边说:“这是纸篓里捡来的‘国宝’。”有许多次董边看见田家英在书桌前将攥成团的宣纸仔细展平,那是毛泽东随手记的日记,上面无非是“今日游泳”、“今日爬山”一类的话。董边不解,“这也有用?”田家英说:“凡是主席写的字都要收集,将来写历史这都是第一手材料,乔木收集的比我还多。”
田家英的女儿在《爱书爱字不爱名》一文里,更是详述了父亲爱书的癖好和收集清代文人学者和书画名家墨迹的爱好——田家英搜藏清人墨迹的用心,并非限于翰墨情趣,更在于撰写一部清代通史。
再如曾任周恩来兼职秘书的梅行回忆说:有五六年时间他和田家英来往很密,成了小莽苍苍斋的常客,常常随同田家英和陈秉忱一起跑书画文物点和旧书铺,常常提着或抱着一捆东西,走上七八十里路,回到小莽苍苍斋喝杯清茶。在梅行的眼里,田家英说到底只是一个书生,可以成为学者,是极难成为政治家的,他无法适应后来变化无常的政治局势。1963年春节前夕,田家英让梅行为他刻了一方“京兆书生”的闲章,闲章的边款梅行刻了田家英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写的一首诗: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从这些追述里,田家英的书生本色形象地凸现出来。
贰
《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三联书店2002年版)一书基本描述“小莽苍苍斋”的收藏风貌。该书从“小莽苍苍斋”的藏品中精选了一百余件明清、近代人物的诗文手稿、楹联、条幅、信札、印章、铭砚和善本书等文物,装帧讲究,文图并茂,用印在封底上的广告语说,“读者在清赏这些翰墨胜迹的同时,可从生动有趣的文章中,了解田家英收藏的故事、藏品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从中见出田家英的书生襟抱、历史关怀和风骨逸情。”
“小莽苍苍斋”所藏的清人翰墨,犹如一部中国近代历史的图卷,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和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些清人翰墨中留下了真实的痕迹。在田家英看来,文人书法不仅是难得的艺术,更能留下一些难得的史料,用古人的话说,画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书法的品位远在画之上。故田家英的收藏以书法见长,所藏清人翰墨的时间跨度从明末到民国初,人物约五百多位,收藏翰墨数量约有一千五百多件,主要包括中堂、条幅、楹联、横幅、册页、手卷、扇面、书简、铭墨和印章等。尤其是书简,在他收藏的二百余家近四百通清人书简中,多数为学者之间的往来函牍,有千言长信,有短篇札记,也有三言两语的名片,谈论的大半属于学术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时代特征明显。
“小莽苍苍斋”里的一幅谭嗣同书七言律诗扇面可以说是两个“莽苍苍斋”的“壁和”之作。1950年代是田家英大力搜集清人翰墨的高峰期,但他始终没能寻访到谭嗣同的墨迹,究其原因,一来谭嗣同死得悲壮,害怕株连的人销毁了与他有关的物品,二来谭嗣同就义时年仅三十三岁,留下的墨迹本来就少。寻访“莽苍苍斋”的墨迹,几乎成了“小莽苍苍斋”主人的一块心病。一个偶然的机遇,田家英得到了一幅谭嗣同的扇面,这幅扇面是谭嗣同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写给友人的奉和之作。从该书所附的扇面图影看,这是件精心运用书法艺术的写件,韵味十足,但名下没有印章,田家英在扇面左下角钤盖了“小莽苍苍斋”朱文篆书印,“这样,两个‘莽苍苍斋’斋主终于在同一件作品上留下了痕迹。此事似乎在田家英收藏生涯中占据着很大的分量……”从这件轶事中也能读出田家英的书生意气。“士可杀不可辱”这是田家英最后的遗言(这是他身边同志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这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慨然赴死的谭嗣同在气节上有着相通之处。
田家英的收藏轶事往往蕴涵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譬如该书所记述的康生将自己补校的明版《醒世恒言》一书送给田家英、陈伯达与田家英之间的“名联风波”、江青和她的《王老五》唱片、谷牧相赠“姊妹卷”、清初文字狱的一份记录和纸篓里捡来的“国宝”,等等。
关于陈伯达与田家英之间的“名联风波”有多种流传,但内容大同小异:1949年10月1日以后,陈伯达和田同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正、副主任。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比较信任和喜欢田,几乎每天晚上都找他,交办完工作后,总要聊一阵天,古往今来,山南海北。这使陈伯达很妒忌,常向田打听与主席谈天的内容,主席关注的动向,都读了哪些书?有一次在杭州,陈伯达坐着滑竿从南高峰下来,半途有人告诉他,主席正步行上山,陈立即从滑竿上跳下来,并打发轿夫到后山暂时躲避。凡此种种,都让禀性耿直的田反感。陈常卑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但田与黎澍闲谈时,常以little man代称陈,意思是“小人”。
1961年,田受毛泽东委托到杭州搞农村调查。杭州之行,田与逄先知在杭州书画社的内柜意外地发现了邓石如的草书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这副对联之前田已从20世纪30年代西泠印社出版的《金石家书画集》中看到过,当时还赞叹邓石如以善写篆隶行楷为长,想不到他的草书也写得这么好。田当即买下这副对联,兴奋得当晚请来林乎加、薛驹一同欣赏。据梅行、范用回忆,这副名联后来田还请毛泽东欣赏,毛主席也非常喜欢,特借挂在他的书房里很长时间。
不知是邓石如的名气大,还是因毛泽东喜欢这副作品,此事让以收碑帖见长的陈伯达知道了。他几次当面向田提出将名联转让给自己,都被田拒绝了。陈伯达碰了钉子,仍不死心,又托林乎加从中说合,此事闹了好一阵子。陈伯达讨了个没趣儿,竟然向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提出索要浙江省博物馆的另一副邓石如的草书联“开卷神游千载上,垂帘心在万山中”。林乎加直言相劝:“进了国家博物馆的东西怎么好再拿出来,这么做是要犯错误的。”陈伯达只好悻悻作罢。
田不满意陈伯达购买藏品的德行,遇有好东西,他常常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和人家讨价还价,其“激烈”程度连暗随的警卫都感到诧异。一次,在北京开中央会议,罗瑞卿走过来半开玩笑地对陈伯达、胡乔木和田说:“三位‘大秀才’在外,一言一行要注意符合自己的身份喽,旧货摊儿上买东西,不要为一毛、两毛和人家斤斤计较嘛。”田和胡相视一笑,他们都清楚罗的放矢之的,只不过是以玩笑的方式出之,算给陈伯达留了面子。
关于陈伯达的为人种种姑且不谈,只谈此副对联的来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就是《西泠印社旧事拾遗(1949—1962》(王佩智编著,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中的一节“当事人言”,大意是: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一位收藏家魏荣廷有一幅邓石如的狂草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因为邓石如书法中隶书、篆书多,草书不多,狂草就更少了,这一幅他一直珍藏在身边。当他听说西泠印社来上海收购时,他说其他人来收购他不卖,西泠印社来他不要钱。这副对联能归西泠印社是最好的归宿。西泠印社负责人在上海国际饭店请客答谢,他说:你请客我退席,东西也不给你们了。最后,还是魏先生买的单。这副对联就归了西泠印社。当时拿回杭州后,印社的女会计兼保管员就把此副对联收好放进了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在杭州写“九评”,休息的时候来西泠印社看字画、喝茶,是杭州市交际处一位姓赵的处长领着来的,还有几位工作人员,来了就到处翻。田家英在抽屉里翻到了这副对联,大喊一声,叫大家快来看,说:“这副对联我找了好几年了,今天终于看到这副对联。”大家评论了一番,都说是精品。临走时,田家英说这幅字他借去看看。中央来的人,毛主席的秘书,不能不借。这一借十天八天没消息。女会计哭了好几次,见人又见不到,大家又埋怨她。去找交际处赵处长,赵说,这些都是高级领导他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又去找市委分管书记、省委宣传部长,都说没有办法。最后找到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林说,人不是走了吗,你早给我说呀,人走了,你让我上北京啊。后来,康生又来西泠印社古书店,谈到田家英借走的这副对联,康说:田是应该送回来的。但就是没有拿回来。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邓石如法书选集》,其中第六十一幅就是这副对联,上面还加盖了田家英的印章,成了田的藏品。
在《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里还有几幅当代“名人”墨迹,譬如康生和陈伯达的书法,这两个人的书法其实也颇值得一观。康生对自己的字非常自负,譬如他说他就是用脚丫子拿笔写字也比郭沫若的字写得好。康生是否真如此说过已经无法验证,但从这轶事里能看出康生的自信和对郭沫若的蔑视。
20世纪50年代,康生曾送给田家英一套由他自己校补的明版《醒世恒言》,这种明版存世只有四部,且有两部流存日本,而留在国内的两部,其中一部原藏大连图书馆的今已不见,只有康生校补的这部衍庆堂刻本成为“小莽苍苍斋”的藏品。这部明刻为三十九卷本共二十册,在该书第一册卷尾,康生用他自成一体的“康体”书法补了一百一十八个字,因与书中的仿宋木刻体不匹配,再补卷四的两页缺页时,他以笔代刀写起了木刻仿宋字,这两页康生的补书和他为补页所作的说明原稿都影印在了《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再加上他送给田家英的另外两幅书法图影,展现了尖刻声称“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的“康公”的书法造诣,尤其那幅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写给田家英的草书“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令人过目难忘。
而陈伯达的一幅是他写给田家英夫人董边的录王国维文学小言轴,即论述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那三个必经阶段: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光阑珊处。陈伯达的这幅字轴,也非常可观。
田家英的收藏还得益于一位年长他二十余岁的“忘年交”陈秉忱,陈秉忱被喻为“小莽苍苍斋”的半个主人。陈秉忱的祖父是清代山东大儒陈介祺,幼承家学,擅金石书画,田家英称他“老丈”,田家英跑琉璃厂,有许多年,只带他一人,他虽是田家英的下属,但在收藏和鉴赏上,却是田家英的师傅,两人到琉璃厂的店铺里,田请老丈先进门,而陈坚持后进门,两人往往相让不下,以至多少年后,琉璃厂的师傅们打听“田公”的下落时,总好搭上一句:他的那位老秘书如何了?
“小莽苍苍斋”的收藏能达到如此规模和程度自然与田家英所处的地位有关,但田家英的收藏更是学者的收藏,是为研究历史和写一部客观的清代通史而收藏,如陈四益在该书《序言》中所说:
“小莽苍苍斋”主收藏这些东西的时候,中国人的商品意识很弱,收入普遍低下的时代,一般人无法进入文物收藏的行列;有清一代文人墨迹因为时代较近,尚不为人重视;再加上田家英所处地位,朋友们也乐观其成,所有这些条件,都助成了田家英藏品的相对集中。若在今天,这样的个人收藏恐怕虽非空前,也称绝后,是再难有的了。田家英生前曾说,这些藏品是人民的。他的家属尊重他的心愿,已将第一批一百多件藏品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先后编印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两大册,使需要研究与欣赏的人得以方便地使用,这样,也就不枉他当年苦心孤诣地寻觅了。
叁
在田家英的朋辈中,对邓石如书法评价不低的大有人在,譬如李锐在1962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故宫观书画,下午二点始归。饿着肚子看的……邓石如展览也是大开眼界。原来他之可贵在脱出千年来虞欧颜柳的影响,而从篆、分金石得法,自创一派。最好的还是隶书,行书似乎苍劲古朴有余而间架不足。其传派有包世臣、赵之谦、何绍基、沈寐叟、吴昌硕、康有为等。大概都在篆、分上受其影响……(《李锐日记》第二卷,119页)
李锐是田家英的好友,可以说在朋辈之中,用田的话说,他们是“道义之交”。李锐在“文革”结束复出后写过一篇《怀念田家英》,我觉得是在同辈人之中写得非常传神的一篇,譬如谈到田家英对毛泽东的看法和内心的忧郁:
家英当时有一个集中的想法,即主席应当摆脱日常事务,总结一些重大经验,专心于理论的著作,这样对后代更有意义。在庐山时,他跟我谈过一副对联,下联是“成书还待十年闲”,即指这个意思。他很惋惜主席志不在此。他早就同我谈过,编《毛泽东选集》时,主席常有厌于回顾旧作的情绪,而兴趣全在新的事物。
家英当年跟我谈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最后一条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应当说,这是一个党员对党的领袖最高的关怀。在山上开“神仙会”阶段,由于我的不谨慎,这三条意见同一位有老交情的同志谈了,开大会时被捅了出来。此事当时虽被“掩盖”过去,仍然影响到家英后来的处境,使我长期耿耿于怀。在山上时,我曾有过一种很悲观的情绪,向家英流露过。开完会,回到北京之后,他特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1960年到1961年,我在北大荒劳动。前期在一个村子里,同老乡三同;后期调到虎林西岗农场场部,场部的生活条件稍好一些。由于身体关系,1961年底调回北京。其后两年,我独自一人在京闲居。两年间,同家英见过三次面,都是电话约到市内某一新华书店碰面,然后带着大口罩,漫步街头,找到有单间的饭馆,继续过去那种长谈。第一次碰面,我才知道在北大荒调到场部,是他和别的几个关心我的同志作的安排。七十年代初作的杂诗中,曾记述此事:“打起精神学打场,忽传意外转西岗。长安故旧多关切,不忍其人葬大荒。”这次在饭馆谈了一个下午,谈到北大荒当时少见炊烟的暮色和农民的生活景况时,我很动了感情。家英也谈起庐山会议之后,他所受到的种种冷遇。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大运动了。分手前,一起哼成了下面这首诗:
闹市遮颜时,胡同犹可行。人间多雨露,海内有知音。冷眼观尘世,热肠向众生。炎凉今亦甚,把酒贱浮名。
1963年12月,我被派到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去当文化教员。离京之前,与家英话别,到后海岸边散步,该夜又到一个小酒店喝酒。当然,谈的主要还是当前大事。他正参加起草农村工作的后十条,说不久后,我会听到传达的。他谈此事,也是让我对形势放心之意。临分手时,走过景山很远了。对我的遭遇,这夜他特别感慨系之,又讲起吴季子来。夜半回到住处时,不能成寐,直到吟得下面一律,才勉强睡去。
客身不意复南迁,随遇而安别亦难。后海林阴同月步,鼓楼酒座候灯阑。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夜半宫西墙在望,不知再见又何年。
关于李锐在文章中说1961年底他从流放地回京及其后的两年,他同田见过三次面等等,这在李锐的日记中可以查到,不过当时的叙述和文字下掩盖的情绪是和后来的回忆截然不同的,譬如1962年7月14日(星期六)的日记中写道:
……与田打通电话,云极忙,文件与会议,也许实情,也许推脱,总之不能要求人家设身处地,要求人家也同我之“厚道”也。呜呼。这就是当代生活。只有手足之情经起了这种考验。……(《李锐日记》第二卷,94页)
再如1962年8月2日(星期四)日记中云:“……我之一生,没遇见过一个有影响的老师、领导者得些收获。朋友则无长期相处者,如田友只得其狂狷一面,与花腔之廿二年则是完全失败了的。”(《李锐日记》第二卷,100页)此处“田友”即指田家英,“花腔”是李锐已离婚的夫人范元甄——当年延安时代的美人之一。因其喜欢“唱高调”总是讲革命大道理,李锐在日记和与亲朋通信时常用“花腔”来代指。
至于李锐在文中说的1963年底被派到大别山流放之前和田家英的最后一面,在他的日记中也有叙述,并比较详细,那一天是1963年11月27日:“晚上看陶然亭客,绕什刹海漫步,烤肉季喝茅台四两,又再漫步,直径到西安门,再喝大曲二两。谭传千万不能写,以谭自居之误会,更置死地:仍在沾边,越来越严重,无人能解……”(《李锐日记》第二卷,237页)当时李锐正计划写《谭嗣同传》,田家英告诫他这万万不能写,以避免被人“误解”成“以谭自居,更置死地”的麻烦。
李锐在《怀念田家英》中写道: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害致死的情况。21日中央文革来人通知,两条罪名:同当时被批斗的办公厅负责同志关系不正常;一贯右倾。撤职交代,搬出中南海。并收走了全部文件。随即又听到办公厅大会上宣布了另一条罪状: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是指整理有关《海瑞罢官》的谈话时,他不赞成将彭德怀写进去。他这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的陷害。真想不到兢兢业业十八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
肆
田家英是自杀的。
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举行了追悼会,如此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一位友人曾告诉我,她曾和田家英的女儿谈到彼此的父亲——她们的父亲是“道义之交”——谈到田家英的自杀,田的女儿说:如果父亲不死,也许他就是第二个陈伯达。
友人是从美国回国探亲,借机会匆匆来到青岛寻找她青春岁月在青岛短暂的旧踪。我们谈到她的父辈的往事,谈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轶事,谈到田家英,当时我说从李锐等人的文章里,不难看出,田家英对康生很佩服。友人说,那一代人有着他们的局限,也有着他们自己掌握不了的命运,然后便说了田家英女儿的话。友人说:“她有这样的认识很不简单,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我做不到。”
相关书目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三联书店2002年版。
《李锐日记》(三卷本),李南央编,溪流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