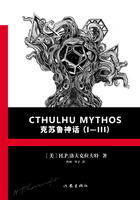雪红算了算,海南岛撞机事件发生的时候西村还穿着开裆裤呢。怎搞的,她的儿子?雪红有点糊涂,有点恍惚,要不是西村在身旁的话,她一定会以为他们被绑架了。以前那条登在广告上的大鲨鱼,以及眼前的这架飞机都让她觉得自己的脚好像没有踩在地上,身子有点飘,眼下自己是在看什么描写星球大战的好莱坞影片。
自然地,她开始担心了,不知道她的儿子搞出的会是怎样的一个怪物。这一来心神不定了,眼前的一切全都变得光怪陆离。当她抬起头来打量了一下这座已经显得破败的仓库以及从仓库的屋顶上延伸开来的蓝天和白云时,她突然想到要是把这个离北京郊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村落放到横贯了几千年的庄稼地上去浏览的时候,那不也就是一件所谓的装置艺术品吗。
11
鲁兵热情洋溢地和他们握了手。作为这次艺术展的主办人,鲁兵对远道而来的青年艺术家的父母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高然还算是沉得住气,和鲁兵寒暄了几句。雪红却尽量地不去把鲁兵打量。心里有气,不用说没有好感。其实鲁兵留着长发,外表也很前卫的,可是冤家路窄,在雪红看来,眼前这个曾经被她强迫西村去忘记的人好像只是这个仓库里的一件库存。不,他好像是从仓库旁边的庄稼地里突然间冒了出来,然后使了什么魔法,掠走了他们的西村。
“西村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艺术家。他这次的参展作品很受同行的赞赏。请过来吧!”
“你别费心了。我们自己随便看吧。你有那么多的客人……”
雪红谢绝了鲁兵的好意。她已经在打算怎么草草收场,早一点离开这么一个是非之地了。她考虑的下一步的行程除了故宫外,首推万里长城。
她看到西村有点不好意思。
“爸,妈,这是我不久前创作的……”
首先看到的是贴在墙上的作品说明,《莫斯科格勒保卫战》,好大的一个题目。只是没有摆放在仓库外面水泥地上的那架飞机,怎么去保卫呢。而且很小局的,映入眼帘的只是陈列在一张小桌子上的一个模具。
突然间雪红吃了一惊,随即她的脸红了。她看到那个模具的下端是一面城墙的片段,从那上面,十个充满了氢气的避孕套冉冉升起。是用十条细小的线索把那些避孕套固定在城墙上端的。
她当然看清了那些避孕套是日本产的,很可靠。
高然就不知所以然了,得不到任何提示,因此也没有相应的理解能力。这位被雪红指定必须努力用自己的地理历史知识来增加儿子知识面的父亲思索了一阵,才有些恍然大悟。他瞧了一下西村,好像是要确认什么似的,可是西村避开了他的目光。他就去看雪红。他从雪红的脸色中看出自己的妻子还没有理出头绪来,没有把事物的本质抓到手。他有些得意了。这回他领先了一步,发言权在他手里。
“让我们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疯狂轰炸莫斯科格勒的德国飞机吧。针对着像乌云一般黑压压的机群,斯大林伤透了脑筋……你知道斯大林最后想出的办法吗?他在莫斯科格勒的天空中升起了几百个巨大的气球……”
这一刻,那十个鼓胀的避孕套也不甘落后地排成了一排,努力去构筑一道严密的防线。
“不错,这个构思不错……”在把既紧张又腼腆的西村表扬了一句之后,高然又转向了雪红,“现在你懂得了吧,懂得了它的意思了吧?”
雪红不敢说不懂得,也不敢说懂得。
“不过这个细节还得靠你这个当医生的来解释了,”高然突然觉得自己仍然停留在表层,挖得不深,“你说这些小玩意儿是用来抵御什么的呢?”
雪红的脸更红了。
鲁兵又过来了。尽管他得接待很多客人,可是他一直在关注着西村一家子。他听西村说过了,他的父母亲不赞成西村搞装置艺术。这使他非常遗憾。他很希望能借这个机会来为西村接下来的艺术生涯去掉一些阻力。他已经隔着人群把他们一家子给仔细地观察了,并且看出了其实西村的父母亲是很懂得艺术的。
“不止是这个,西村还有一个呢,有一个更妙的,你们怎不去看呢……”
原来西村这一回还带来了一个新作,就是为此他比父母亲早来了北京一个星期。这一次是一个大作品,占据了仓库的一个显要的位置。因为大,西村只带来了一些事先在日本加工好的部件,能在当地凑合的东西他都尽量省略了。最后是组装,修葺。用文学的话说叫做串起来,然后再润色,做一些文字上的推敲。
在西村埋头苦干的时候,鲁兵去看了他两次,悄悄地。第一次鲁兵看到一堵巨大的红砖墙壁,墙壁上有两个挖好了的洞。第二次鲁兵看到那两个洞口有两个人,跟真的人差不多大。
鲁兵没有去干扰西村。不过他感觉到了从木制的框架上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气势,尤其是那两个人的表情挺打动他的。当时他无法把自己的感受说得很具体,他也没有去细细地琢磨。他当然不会像一个外行的人那样,只盯住一个局部就会有连篇的议论。
他认定西村的这个作品是一个杰作。艺术展完了之后,他打算把它带到海外去做巡回展出。这会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西村父母,以设法引起他们更大的关注。
西村却想打退堂鼓了。《莫斯科格勒保卫战》的成功超出了他的想象。效果比预期的要好。正因为如此,他有些担心,担心这部被他命名为《生命的横渡》的新作会对雪红他们产生更大的冲击力。见好就收,况且他自己也很害羞呢。可是鲁兵却极力推荐,连声说那作品太好了,必须一睹为快。单单是替西村着想,他都主张应该一鼓作气。
新作的前面的确围了一堆人。是有一种气派,也许是因为块头大的缘故吧,没办法一览无余。雪红和高然被站在前面的客人挡住了视线,只能从局部着手,透过人缝一点一点地啃。
一男一女的两个人分别被困在一堵砖墙里,无法动弹。不过他们的身子却尽量地前倾,两只手拼命地往前伸着,像是在探索着,求冀着。头是抬高的,眼睛前瞻,盯住非常遥远的前方,眼神徒劳地透露着一种企盼。
他们不由得对望了一眼。有点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一般。那两个人是谁呀,他们干吗要那样子地拼命挣扎。
观众慢慢地挪着。空间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画面上因此有了一种不易察觉到的动感。他们突然觉得那两个被困住的一男一女也互相对望了一下,像他们那样。只是那两个人被两堵砖墙卡住了,怎么也无法靠近。倒是他们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一点,尽量地缩短了一下他们之间的距离。
他们不由得踮起了脚跟来。这一下,看得更全了,几乎整个画面都被他们映入了眼中。这一来他们又有了一点像是在上浮的感觉,轻飘飘的。他们赶紧把踮起了的脚跟放下。可是那脚跟刚触到了地面,却又踮了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给托住了,身不由己。
原来是在作品的下方,有上下起伏的波涛。那波涛是假的,是道具,是画好了以后贴在锯成波涛形状的木板上头的。只不过西村制造了一个假象,一种视觉效果,让人看了会觉得自己是在随波逐流,飘向看不到尽头的地平线。
要是把那两堵墙换成救生圈就好了。不然的话,他们觉得太沉重了。救生圈帮助落水的人游向彼岸,而那两堵墙却像是两条锁链,把人给束缚。人在潮起潮落的大海中毫无希望地被淹没。
不知不觉中,他们把对方的手抓住了。他们看到画面上的两个人明明隔得很近,却无法携起手来。显然他们害怕他们变成了画面上的那两个人。现实当中的他们一直是患难与共的,相依为命。
最后他们站到了最前面的位置去了,去和整个画面相对着。这一下,他们吃了一惊。他们看到西村也站在画面当中。西村站在画面上的两个人拼命想游去的那个地方。其实西村站在画面的旁边,站在画面的一条延长线上。他们不知道那是一种意念,是装置艺术玩的把戏。刹那间他们懵了,和他们近在咫尺的西村原来是那样地遥不可及。
见到这情景,西村赶紧站到了他们面前来,把自己的作品挡在身后。西村的微笑在说爸、妈,我在这里呢。我在你们的身旁。西村显然是在说爸妈,从我的作品中走出来吧,回到现实当中。
可是雪红和高然仍然像刚才看着西村的作品那样子看着西村。看着,看着,雪红的眼睛湿润了。
“西村,你……这是你做的?……”
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而且雪红也不需要西村的回答。她难道会不知道这是谁做的,她只不过是想掩饰一下自己。她还不习惯在儿子面前这般情不自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