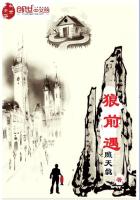我带着极度不快的心情,用耷拉着的上眼皮遮盖里面翻得高高地眼珠子,一万个不情愿的跟荷花坐在了同一条长板凳上,我看着她洗的较往日还算白净的脸,眼前浮现的却是那副鼻涕邋遢满脸汗泥的样子,早晨吃的那俩鸡蛋似乎想要变成小鸡从嗓子眼儿里扑腾着翅膀逃出来,一阵阵的燥痒。全部小孩儿落座之后,我大致扫了一眼,一排八个桌子,一共有六排,教室后墙前还空了一块地方,上面也挂着一块黑板,画满了向阳脑袋那么大的向日葵,上面赫然写了几个大字:祖国的花朵。杨大腚唇子跩着硕大的屁股晃着胸前两坨肉走上讲台,定睛看着台下,似笑非笑的说,同学们好。台下的同学们还没进入学生的状态,嘻嘻哈哈叽叽喳喳的无法形成整齐的回答,有的说,老师好,有的说好,有的嘴里含着鸡蛋或者地瓜瓤喷着碎屑不知道说啥。老师问过之后表示十分失望,纠正大家说,以后我问同学们好,你们要站起来说,老师好,听到了没?我们再试一遍,看看谁最会说。杨大腚唇子抬高声音扯着犹如鸡叫的嗓子大声喊道,同学们好!台下的小孩儿们歪歪斜斜的站起来一半,拖着长声儿参差不齐的喊道,老-师-好-!我虽然没吃东西也没叽叽喳喳,但鉴于对她的不满就是没有站起来,坐在椅子上歪着脑袋斜楞着眼看她,我不站起来也不让我旁边的荷花站起来,扽着她的红底白花小褂硬是把她刚刚抬起的屁股扯到座位上。嗯,很好,还是有很多同学没站起来,说的也不够整齐,我们再来一次,这次大家必须站起来,一块说老师好,都不要吃东西了,也不要讲话了,我看这次谁不站起来,就罚他到教室外面站着去。说完,杨大腚唇子拿黑板擦使劲拍拍讲桌,桌面升起大片白色粉尘轻舞飞扬,桌子发出啪啪啪的声音,伴着她剧烈的咳嗽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几个嘴里吃着东西的小孩儿停住咀嚼的嘴,又不敢直接吐出来,只好紧闭着嘴使劲儿往下咽,有几个噎得差点全部喷到课桌上,手忙脚乱的从小书包里找水。等到教室鸦雀无声,杨大腚唇子立刻切换一副面带笑容和蔼表情,眯着俩眼珠子扫视教室每一个角落,突然再次提高嗓门儿大声的说,同学们好!整个声音由于嗓门儿的过度提高已经从鸡叫变成了马吼驴嘶,大家被她这突然吊起的嗓门吓了一跳,麻利的站起来张开嘴喊,老~师~好~我看到大家都站起来了无奈的也跟着慢慢的站起,隐藏在人群中光张口不出声。
今天开始,我们在一起学习,我是你们的老师,以后都叫我杨老师。杨大腚唇子话音刚落,几个从娘胎里就会溜须拍马的小孩儿舔着脸的叫了起来,杨-老-师-。我不屑的瞅了一眼到底是哪几个孙子这么谄媚讨好,于是我在心里默默记住了他们的位置或者名字,而其中就有一个是大头向阳。这个大头儿子摇头晃脑的咧着大嘴,扯着洋腔儿拖着五米远七拐八拐的调调儿,两只眼睛眯成缝流着斜唌昂着头对着杨大腚唇子,那熊样儿恨不得让她抱在怀里吃那俩硕大的奶。那副忘我陶醉的样子,以至于他把“好”字拖到了最后,整个教室只剩他自己的声音回荡许久,大家哄然大笑,他也不觉得不好意思,慢悠悠的抬起袖子擦擦斜唌,挺挺单薄的腰杆,右胳膊压着左胳膊,笔直的端坐在桌子上目不斜视。
我看看自己身边的荷花,再看看大头身边的静静,好比人家手里有一根奶油雪糕,而我手里只有一根水果冰棍,我恨不得拿着荷花去换静静。偏偏我是一个想的比别人多,做得比别人少的小孩儿,而且很多想法转瞬即逝,没多大功夫已经不计前嫌的跟着我们的杨老师我的秀香姑姑和所有同学们一起学唱人生的第一首儿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要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在越来越整齐嘹亮的歌声中,我渐渐有了一种神圣庄严感,我要好好上学,好好学习,好好劳动,做一个为人民立功劳的好孩子。既然我已经忘却前嫌了,就不妨碍我搭理老师,她在教室中转来转的带着我们唱歌,我趁她走到我旁边时拉住她的胳膊问,姑姑,人民是啥?我这么一问,好多小孩儿也跟着问,啥是人民?人民是人吗?秀香姑姑被问的不耐烦,说,人民就是人,人就是人民。大家穷追不舍,那为啥不唱长大要为人立功劳?秀香姑姑无奈的顿了顿嗓子说,人民是为了唱着好听。
害羞如我者,一直到中午放学都没能够在课间和静静说一句话,她的大眼睛小嘴巴总是在我脑子里闪来闪去,而旁边的荷花,果然不出我所料不等中午放学袖子上已经沾满了鼻涕,而我偏偏坐在她的右边,她抹鼻涕的袖子刚好是右胳膊,擦完了鼻涕放到离我胳膊很近的地方还时不时的碰到我,我觉得浑身都被她那只胳膊给弄脏了,往右挪了好几次,我的右半边身子几乎要到了桌子边界外。这么坐着实在难受,我转变策略,心想不能老是我往外边挪,索性把她往左边推,起初推了几次她还乖乖就范,我对她的配合表现还算满意,但是后来就不行了,我怎么再继续推她她都憋着一股劲儿的抵抗着,整个人僵在桌子上不肯移动分毫。我看她赖在那里就是不动,已经有一半身子在桌子外,还有一半屁股在板凳外,我灵机一动稍微一起身,抹鼻子荷花顺势就趴到了地上来了个猪啃泥,秀香姑姑走过来把她扶起,没等她要张开嘴哭,先说,不哭不哭,我帮你打地,让它把你摔着了。荷花无辜的看看被秀香姑姑用脚跺的蹦起灰尘的地面,然后鼻子眼睛拧成一块的转头再看看我,我若无其事的迅速转身看向窗外,窗外有只麻雀刚好从窗台上停顿一下,靠窗而坐的一个李家小孩儿伸手去抓,麻雀不屑的拍拍翅膀腾空飞走。秀香姑姑安顿下荷花,走到我旁边说,你坐好了,要是不听话回去跟你奶奶说。她要跟奶奶说的话,我多少是恐惧的,但是她这么一说立刻再次燃起了我对她的不满,我还没跟奶奶说你让我跟她坐到一起呢,凭什么让我挨着抹鼻子花。
中午放学回家,堂哥已经在我的教室门口等着我们,我和堂弟等几个人跟着堂哥开始往家走。一边走,堂哥一边说,以后在学校里谁敢找事儿的你们就去找我,我们二年级教室就在旁边那个屋里,下午我领着你们认认门儿。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片湾,三五成群的各年级学生沿着湾边儿往家走,好多人脱了鞋子挽起裤腿趟着水,还有的干脆把鞋子装在书包中光脚在路上追逐打闹,太阳已经到了头顶上方,几只肚子鼓鼓的青蛙躲在水草底下一边乘凉一边看着我们,抹鼻子花跟着她上三年级的姐姐莲花走在我们前面,我不无自豪的跟堂哥说,老师让我和她坐一个桌,我还用板凳把她闪到地上去了呢。还没等哥哥夸奖我,只见莲花拉着荷花擦过鼻涕的手停住脚步转过身来。无所不能的堂哥,看到她姐姐莲花面露一丝怯色,拉着我的手就准备朝一旁走。离我们五六米远,个子高高的莲花,细胳膊细腿从肥大的袖子和裤腿中伸着,脚上一双与荷花平日里穿的相差无几的黑布鞋,留着一头茅草似的打着自然卷的干枯短发,双目常年圆瞪,眉毛天天上扬,微风吹过裹着她细长身子的褂子轻轻摇摆。她三步并两步的加快速度拖拉着面部表情半死不活的荷花走到我面前,站定,停顿半分钟看着我,我被她看得心里发毛,转脸看看堂哥,堂哥强撑着小地主的傲慢姿态看着她,她见我不看她,便也转而看堂哥,堂哥正欲开口,莲花指指我对堂哥说,以后他跟荷花同桌,咱们住前后邻的,你让他不要欺负我妹妹,也不要让别的小孩儿欺负我妹妹行吗?我听到这里,长舒一口气,莲花的指甲盖是出了名的锋利,已经把村里好几个小孩儿的脸抓破了,堂哥对她也敬畏三分也是难免的。堂哥见人家没有追究我把荷花摔到地上的事情,觉得是自己小地主日久天长积累的威名起了作用,刚刚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神气十足地说,行啊,以后在学校里谁敢欺负他们,谁敢欺负你,都跟我说就行。莲花听完后,表示满意的把圆瞪的双眼眯成一条缝抿着嘴冲堂哥和我笑,自始至终荷花那脸上没有半点表情,鼻涕已经比在教室里的时候多了一些,因为右手被牵着,不得不抬起左手拿袖子使劲儿的抹了两下随姐姐转身离去。
看着她姐妹俩远走后,堂哥下了命令,以后你们都不要再惹抹鼻子花了,她姐姐直接不好惹,还有跟她姐姐整天在一块玩的那好几个闺女,劲儿都很大,指甲盖子也很长,万一让她逮住了能撕烂你们的嘴。我说,为啥连你都害怕她啊?堂哥说,我不是害怕她,反正我不能惹她。
后来我们才弄明白,我们的小地主婆李家姑娘,经过与堂哥多次来往,自己在杨桥村已经混熟了好多小姑娘和她一起玩,而莲花就是其中一个领头的。我想到这层关系便立刻觉得堂哥不惹莲花是天经地义的,这么说起来都是自己人,甚至觉得跟荷花也是亲戚了。那时候我们说谁跟谁关系好坏,不用穿一条裤子或盖一个被窝来衡量,而是以谁跟谁有亲戚来判定,谁要是跟谁有亲戚是顾名思义血浓于水一致对外的关系。所以堂哥才会突然听到他的表弟贾海亮跟李海港一起玩之后立刻置李家姑娘于不顾的怒火中烧,所以贾海亮被堂哥抓个正着之后整个人都呆傻了,抹着眼泪往家走不晓得心里有多么难受。背叛亲戚,那是天理不容大逆不道的事情,即便是小小的孩童都坚信这个道理,那是伟大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连着血脉的信仰,那是缺衣短食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面所有人身后的一种生存寄托。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要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线,一转身,学校炸没了。清晨的阳光明媚,百草芬芳,绿油油的一湾秋水带些柔弱的微波拍打着长满了水草的泥岸,抚掌合奏,哗~啦~啦~啪~。浩浩荡荡的七八个孩子大摇大摆的走在去炸学校的路上,一派安宁祥和。贾杨李小学的正门是一个宽五米,高三米的生铁大门,站在我们的高度仰头看上去,一根根的黑铁柱子带着尖笔直的插到云彩里。每次我们去学校都早很多,于是滋生了若干在学校大门外空地上的各种娱乐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挑战这个铁栏杆大门,我们两个人几个人一组,抓住栏杆踩住横梁,费了劲的站到最上面一道横柱上去,然后用嘴咬住柱子顶部尖尖的铁片,那铁片厚约半公分,每一根都反射着可以将人穿透的犀利寒光,我们将它含在嘴里,低着头用牙小心翼翼地紧紧咬住那个生铁尖,然后撒开手伸展双臂做平衡状,看谁坚持的时间久谁就赢了。这种情况下,那些胆大的身轻如燕的占尽了上风,我只尝试过一次便败下阵来,站在上面的时候由于旁边的人还在攀爬,导致整个铁门晃晃悠悠无法站稳,持续几秒立刻退将下来。然而小地主缺从来不上去,每次站在门下抬头望着我们,一会儿训斥下这个,一会儿吆喝下那个,说大家动作不标准,爬得不够快,双手撒的不够开。后来证明小地主是正确的,明知道危险的事情他不会去做,但是可以指挥别人去做。老天作为每次攀爬铁门的第一名,终于在一次铁门剧烈晃动中把上嘴唇划破,作为我们每次战斗的英雄,他满嘴留着血坚强勇敢的慢慢从最高处爬下来,迎着阳光张着血盆大口,几道红色的血光从原本洁白但歪歪斜斜的牙上反射出来,面带痛苦却也不哭,跑到旁边的湾边捧起水来哗啦哗啦的涮嘴。自老天负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铁门望而生畏,任凭小地主再怎么怂恿都无人再爬。于是我们的更多游戏就从半空中转移到了地面上,学校门口的空地大约有五六个场院,每个场院聚集了不同年级的几拨人。每一拨人之间距离甚远,互不侵犯。小地主带领了杨桥村低年级的五六个小孩儿,盘腿坐成一圈儿,在等待学校大门打开的时间里,无聊的扯开松紧带的尼龙裤子掏出小又鸟又鸟玩。于是,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以小地主为首的杨桥村的小孩儿们在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贾杨李小学门口,进行了骇人听闻史上罕见的又鸟巴会议。或许是因为过于投入会议,我竟然丝毫忘了周围有没有人和我们做一样的事情,更不记得旁边是否有众多女孩走过或者看到,我印象最深的只有堂哥,堂哥伸着沾有白色东西的手指头给大家晃一圈,郑重其事地说,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雄”。大家对“雄”不甚了解,莫名觉得有“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充满了佩服的看着他,这事儿过去不晓得多少年后我纠正他道,你那不是“雄”,是垢!
我对静静的印象至今保留在一首歌上,耳边响起这首歌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静静,而想到静静自然而然就想到这首歌和她们排练舞蹈的样子。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这歌声,
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
明天明天这微笑,
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
开学几个月后,老师带领同学们为庆祝元旦排练歌伴舞,静静作为当仁不让的全场的主角,既唱又跳的在教室后排的空地上莺声燕语轻舞飞扬,我作为自命不凡不屑于参加活动的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在一旁托着腮帮子看,怎么看都觉得好看。怎么看都忍不住想要跟她说话的冲动,但矜持如我者,想多做少如我者,依然不肯上前跟她说话。不说话又憋的慌,只好转身对荷花说,你咋不上去跳舞唱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