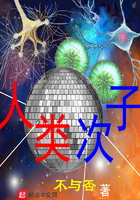金光有个小伙伴,叫做李小妮的,不嫌弃他经常赤身裸体的穿梭在人群中,愿意追随着他。他俩时常在一起托着腮帮子坐在北河之堤,看着暗流涌动的北河之水向东流去。或者每当金光赤裸着身体坐在河堤的夕阳下时,细心的小妮便会在一旁给他驱赶蚊虫,而金光则像一座雕像,全神贯注的看向河对岸,参差不齐的垂柳,一望无垠的田野。
起初的金光,神智并没有那么混乱,行为也没有那么大胆,本身是个秀气又内向的人,即便受了再大的刺激,冷不丁让他脱光了衣服站到人堆里也是有难度的。受了刺激后骨子里的腼腆依然让他害羞的像个姑娘,即是姑娘,那么衣服自然得一件件的脱才显得庄重。这一个庄重就是三年五年,从上衣脱到只剩裤衩,最后才索性把裤衩也褪去已经又过了三五年光景。这时候的金光已经接近三十岁,而他的好朋友李小妮也终于长大成人,至少从个儿头上能够获得与金光并排走路的资格。可是偏偏,妮儿的手脚不利索,步子迈起来费劲,胳膊和手也不是很受控制,容易抬起来不由自主的往两边抻,嘴巴略微倾斜,说话含糊不清还慢慢吞吞且词不达意,眼神儿略差,耳朵略聋。也正是因为这样,没有朋友的妮儿跟着没有朋友的金光,闯荡贾杨李。讲到这里我不禁要说,妮儿虽然叫妮儿,但却是个男人,就在去年晚些时候,派出所户籍科的人才知道妮儿的性别,给他更改了户口本和身份证,李小妮,男,一九七六年生。而一直被官方作为女人生活了四十年的妮儿,户口本的性别设定对这样一个他貌似毫无影响。毕竟他只有金光这么一个朋友,毕竟不会有女人嫁给他做老婆。
随着金光的疯病越发厉害,他的养父母开始经常把他锁在家里。一是为了他少出去丢人,二是让他别出去惹事儿。他从赤身裸体在街上行走到开始冲人谩骂,发展到后来拿着砖头朝人挥舞,做出一副要打人的样子,阴阳怪气的咋咋呼呼。这些恶行伴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让人对当年那个惨遭不幸的大好青年所存有的,指甲盖儿大小的那么一丁点儿,少的可怜的同情,消失殆尽。好在他终究不是个敢惹事儿的人,就像朝大许一样,至死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旁人。不过,他真要在外面拿砖拍了人肯定会被群起而攻之,好几次,堂哥都想要壮着胆子上去逗逗他,好在自始追终也没有真的去招惹过他。既然他内心有洪荒之力无处发泄,加上常被锁在家里无法上街,无论是出于对父母或者社会的反抗,还是处于过度压抑的扭曲,亦或是他产生了父母是害死他对象的暴徒的某种幻想,他开始在家里打他爹娘,而且打的很狠,是那种往死里打的很。邻居经常会跑过来阻止他的暴行,而他娘总是挨打完了带着伤,一遍呜咽着一遍给他洗衣做饭。他爹则更多的只能逃出去,到金光的亲爹娘那里去诉苦。面对金光的变故,他的亲爹娘一如当初把金光过继出去时候的决绝,无动于衷之余也袖手旁观。我曾就金光的问题咨询奶奶,我说他都这样了为啥亲爹娘不管呢,奶奶说,这种事情,送出去了就不敢再多管了,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但是插不上手,也不能随便插手。如果是个正常亲戚家孩子出了这样的问题,帮其来倒也自然,偏偏就是这种亲生骨肉送出去了,管多管少都太难拿捏。这种把孩子送人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加上在大家看来,金光在村里越来越丢人,也越来越惹事儿,索性不管反而倒是更省心的。
这天下午,妮儿拖着那看起来永远比心情沉重还要沉重的步子挪到了金光家门口,见四下无人,便用并不灵活的手灵活的解开了拴在栅栏门上的铁链子,走向偏房。他两只手罩起眼睛,紧紧趴到窗户上朝里张望,只见金光光溜溜的躺在床上挺尸,妮儿大惊失色,往后腿一大步,然后跳将起来就开始斜冲上去撞门,虽然说门上有一把生锈的铁锁,但房子毕竟是破旧的土屋,经过一阵猛烈的撞击,纷纷扬扬的灰土之中一声哐当巨响,门锁安然无恙,门带着门框带着妮儿,整个从门洞里倒进屋里。妮儿顾不得浑身疼痛,三个轱辘踉跄站起来,又用了五个站不稳的箭步才跨到距离门洞两米远的土炕前,一把抓住金光的胳膊使劲摇晃起来,嘴里大声的咿咿呀呀的嚷叫着。光着的金光被他一公分长,填满了泥垢的指甲扎的嗷嗷直叫,抬手一巴掌反打在妮儿的灰头土脸上。妮儿虽然挨了巴掌,但是看到金光没死,按耐不住的咧着嘴流着斜唌咯咯笑起来,两只本来朦胧不清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漏着喜悦与兴奋的微光。都说傻人有不同寻常的感知力,或者某些奇怪行为具有预示性,此话在妮儿身上一点儿不假。他担心金光在屋里死掉了之后的一周内,金光真的在屋里死掉了。应了那句话,赤条条的来,光溜溜的走。他曾经为之走火入魔的执念,急火攻心的憎恨,在他吃不上喝不上的时日里,充当着一种精神食量,坚持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筋疲力尽一命呜呼,在事隔二十年后追随那红颜薄命的董家姑娘而去。
妮儿是个善良老实本分的人,虽然身残智不全,但是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周围几家邻居,哪家有事儿他一定会出现在帮忙的人群当中,比如摆喜宴,他不能一次两只手各拿一个凳子,至少可以两只手抱一个凳子。再比如地里割麦子,别人割十垅地的功夫他可以慢慢的割一垅,至少是慢工出细活儿。如此,东一家西一家的忙活开来,妮儿倒也算得上靠自己的双手吃饭的人。在若干年后的现在,每次回到贾杨李都会看到妮儿在表叔家里帮忙,或是帮他看门,或是给他跑并不快的腿,而表叔只要是妮儿在就会管他口饭吃。我记忆犹新的一次,我带了些人去村后北河之堤上,表叔的贾杨李大酒店吃饭,坐在河堤之上,小风徐徐的吹着,看着落日映在北河大桥上,映在帮忙拿马扎拿碗筷的妮儿那若干天或者若干年没洗的脸上,不无感谢的邀他一起坐下吃,他傻笑着摆摆手,慢吞吞的的说,我,吃,了。然后退后两步,站在一旁看我们吃饭,他那样我是吃不下去的,便推过一个马扎去给他说,你坐会儿吧,抽烟吗?表叔接话说,妮儿人可好了,自从我开起了这个饭店,每天在我这跑前跑后的,我这儿倒也不需要人手,但是他愿意在我这里玩,我就管他饭,啥时候饿了就来我这里吃饭,倒也不多他一双筷子。然而我们的金光,朝病愈发厉害的金光,直到他娘去世,八十高龄,被他打怕了的父亲也顾不上他吃喝了,才饿死病死在妮儿撞烂门洞的茅草屋里。
人们说,别看妮儿人傻,但是金光的死对他的打击还是很大的。金光死后,他曾经几天见不着人,后来才被人发现是他自己坐在金光的坟前几天几夜。晚上就倒在坟地里睡,白天就坐在坟头前发呆,隐约听到他自言自语絮絮叨叨。他回来的时候,只穿了一个破烂秋裤,光着背光着脚,身上头上满是黄土,头发像鸡窝一样,眼窝像鸡蛋一般。好在坟地里有很多坟前有或新或旧的祭品,倒也不至于饿着。特别是在离金光的坟不远处,有一做硕大无比的坟,坟前石板上各色水果,馒头,白酒,甚至还有鸡鸭鱼等佳肴,堆得满满的。
这座坟就是传说中的宋先生坟。童年时期的我,第一次去宋先生坟,自然是在堂哥的带领之下。我们早熟的男子汉一样的小地主,自从找了李家姑娘做小地主婆,开始变得更加男人。隔三差五的就要给李家姑娘拿个苹果,弄个香蕉,鸡蛋或者弥足珍贵的钙奶饼干。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被命令从家里拿东西的次数增加了,甚至,有时候拿过去的苹果个头达不到他的要求也会挨骂。除了从我家里和他家里拿东西之外,他还另辟捷径,带我们去村东的田野中并不算大的苹果园里偷苹果。那片果园虽然看起来郁郁葱葱,但是树和树的间隙十分之大,在间隙之间,会有若干个坟头,在田野之上也零星散落着若干坟头,这样一来,树林中的坟和田野中的坟,形成了大片坟地。而宋先生坟就在田野里,于群坟之中高高耸立,上面插满了各种颜色的新旧彩旗,迎风招展,呼呼作响,好不威风。堂哥带我们去偷苹果的时候,往往会被看果园的五爷爷看到,先是吆喝,然后拿着棍子奋起追赶。这也就是为什么堂哥会让我把冰放到五爷爷被窝里的原因。那时候尚且年轻一些的五爷爷看管着村里共有的果园,而作为孩子王的堂哥便是挂了号的偷苹果惯犯,心里自然是逮着机会就要报复一下的。五爷爷看园子的时候在一个离果园不远的,某户人家盖的新瓦房里寄居。新瓦房只是盖了起来,没有门没有窗,里面依然是没打水泥地面的泥土地,顶子是没吊顶棚伸着麦秸秆的席篷。五爷爷在靠墙的地方打个地铺,下铺一层盖粮食用的防雨油布,上面铺了白花青底的粗布褥子和被子。小地主带领我们进到五爷爷的临时的看护宿舍,命令我们集体往褥子上撒尿,善良如我者,故作一脸愁容的说,哥哥,我刚尿了,实在尿不出来了,能不能不尿。小地主白我一眼,不屑的,果断勇敢的,第一个把裤子退到膝盖,掏出他自觉已经带雄的小鸟儿,挥洒自如的来了一个锦上添花,其余几个小孩儿自然是不敢怠慢的,也学着他的样子,锦上再三添花。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长江商学院的口号,“因为向往大海,所以汇入长江”。
不记得是在五爷爷第多少次追赶的时候,我们被赶进了以宋先生坟为旗帜的坟地里。我们几个集体趴在了宋先生坟前的土沟里,再往后远远望去,早看不见五爷爷年迈但挺得笔直的腰杆儿,也听不到那声如洪钟的叫骂声,这才放下心来。稍顷,不等我们完全平复了急促的喘息,便对眼前这座五彩缤纷的,体态丰硕,造型出众的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五爷爷和果园瞬间抛之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