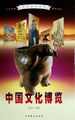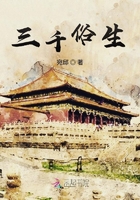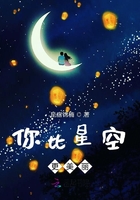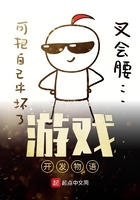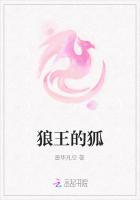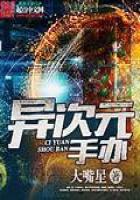(第一节传统孝道的内在矛盾
省察传统孝道,其间不乏道德上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是角色规范的冲突。任何一个社会人都同时兼有多重身份,每一身份都有相应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在遵守这一规范的同时,往往违背了另一规范,于是就造成了规范冲突和角色混乱。前述孝与忠的冲突正是这种角色冲突的典型表现。二是基于对不同行孝主体、不同行孝情境的不同要求,使孝道规范自身出现了混乱。
一、保生全体与舍生取义。
道德评价既是对人之道德动机的价值评判,也是对人之道德效果的价值评判。但动机与效果常常是不一致的,这就造成了道德评价的复杂性。孝道的许多悖论就是来自于动机与效果的背离。
比如,保护身体不受伤害是孝道的重要价值规定。《孝经》要求孝子居丧“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唯其如此,才能为敬养父母、恪尽孝道提供最起码的保障,“父母全而生之,死全而归之,可谓孝矣”,“能全支(肢)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同时,为尽丧而毁身灭性是却又是孝的表现,是历代表彰孝行的重点内容。譬如,居丧者庐墓数载,乃至毁身灭性、悲郁而死,是出自对父母的哀思追念,动机是“孝”;但从效果上说,除昼夜悲哭外无所事事,既没有爱护父母所遗之体,也不能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更不能继先人之志,述先人之事,完成传宗接代、显耀门庭的使命,不孝之罪诚为大矣。割肝剔骨疗亲疾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这种“不孝”虽有乖先王之典制,所造成的后果仅仅牵涉到行为者自身,对社会不但没有危害,而且观过知仁,对孝道的倡扬大有裨益,所以历代对此类孝行的表彰都是从动机论出发的,也极少为此而发生异议。这与复父仇者的情况不同。复父仇属于角色冲突,其动机虽然是“孝”,但其效果却违“忠”,也即违孝,为私孝而损公法,这就不可能仅考虑动机而置效果于不顾,因而为处理复仇案件而争执不下,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同样地,如果仅从保生全体为孝的效果论出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乃是不孝之举。但是,真正的爱身、保身、不辱其身,并不是消极地无所事,而要积极地有所为,不是怕伤,怕死,关键是死伤要有价值。奉行孝道的中国人是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的:“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荀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为道德理想、公利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为公为忠而杀身舍生、名垂丹青、光耀门第,这是孝道价值的最高实现形式。孝道中蕴涵着道义的原则。道义是封建社会政治、伦理价值的凝聚,它与父家长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指导父子关系的最高原则。所以,所谓“伤足不出”、“拔矢啖睛”、“全尸而死”之类均属于爱身和不辱的低层次,更重要的是把保身、守身与立身、立志、守道、守义统一起来。
道义同样也是把握顺与不顺、谏与不谏的最高标准。一般地说,子女应当无条件地顺从父母。但是,象曾子那样,“事父母,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他应该象舜那样,“小棰则待过,大伏则逃走”,使父“不犯不父之罪”,子“不失蒸蒸之孝”。再以进谏来说,指出父母之过、顶撞父母本身是不合孝道的,然而,进谏是为救亲之过,亲之命可以从而不从,是悖戾;不可从而从之,则陷亲于大恶,则是视父母为路人。所以,“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畏鞭棰之严而不敢谏其父,非孝子也。惧斧钺之诛而不敢谏其君,非忠臣也。”由此,汉代仲长统提出了“父母可违”的伦理命题:“不可违而违,非孝也;可违而不违,亦非孝也”。从表面上看,谏父、不从父似乎与敬顺之孝道要求相抵牾,但在“不从命”的表象背后,却是对父家长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积极维护。
有矛盾才有辩证法,有矛盾才有发展。其实.这种在孝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针对不同情况而形成的特殊价值准则和具体行为规范,正是儒家“经”、“权”辩证关系在孝道中的体现。“孝子唯巧变”,人子行孝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这是在近乎封闭的孝道樊篱中为孝子们留下的一方极为有限的自由空间。也唯因具备了这种灵活性和适变性,孝道才不但没有因其绝对化而走向僵死,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它对各阶层的实际约束力。这也正是传统孝道的生命力所在。
通观历代孝子的孝行,尤其是孝子们丧心病狂的自虐自残如卧冰、尝粪、恣蚊、燃指、割股、剖肝,或虐人残人如休妻、埋儿、卖女,、杀子等“愚孝”行为,我们认为,传统孝道最大的悖论就在于:它在诱导、奖掖、歌颂人子之孝的同时,却把封建家长的愚昧、暴虐、刻薄、寡恩的丑态尽展无遗,无形之中将为人父母者陷于不慈不义之境地。从传统孝道“勿陷父母于不义”的要求来看,这本身就是大不孝。如朱熹的弟子就曾提出这样的疑问:“舜不能掩父母之恶.如何是大孝?”对此朱熹搪塞道:“公要如何与他掩?他那个顽嚣-已是天知地闻了,如何地掩?”袁枚也讥刺埋儿尽孝的郭居日:
“拟以埋闻,母弗禁,似母勿爱儿也。以恶名怼母,而以孝自名,大罪也。”这个悖论又该如何解决呢?
二、权利与义务的背离与统一尊卑长幼代际关系具有相对性。如果仅仅就一代亲子关系而言,孝道固然是子对父单方面的、片面的义务,但若从家族生命链的角度看,孝道其实依然保持着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在代际之间完成的:伦常之网在自然力的推动下,缓慢地垂直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属伦理自然更替,为人子者成为人父,为卑幼者成为尊长。“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亲在我之上,子孙在我之下”,这样,每一个人都机会均等地经历着先行孝、后被孝的身份轮换。这也就是俗话说的“千年的古道变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个“熬”字,透出卑幼者对自己卑幼身份的不满和无奈,以及对获得尊长身份的期盼和欣慰。
这种期盼和欣慰里面,暗含着一种要求“补偿”和“回报”的心理。补偿的要求来自于自己做孝子时所付出的一切,“回报”的要求则源于为抚育下代子女而在物质上、精神上的付出。因而,他们理所当然地期望得到子女的双重补偿和回报。
子女的孝就是对他们的补偿和回报。孝道正是以反本回报为运作逻辑的。
就前者而言,斗转星移,以自己为卑幼者时对上代所行之孝作为资本,必然要求自己的孩子去做孝子。“孝顺应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若自己没有对上代尽孝,也就失去了要求“补偿”的权利:“每常人责子,必欲其孝于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你怎样对待上辈,下辈便怎样对待你,“不孝其亲,而欲子孙事我以孝,岂可得也?”元谷行孝的故事戏剧般地耐人寻味:“元谷者,不知何许人。祖年老,父母厌患之,意欲弃之。谷年十五,涕泣苦谏,父母不从,乃作舆舁弃之。谷乃随收舆归。父乃谓日:尔焉用此凶具?谷乃日:恐后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父感悟愧惧,乃载祖归侍养。”
就后者来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父子之间存在着对等的回报和互惠:“夫礼与律皆尚往来,借人一钱者必当偿之,受人一饭者必当报之;借钱不偿,则法有刑;受饭不报,则俗有议。……受恩之重大莫过于父母,故酬恩之重大当责之于人子矣。……若不孝者,其律可依欠债不还,科而罪之。”富贵者指望儿孙光耀门户,贫贱者亦望其反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多子做福”便是孝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封建社会人们对生育的热情一半出于传宗接代的伦理需要,一半则来自养老送终的功利目的。只是在父母一方,几乎是一次性付出的,“父母,子之天地与?无天何生,无地何形?”对子女而言,对这种恩情的“还本付息”式的回报则需要一生,“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如父母”,“从来亲恩报当先,说起亲恩大如天”,“父母恩情似海深,人生莫忘父母恩”,所以孝也就成为人子的终身行为。即使如此,还是不能达到“养”与“孝”之间的平衡:“子虽终身承颜致养,极尽孝道,终不能极其少小爱念抚育之恩”,“想汝身从何而来?即使捐生报答,也只当欠债还钱”,何况孝道还有不尽者。
这样,虽然从理论上说,补偿和回报都应该是对等的,但实际上父母孝先辈和养子女行为在时间纬度上的优先,已潜在地决定了对等的不可能性。因而生长在孝道环境中的子女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作为尊长和家族象征的父母,即心甘情愿地交出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权力,包括自由和生存的权力,作为对父母的补偿和报答。尊长也理所当然认为自己以孝上代和养下代作为预付资本的艰难付出,足够任意享用和挥霍儿孙的孝顺,因而“变本加利”、滥用权力的现象极易发生。这就不仅要求自己的孩子做孝子,而且一代一代都在孝的链条上增添新的环节、新的内容。这种循环效应使得孝道愈发走向异化,走向极端。
三、孝顺父母与家无二尊。
我们一般只是笼统地说,“孝”的对象是祖父母、父母,这固然是没有问题的,社会、法律也要求子孙对他们同样的孝顺,“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但是,若把“君父各有疾,有药一丸”的假设移借为“父母各有疾,有药一丸”,选择就不免再次陷入两难境地:
这粒救命的药丸是给父亲,还是给母亲呢?
对于我们来说,君父之间的选择也许倒不困难,于父母之间如何忍心进行取舍?但是,依照传统孝道,父母间的选择比起君父间的选择要容易多了。这是因为,国无二隆,家无二尊,父亲虽然“尊而不亲”,母亲则是“亲而不尊”,父亲才是真正的“家长”。严格地说,父权与夫权的结合决定了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妻对夫的“从”,决定了母对父的“从”。相应地,母权是得之于父的,是父权的延续,是植于孝道的需要,《礼记?哀公问》云:“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所敬的并不是妻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亲,因为她负有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神圣责任,自不得不敬之。母亲之尊,是借自父亲的,如《仪礼?丧服》要求“继母如母”,原因是“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女子缺乏独立的人格和相应的社会地位。因而母权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绝对的。当母权与父权发生冲突时,父亲的话才是最高的绝对的命令,“兼一家只容有一个尊长,不容并,所谓‘尊无二上,也”,“母终不可以并乎父”。丧服制度是很能体现父尊母卑的礼教观念的。如《礼记?丧服四制》
规定,为君、为父都是服斩衰三年,母亲则是齐衰。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父亲在世,则只为母亲服期丧,唐开元年间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改为齐衰三年,一直到明代才“定制子为父母斩衰三年,后为定制。”究其根源,《礼记》坦言:“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张载也说得很明白:“父在,母服三年之丧,则家有,二尊,有所嫌也。处今之宜,但可服齐衰,一年外方可以墨衰从事,可以合古之礼,全今之制。”“礼,子于母则不忘丧,若父不使子丧之,为子固不可违父,当默持心丧,亦礼也。若父使之丧而丧之,亦礼也。”清人也说:“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同时,法律也毫不掩饰地置父权于母权之上。例如,亲属容隐制度规定子女应为犯罪的父母隐匿罪行。但若遇到母亲杀害父亲的情况,子女该如何处置呢?对此,法律采取了重情压轻情的原则,规定:母杀父,不论是继母还是嫡母,子女皆不能再履行为母容隐的义务,必须向官府告发母亲的罪行,相反,父亲杀害母亲,则可适用容隐制度。如清律规定:“父为母所杀,其子隐忍,于破案后始行供明者,照不应重罪,杖八十。……若母为父所杀,其子仍听依律容隐免科。”
一个有趣的、也极容易造成误解的现象是,在二十四孝孝亲事迹中,被孝的对象,除父母双孝的六例外,孝母者为十四例,孝父者仅四例,对母亲的孝占了绝对优势。在历代正史的“孝行传”、“孝义传”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但这并不能说明母亲比父亲更受尊重,只是表明在传统亲子关系上女性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而已。传统家庭中父母的一般形象是“严父慈母”,母子关系要比父子关系亲密得多。因而不难想象,与对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孝“相比,子女对母亲的“孝”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应该多些。“亲“与”尊“本来都是孝道的要求,但父亲的尊而不亲与母亲的亲而不尊,恰好反映了礼法与情感的不一致。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个与此相应的现象:二十四孝中,孝亲的主体几乎清一色的是男性,历代孝子传中记述的也几乎都是孝“子”,孝“女”或孝“媳”只占了很小的比例,而野史、笔记、小说中因不孝而受到种种报应的却多是媳妇。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对母亲在孝道中的地位的又一种变相的诠释呢?
四、传统孝道中的血缘优先原则
从起源看,父子关系是由夫妻关系衍生而来的,即《易传?序卦》所谓“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但是,在古人看来,夫妻关系乃“人合”,只是一种社会的或法律的关系,与有天然血缘联系的“天合”的父子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婚姻的目的即是尽孝,妻子的责任就是事父母、奉祭祀、继后世。所以,孝子“常语其妇日:汝事吾母,小不谨必逐汝。”即使谨小慎微,妻子为鸡毛蒜皮之类小事招惹姑舅不欢,继而被遗弃的事仍屡屡发生,而且被当作孝行而大加褒扬,被誉为美谈而千古流传。如“姑前叱狗”讲鲍永妻因当着婆婆的面斥狗而被休;“缘壁挂履”讲刘钀妻穿壁挂履,土落在婆母孔氏床上,孔氏不悦,刘即出其妻;“蒸藜出妻”讲曾子妻因把没有蒸熟透的野菜给后母吃而被休。孝子姜诗“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谴之。”可见这些“美谈”的背后,隐藏了多少个无辜女子的泪水。有些孝子为避免娶妇不孝父母的可能性,索性终身不娶,如汤某就声称:“何忍分养母力以养妇?”四十多岁的夏某勉强成亲才半年,即因“妇与姑诟于室”而出妻,当别人问他“出妻,如无后何”时,他坦言:“有妇,欲其孝;有子孙,亦欲其孝。荀不孝,安用妇?安用子孙?”
兄弟关系也以其血缘性质而优先于夫妻关系。没有血缘关系的夫妇之情是不能与兄弟之情等量齐观的:“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后手足乎?”家族血缘体系天然地具有排外性。传统伦理认为,由来自地缘关系的婚姻所带来的血缘异己成分,是破坏宗族和谐团结,导致兄弟疏离分析、别籍异财的主要力量:“盖兄弟之不和,多起于妻子之离间。”
后世单纯作为家庭伦理的“悌”观念,重点是针对已婚的兄弟,目的是维护血缘家族的生命。所以有些特立独行之士为免兄弟相疏而不娶妻,如唐代阳城兄弟。更有些已婚的兄弟仍然同床共卧,只是为了生子立嗣的需要,才与妻子同居。基于家族伦理的至上性,这种不近人情的教化风行于世。近代有人依照《二十四孝》
编撰了《二十四悌》,可谓深得“悌”之要领。这样,以孝来保证纵向的延续,以悌来保证横向的蔓延,则家族之大树何以不繁茂?
(第二节近现代知识界对传统孝道的批判和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