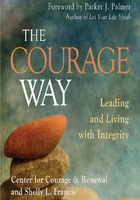剑法练了一月有余,转眼,已到了寒冬。长留虽未大雪纷飞,却也比往日寒冷许多。修仙之人自有御寒之术,因此不甚怕冷,温度的改变对他们而言并无多大差别。
这几日紫萱的仙术和剑术也是愈发进益。这套为她量身而设的剑法已练到最后两式。有白子画从旁协助,她的吐息功法也已至上乘。当真是与她的体质相宜,这些日子发现身体更有力气了,睡眠越来越好,容颜也愈发靓丽。甚至素颜之时也好似上了淡妆一样。
不过,这几日夜晚,白子画没有似往常一样待她安睡后再去入定,反而是拥着她睡至天明。每次她醒来,都在他怀里。有时还被他缠绵地吻着。
他有心事。她看的出。
有时他们在行事之时,他会轻抚着她左胸前的痕迹出神,在耳边念着她的名字。
她有些担心。看见他在风露石上弹奏古琴,俯瞰长留众生,便取来玉笛,在他身后吹奏。
琴笛和鸣。他的曲子原本清冷孤高,身处化境。却不自觉被她玉笛的清音带向了情思波动。原本无恋无欲的长留上仙,竟然会弹出这样有情的曲调,而且会被笛声牵引而走,真是件天下奇闻。
他停下,回望。“萱儿,你这是何意?”
她轻笑,在他身旁坐下,偎进他怀里,故作瑟缩。
“冷…”她轻哼。
他笑了,抱紧她,“怎么这样爱撒娇?嗯?”
“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他低头看她,“好啊。”
“相传有一只银狐,千年修炼后,成了人形。她爱上了一位男子,他们度过了一段温暖而幸福的时光。却因为人妖不能相恋,亲眼看着他娶妻、生子。他死去时,她耗费自己千年修行的内丹救他夫妇二人,终还是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她在他怀里换了个方向斜靠,继续说,“后来她万念俱灰。你应该知道,妖没有内丹,唯有画皮食心才能保留人形。五百年来,她便成日流连于青楼楚馆,以美**之,食那些贪财好色之人的心脏,才能撑到月圆之日。她却因为自甘堕落、滥杀人命,而被狐族押回,关进了寒冰地狱。”
她语调温柔平淡,长发低垂,看不到她的表情。他静静听着,为她暖着手。
“后来她被母亲想方设法救回人间。可是她并不想回到那个没有他,没有爱和温暖的地方。还不如呆在寒冰地狱,忍受着每日的冰刑,让寒冷渗入自己每一寸身心骨肉。可是,她却机缘巧合地遇到了他的后人。和五百年前的他是那么像,他对她很好。在他怀里,她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她瞒着自己的身份,一直在他身边默默做一个温良娴淑的女子。却不忍再食人心。每到月圆之日,她只能躲起来,独自忍受着剧痛,苟延残喘。”
“他是习武之人,志愿保家卫国。战场上,她救了他许多次。他也爱上了她,许诺照顾她一生一世。那天,她好开心,他是她活下去唯一的理由。”
“直到有一天,一只妖借机生事,变成她的样子剜军中将士的心脏。他虽不信,却证据确凿。那日,她在他面前被人逼着现出妖形。他的眼里尽是失望和愤怒。她申辩,她没有杀人。除了自己是妖以外,从来没有骗过他。可是他再也不信她的一句话了。他要她滚,滚的越远越好,死也不要再见她一眼。他恨她骗他。”
讲到这里,她的眼眶红了。白子画察觉到她的手越来越凉,蹙紧眉头。
“萱儿…”
“等我讲完。”她固执地说。
“她知道会有这样一天的。只是还会天真地相信他的话,以为那份温暖是永不背弃的。他曾经是爱她的。可是,人妖殊途。”
她讲到这里,停下了。沉默了很久。
“子画,如果是你,一定会去超度那只狐妖吧,让她别再执着于****。”她笑道。
他搂紧她,低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是啊。我会这么做。修行不易。这只狐执念太深,只会伤到自己。与其如此,不如让她忘却前尘往事,重新入道修炼。”
她从他怀里坐起,笑了笑,平静说道:“我能理解。”
“萱儿,讲了这么久故事,累不累?”
“萱儿?”
她低头沉默。
“那你呢?”她忽然问道。
“什么?”
“你就没有执念么?很快,我们去人间,面对上一世的过往。若是你真的想起,上一世自己心心念念要忘却的人。又该如何?”
她如何不知,他的过去,和她息息相关。
这几****加倍爱她宠她,时刻抱着她,是怕什么?怕自己也无法面对这过往么?
他轻叹,重新揽她靠进自己怀里,和平常一样包裹住她的身躯。
原来讲了这么久故事,是在担心他,担心他会处于道心和爱的两难而痛苦。
殊不知,他从没有这样想过。如果可以,他并不想知道前世到底怎样。只是为了保护她。她命中似有劫数,如今却勘不破。
“我不会逃避,也没必要逃。记忆再怎样轰轰烈烈,毕竟是过去了。萱儿,我担心,是怕你。你会逃。”
她愣住了。能够让他们二人都忘却的记忆,该是怎样呢?相爱到怎样的地步,却是相忘的结局?她会为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而落泪,真的有勇气面对他们的过去么?
一直怕他会后悔,其实,她才是最脆弱的。
珍惜的吻轻轻滑落,他锁着她的身躯,望着她含水的眸子,直望到心底。
“所以,我决定,无论回忆起什么,都不让你知晓。”
她惊讶,“这…”
听到他一字、一句地说:“我要你,自己,想起我。”
她怔怔凝望着他,却忽然亲上他的唇。微笑着,点头,“好。”
他回吻,却发现她目光有些犹疑,欲言又止。
“如果你是那只狐,我只愿你爱上的,是一个信你、爱你,不会伤害你的人。”他竟知道她在想什么。
还是不甘心地问:“如果我原是一只妖,而你是上仙。你会因为我是妖而不和我相爱么?”
女人是不是都喜欢假设这种不可能的问题?他无奈。
便是她真是妖,他又能拿她怎样?
却也认真回答她,“在我眼里万物众生皆是平等。你是妖是人,我自然不会在意。如果可以,自会度你成仙。”
她是不是该庆幸,爱上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