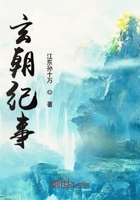十月初二日,黄历上写,宜嫁娶,裁衣,祭祀,开墓,入殓,举丧。忌掘井,扫除,迁移。
钱家大宅。
高高的灵台摆设在大堂里,大堂被一块黑色的帷幕断成了两部分,前一部分顶着帷幕放着一张大方桌,桌子上摆设着灵位,祭品,火烛,桌子下首,一个大铜盆里,高高的火焰正吞吐着它的火舌,铜盆旁边,一个身着丧服的男子正不断的往里面添着冥钱。
一身着怪异服装的道士围着火盆乱跳着,他左手攥着一把带血的纸钱,右手举着一柄锈迹斑斑的铜钱剑,摇头晃脑,左蹦右跳,口中念念有词,那双本来就不大的眼睛,时而紧闭,时而又睁得浑圆。
而铜盆后面,一群人披麻戴孝的跪坐在灵位前号哭着,在人群的最前边的,是我。
“三弟,你已经守了一夜了,我来替你吧!你快下去休息,可别把身体给累垮了。”
温和的声音传来,我抬头一望,却是钱季站在了我的身旁,他的双眼通红,面露悲戚,眸子里更是射出掩饰不住的关心。
这是在猫哭耗子么?就像吃了老鼠屎般,我胃中忽然翻滚出一股强烈的恶心之感。
自从大哥死后,这钱季仿佛就跟换了一个人一般。大伯伤心过度,一病不起,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所以大哥的丧礼,基本上全都是钱季一手操办,没想到他不但是办得井井有条,而且在待人接物上更是表现得分毫无差,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就是钱家费劲心思培养出来的接班人!
或许,他已经把自己当做了钱家的接班人?
我面无表情的瞟了他一眼,强行把这股不适感按捺了下去,站起身来,从他面前一走而过。
在大哥大丧的这个关口,想来他也不会多想什么。
我走到帷幕的另一头,那里,八张黑色的条椅被摆成了一个奇异的符号,据外面那个道士说,这是个招魂安魄的法符。
条椅上面摆着一块桃木木板,木板上被众多金银彩罐拥簇着的,是一个正在安睡的男子。
男子躺在木板中间,八层华丽的锦衣让他的身形略显臃胖,却让他那因浸水而浮肿的身体又匀称了起来,他手指自然伸展着,面容安详而恬静,嘴角似乎还带着微微的笑。
是在那边过得很开心么?大哥。
我默默注视着这个男子,眼中似有湿润,嘴角却突然一咧。
大哥,你快乐就好。
......
时至中午,天上却没有了太阳。
大片大片的灰云漫天而过,天地间的一切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惨淡。
冷风阵阵,地面的残币和着灰烬一起漫天飞舞。道路两旁立着两行招灵番,番上长长的白色布条被风吹得高高扬起,像是恋家的游子依依不舍的挥手,又像是不舍的父母伸而未得的衰老的手。
丧礼还在继续,悲伤,还在延伸。
忽然,就听得门口小厮颤声大声喊道:“李家李苍松大老爷携子珩前来拜祭!”
众人顿时一惊,连忙起身回望,就见得李家家主李苍松和他儿子李珩走了进来。两人身着素衣,面沉如水,看不透情绪。
李苍松和李珩继续向前,一条通道自动退让出来,众人低着头,面面相觑,却又不敢上前,似乎面前这两人是某种可怕的瘟疫。
两人也不在意,走到灵前,李苍松皱眉道:“小厮呢?还不拿香上来?”
点香的小厮畏首畏尾的站在一边,那紧攥着香的手手指节都发白了,却是死也不敢把香递上来。
李苍松脸顿时一沉,喝到:“你家主人就是这么教你的?”
常年蓄养的上位者的威势随着这一声沉喝瞬间展开,拿香的小厮浑身一哆嗦,差点连站都站不稳了。
我刚想上前稳一稳局面,就听得一声冷哼挟怒而来。
“哼!你们李家还真是好大的威风,把我大哥杀了还不够,竟然还跑到他的灵堂前面来闹事,你们就不怕天打雷劈么?”
我循声望去,不远处,钱阳龙和钱季正迅速的往这边赶来。
“季儿!”钱阳龙不满的瞪了钱季一眼,随后朝着李苍松拱手道:“李兄,却没想到你今天会来。”
“我不能来么?”李苍松向着四周低低的扫视一圈,声音里透着一股从容不迫的气度,“我李家与钱家在这城中并肩而立二十年,今天令贤侄大丧,老夫于情于理都应来拜祭一番!”
钱季眼睛怒睁,道:“哼!有谁不知道......”
“季儿!”钱阳龙语气加重,钱季顿时不做声了,他怒气冲冲的撇过头去,却马上又扭了回来,两只的眼睛死死的盯着后李苍松一个身位李珩。
“李兄。”钱阳龙再次拱拱手,眼睛却觑向后边低着头的李珩,“令郎作为杀害羽儿的最大的嫌疑人,李兄此时来拜祭,怕是极为不妥当吧。”
“哼!”李苍松袖袍往后一甩,含怒道:“我李苍松行得正坐得端,有什么不妥当的?”他又指了指自己的儿子,“此事决计不是我们李家所为,珩儿这些天一直都待在自己房里,根本就没出去过,这是我亲眼所见的,试问这如何去找辉夜下单?”
钱季阴阳怪气的说道:“嗬!做父亲的当然能给做儿子的作证呐!莫非你还看见过胳膊肘往外拐的?”
“你.....!”李珩被呛得面色铁青,刚欲说什么,却被他父亲死死的拉住。
钱阳龙此时却没有再却责备钱季,他抬头看了李珩一眼,轻叹了一声,说道:“不管怎么说,那日贤侄是当着众人亲口说要报复钱家的,光凭李兄你空口白牙的一句轻飘飘的话,未免显得太过无力了吧!”
我默默的站在旁边,见着这两人精湛的演技,心中蓦然一寒。
李苍松刚要开口,后堂却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不过片刻,就见得一大群人从里面冲了出来,有拿水盆的,有拿毛巾的,有那衣服的.......有小厮,有侍女,还有......大夫!
众人都面带急色,大声的吆喝着:“大老爷!大老爷!您回来!您快回来!”
而他们的前面,一个身穿白色袭衣的老人正踉踉跄跄的往这边跑来,老人披头散发,脸上涕泗横流,态若疯狂。
跑一段,他又把手中的木拐杖往后一挥,把欲上前的小厮们往后一逼,又继续往前奔来。
钱阳龙面色顿时变得铁青无比,他撒开腿向老人那边就跑,边跑边大声喝骂道:“是哪个猪脑子把大老爷惊动了的?看我回头不剐了他的皮!”
他跑到钱阳国面前,张开双臂,像一只护崽子的老母鸡,“大哥,你身体还很虚弱,你先回房,这里交给我处理如何?”
“你给我滚!”
枯瘦无肉的手抓着拐杖向着钱阳龙的头劈了过来,眼中的悲伤已经把他的浑黄而无神的眸子凝固在了眼眶的正中央,泪水与涎水在他沟壑纵横的老脸上肆意流淌着,花白的头发在空中散乱的飞舞,一夜白头。
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吧!
钱阳龙不能躲,但他也不敢用头接,他举起手臂,硬挡了这一棍。
“噗!”的一声,这是棍子和胳膊碰撞的声音,钱阳龙吃痛的捂住手臂,钱阳国却把他弟弟猛地往旁边一拨,任谁也想不到他那虚弱得已经脱了人形的身体里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大的力量!
“大哥!”钱阳龙失声叫到。
可钱阳国却不管不顾,他冲了过来,那模样,简直就是一个发了癫的疯魔!
“宝宝被你们杀了!现在羽儿也被你们杀了!为什么啊!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哭嚎着,在他嘶哑的喉咙里发出的是最撕心裂肺悲鸣!
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可他却不管不顾的往前爬着,爬着......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要杀就来杀我啊!杀我啊!”
他双脚在地上无力的乱蹬着,双手使劲的抠着地面,那瘦得只剩下一层皮的手指在地面上磨出一条长长的血痕!
我心中堵得有些发慌,或许这种情况是大哥没有预料到的?他一定以为就算自己死了,也会和自己的妹妹一般因为家族的利益而被遗忘吧!可是谁又能料到儿女双失对一个花白老人的打击会有多大?
“大哥!”
“大伯!”
两声急切的呼唤,钱阳龙赶紧跑了过去,他把钱阳国报在怀里,朝着四周怒喝道:“人呢?人呢?还不赶紧死过来!快把大老爷抬回屋里去!”
众小厮闻声赶紧围了过来,他们把钱阳国抬了起来,像放一块易碎的花瓶一样小心翼翼的放到了一个身壮体阔的小厮的背上。
“为什么.....为什么啊......”钱阳国趴在小厮背上,口中含糊不清的呢喃着,他的头无力的耷拢在小厮的肩膀上,涎水不断的从他嘴角低落,两只眼睛已经失去的焦距。
钱季双拳紧握,两眼通红,他左顾右盼着大声吼道:“刀呢?刀呢?拿刀来,看我不剁了这两个狗杂碎!”
钱阳龙站起身来猛地一脚踹了过去,劈头盖脸的朝他骂到:“混蛋,你难道要在你大哥的灵堂前见血么?”
他又转过身对着李家父子说道:“二位还是走吧!求你们了!”
李苍松闭上眼睛,长叹一声,他朝着钱羽的灵堂深深的鞠了一躬,又朝着钱阳龙拱拱手,什么话也没说,带着李珩转身离去。
他们前脚刚走,就听得后院传来一阵惊天嚎叫:“大爷!大爷!大爷您醒醒呐!您快醒醒呐!”
我心中顿时一惊,钱阳龙与钱季面色瞬间就变得惨白,三人连滚带爬的朝着后院奔去。
......
新历十九年十月初二日,钱家家主钱阳国卒于钱府内院,享年五十二岁。
十月十八日,钱家次子钱阳龙接任家主之位。
十月十九日,钱家新任家主钱阳龙对外宣布曰:钱季与李家不共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