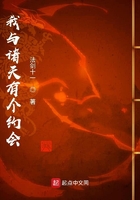(3)以法约束,以德收心
船颠簸的很厉害,有时为了避去一场大风,有时为了躲过一条大鱼,有时为了绕开一个涡流,不停地变换方向。除了鱼,吃不到新鲜饭菜,这样的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岸近了,心情就踏实起来,提前的庆祝拉开序幕,大家尽情享用船上最好的东西,有些人开始谈论老婆孩子和生意买卖,燕如则越来越不喜欢闹腾,还动不动就吐。
这是多晴的晴天啊。舒爽的风中,带着些许泥土的芬芳,远远看去,岸上一幢幢瓦房在秋天明丽的阳光下亲切安详,碧蓝的湖水像柔软的飘带护卫着这个城镇,不时升起的一缕缕青烟温暖着归来游子的胸口,我们都被一种叫做乡土的东西抚摸着脸颊,被一种叫做回家的感觉轻轻拥抱。越来越近,喧嚣声取代了一切,到处是忙碌的人群,嘈杂的声音,纷乱的脚步,和那一张张视而不见的热情面孔。“到了。但不是家。”这是我一脚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感觉。
西泰东要了一辆马车,七拐八拐,把我们带进他家,院子好大,篱笆一圈,种不少花草树木,北边一幢三层小楼,通身铁红色。他爹开个小作坊,他妈则有不同的两个名字和职业:一个是马回兰,家庭主妇,一个是姬图,一小修道院的神甫,都还没回来。燕如一沾床就昏沉沉睡去,我上到楼顶,看这里那里冒出的烟囱,就像一个个茁壮成长的小伙子,不时飘出的烟尘里弥散着一种好闻的焦烧味儿。敲打声、吆喝声隐隐传来,交汇成一条兴奋的河流,不断打破着远处的宁静与悠闲,行色匆匆的人们,紧张、亢奋,焕发着活力、生气。西泰东拿着两酒杯上来道:“这里是天底下最美的地方,你不老问什么是美吗?现在摊开在你眼前了。”我看着远方隐隐的绿意道:“你最有资格说这里的美了。”
“那是。这里的人个个朝气蓬勃,如初生牛犊,他们追求自由民主,崇尚开拓竞争,讲求理性实用。”“自由就在那里,用得着追求?民主也要追求?自然而然、合适不就行了?”“还是大家做主好,通过法律、制度,再也不会有什么怨言了。”我笑道:“可很多人不懂、又没兴趣了呢?就为了让人少些怨言,会不会太浪费人的精神头了?”“你太奇怪了,不愿自己做主,奴性还是惰性所致?”“我当然愿意自己做主,但许多事不懂,瞎做那主干嘛?照我看你们的民主才是逃避和最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是比较冠冕堂皇的说辞而已,而且,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类似群众的暴行更使人反感了。”“有法律保障啊?它是追求自由公正的正确途径。”“我觉得也比一言堂好很多,但有术无道不可取。”“什么术啊道啊,我看你是偏见太深。法律保护财产的同时保护了自由、独立、繁荣和秩序。”“我同意啊,但有时它也限制自由、削弱独立、锈蚀秩序、甚至拖繁荣的后腿,还是得顺道行德。”“你说的‘道’是什么?”我哪里说得清?但还是想了想道:“对人而言,那道就是和融广大、创造日新,就是人德,是人们头顶的美丽星空,是愿望垒起来的城堡,是灵魂弹出来的夜曲,是爱意育孕来的和谐。”“嘿嘿,太飘渺,不切实。这样的人德吧,它不能规范,只能是引领,会叫人无所适从。”
我又想想道:“法倒是清晰,但不照耀,它是盖房的砖瓦;人德则是房里的虚和房外的空,是最高广、最充斥、最有用的。”西泰东道:“你为什么看不到实在的东西却总盯着虚无?在我看来,人世间最迷人的价值就是实用,最切近的念想就是成功,最现实的生活就是奋斗。所以,去做自己的主人,做勇往直前的勇士,做呼风唤雨的英雄。”“个人太过膨胀,利益私欲至上,这样的一堵墙岂非一推就倒?”“你的成功就是别人的参照,如此往复推动,大家都向前走,岂不就和谐共进了?”“这些最多可归于还算正统的术而已。”“我看德就是需求,你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最后人人各取所需,就是最高的人德境界了。”“高举欲利的大旗,一起走向道德的最高境界?这听起来倒新鲜,可那样所有的贪婪势必会公开一律地伪装成各种善举,最后还会搭建成一个没有照耀的国度。”西泰东嗤笑道:“儒以乱法,侠以犯禁。兄弟,你可是两样都占了,我又如何说的通你。”“可不兴这样攻击啊?好像我阴暗而又无德。”
西泰东摇摇头,嘴角挂着一丝轻蔑,“嘿,酒品到现在,味儿好像淡了。这种淡应该是你喜欢的?”我看着杯中酒道:“我以前是个酒鬼,现在很少再愿意喝醉,酒至半酣方好。”“你看起来不像是那种痛快淋漓的人呢。”“我想自己是,但可能我不想人人都是。”“嗛,那样说教给谁听?既不君子,也不道德。”“所以许多事是很难说的。道很精微很覆盖,理很具体也很尖锐。”“我劝你明天去教堂拜拜,说不定神会给你一个确定的指引,告诉你所谓的为政之道是什么。”
这里是“门福教堂”,夹杂在众多楼房间,很难找,少了太多的神秘威严。很明显,在这里,心灵的力量在不断外泄,世俗的泡沫在越吹越大,我与一个百无聊赖的修女聊了起来。
“你信吗?”我问,“当然。”她打个哈欠,看了看我,振作精神道:“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小帅哥?”“可是你好像很累。”“太闲了就会觉得累,不过你要有时间和兴趣,我会很快兴奋起来的。”我看她三十多岁模样,也算是略有姿色,便道:“我不谙世事,姐姐可不好骗我。”她伸出长袖拉了我的手,在厅中边走边介绍道:“这个是神仙,这个是神仙他妈,神仙们生孩子时都不用结婚的。你知道什么是处女、什么是结婚?”我想起那个长耳朵所讲处子怀孕的事来,忙岔开道:“处女?是楚楚动人的女子吧,像姐姐一样?”“小兄弟嘴真甜,姐带你去个更好玩隐秘的地方。”“你不会带我去极乐世界吧,我可没活够。”她竟抓了我的手在身上摸了几下道:“比极乐还乐。小弟弟难道是有备而来?太可人了。”我道:“我怎么越来越小,都成小弟弟了。”她嘻嘻笑道:“一会儿让小弟弟也找不着地儿。”
穿过一条长长幽深的地下走廊,来到一阴暗的屋门前,她划着一根火柴,门反锁着,拍拍门轻声道:“里面的快点!”透过门缝,见屋内亮着灯,四壁全是丰腴的裸体女人雕像,彩色的油漆剥落不少,床上锦绣被褥,两人正在那里酣战。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是天上人间。”“哦,那就是生死轮回的地方了?”“什么呀,我们不相信来生的,死后要么进天堂,要么下地狱。”“所以及时行乐?”她又拿我的手乱摸:“太对了。”我纳闷道:“拿我的手摸、你却那么有感觉,姐姐你境界真高。那你们就没有教规戒律?”“需求就是教规戒律。”“也没有神谕启示?”“需求就是神谕启示。”她紧紧拉着我,一面不耐烦地拍着门,我生气道:“又是需求,总是需求,需求是美、需求是道德、需求是神谕,需求比什么都万能,还费劲盖教堂这玩意干嘛!”“小弟弟,你别生气,他们一会儿就好了,我们的需求很快就会解决了。”“我很生气!这个无道无德的利雅坚府!”
转身欲走,却被那欲火烧身的修女缠住,先是磨磨蹭蹭地又拦又逗,后来竟不客气地一把朝我脉门捏来——这个小妮子竟然会功夫!我藏起了猫猫,她也惊讶道:“你会功夫!原来是个寻事的,看老娘今天不先奸后杀了你。”说完伸出尖尖的指甲抓了过来,猿跃蛇击,迅捷阴毒。灯灭了,我只能听音辨位,她却越打越快,无奈之下催发内力,大致点了她十几处穴道。
这时,门“吱呀”开了,一个女人出来埋怨道:“催命鬼,忒也着急!”我又点了她穴道,走进房间。里面一老头拉着我道:“恩人哪。我二十五岁时就被骗到这里,十年了,都榨干了还不放。”我盯着桌上一个奇怪的细竹筒,正要拿来,老头一把拔去竹盖道:“最后风流一次吧!年轻人,你的日子还长呢,我先来。”原来里面是****,看他一会又生龙活虎的样子,我忙退了出来。
(4)奈何桥
逃离艳窟,看着身边无数匆忙的陌生人,懊恼地回到住处。燕如见我落寞,笑道:“我陪你走走吧。咋刚来几天,我晕船的劲还没过去呢,你就没兴致了?”“这里看起来生机勃发,百业兴旺、也算自由自在,可我就是不喜欢。可能我老了,已经不是打拼的年龄了。如果你是那些年长失意的人,看着这个人欲横流、自私冷漠的地儿,会多难受啊。”“各顾各,AA制,有什么难受不难受的,什么都看不惯想不通,我都要以为你是假仁假义了。”我看了看她:“你们真是一个种子种出的豆,这么快就认自己人了。”“你怎么说话的?”“西门窦曾告诉过我,这里的祖宗叫西追,为瓯平府离家出走之人所建,你看也就百余年的光景,已经和瓯平府不相上下了。”“你这样满肚子怨气不好,谁也没欠着你钱。”欠钱无所谓,只是这没有关怀的地儿,怎么也不会舒畅了。”“慢慢找吧,你不熟悉。总不会一点没有。”
我决定继续东行,辞行的时候就西泰东他妈在,姬图道:“听说你不喜欢这里,能否听一听你的高见?”“什么高见,感觉而已,太闷了,不好玩。”“大家都在忙着办事,事业最重要,你年纪轻轻,也得早点做些事,或可成就一番功业。”“就是说没什么人情味嘛,骂仗打架了也没人劝。”“有法律呢。”“又是那冷冰冰的东西,它哪有亲戚朋友暖心啊。”“可它有效率,公平公正。”“无‘心’的法律,最多是阻止别人作恶,怎么保证公平公正了?大家都同样的待遇,这就叫公平公正了?”姬图吃惊地看着我不再言语。
往东来到一城堡前,我们遭到了卫兵烦琐的盘问,并且警告:出去容易,再要过来可就难了。我生气道:“为啥?难道这里是奈何桥不成?”“差不多。”“我没多大本事,可就不喜欢人激我,死也要充了这次英雄。”没行几里,来了一队人,蓬头垢面、赤脚裸怀,一个个被长绳系着,慢慢往西来。“他们什么人哪?”“本地人,都是比较健壮的,不知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原来西追一到这里就抢了人家的地儿,那个城堡就是目前大致的分界,先抢后建,省去不少工夫,难怪很快这么欣欣向荣。
再往东走,或遭驱赶、鞭打、掳掠、抢劫、焚烧,完全一幅文明人对落后族群野蛮欺凌与屠戮的画面,惨不忍睹。忽然就想起一件奇怪的事来:经常说我们宽州府文明富庶先进,却总是遭落后族群的攻夺占领、统御治理,好似一只硕大肥美的食草动物,面对一群狼,就算偶尔踩伤几只,但最终必然还是要走上被吞吃的命运。而其他如利雅坚府、瓯平府、梅庄,就是北地府、沙驼府、向原府,也最终都是文明人在那里抿着嘴阴笑。真是天理何在!
对此我想了很多原因,比如自大满足、少了意愿,贪腐惰懒、送人机会,仁德守礼、又多了一层束缚,甚至是是帝国已老,本性上已没有那种咄咄逼人、先声夺人的气魄等。但半年以后我就不那样想了,很明显,这与我们的为政之“道”有关系,我们把阴阳、先后、矛盾、你我等都看成是自然的状态,别人却非要把它们看成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东西。所以我们两端持中,中庸平和,总喜欢在自己锅里搅和,别人则两端外向,扩张激进,习惯于往别处找平衡。可见道不喜人!我们在心理上先输了,自己遵道而行,中规中矩,别人却不理道的事,量力而行,不断试探刺激,就把我们打翻马下了。
燕如问:“这是到哪里去?我们真的要往阴间赶?渗得慌。”我笑笑:“阴间指不定比人间还好些呢。赶快离开这儿,好赖找个清静点的地方。”我担心她肚子受不了,凭着记忆,做了叶明发明的那种小飞车,推着燕如飞快地跑了起来。燕如站上面扶着,看残阳如血、流霞飞渡,听山风树吟、泉响河鸣,长发飘舞、浅笑遐思,立时一个烂漫的如花美眷,又开始了她心灵安宁的课业。忽然想起我们常家镇有一女红坊间,起名“浅秋”,对照时下情景,倒是绝佳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