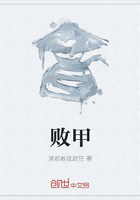(1)西泰东
自此,便少有人再来打扰,盛夏炎炎,总令人昏昏欲睡,我俩又亲密起来,乐不思蜀。这天,燕如感觉身体不适,我忙去找大夫,听他搭过脉道:“咦,今天看的两人真是有趣,一个是女圣人,有孕已经八个月,看身子却仍如处子一般。你这个武圣人也有喜三个月了,而且像是双胞胎。”我看燕如脸色瞬息万变,忙打发他走,警告他勿要声张,燕如偎我怀里,半响轻声埋怨道:“你呀你!”
忽然听得一声咳嗽,是封秀来了:“真不知怎么开口,利雅坚府来人了,说是要做生意,可我们不想卖的东西,他们还是逼着买走,你说这叫什么事嘛。”我道:“那不就是你们在周山镇做的那些事吗,咋又觉得不妥了?”“嗨,不爽不说,还断了几个望族的财路,大家都很愤慨,可他们人高马大,船坚炮利,又都会点武功,惹不起啊。”“多少家望族啊?”“主要有封家、慕家、傅家三家。现在最着急的是慕家,原本是想借有德大帝挣些好处,双手奉上耀敛观,谁知被牛大侠你一撸精光,有德大帝又经常向他开口要这要那,本已难以为继,利雅坚府一来,他立时便受不了,要去拼命。”“那跟你什么关系?你不可以趁机抢了他的地盘吗?”“嗨,不瞒你说,他好对付,要利雅坚府的人不走,才真没什么好招了。”我点头道:“你心思挺深嘛,这儿吃喝这长时间了,去就去吧。”
利雅坚府来了十五六条船共两千人,我问封秀:“你们交过手吗?还没,不过大家心虚,自己家里,打的一塌糊涂,今后怕是无法立足了。”“有德大帝没什么指点啊。”“没有,我现在才知道他是只老狐狸,暗中与慕家串通一处,想对我们几家不利,却让大侠把他的尖牙利齿打掉了。他现在依旧一心想要重塑威望,正等我们谁出错了好借机掳他手底下做事。”我越听越生气,他们自己的事,却一个个龟缩到后面,生怕伤筋动骨,却叫声“大侠”就把我个不相干的小天真忽悠到前台作挡箭牌,不禁萌生了去意。
快到湖边了,见树林里一利雅坚府的人在练武,挥舞着长长的宝剑,身边落了一地的枝叶,兀自在那里哼哼哈嘿,正要前去招呼,树荫下一喝茶的人道:“咳,先生,请不要打扰他。”我走近问:“他在干什么?”“在治病。”“他疯了吗?”“还没有。”“你在干什么?”“我在喝茶,一边看他会不会疯。”我笑了,看看封秀又问:“你们为什么来这里?”“老板想做生意,派我们先来探路,看什么生意好做。”我也坐下,与他攀谈起来。
他叫西泰东,二十出头,见了西门燕如,过去拉住她手,一嘴叮上便迟迟不肯松口,一双贼眼在下面滴溜溜不知往哪里转,把个封秀恨的握紧了拳头,我拍拍他肩膀,递过去我的手道:“这里又不是她一个人,我手痒,你也给舔舔?”西泰东道:“兄弟我在这个大湖里乱撞了三个月,你看那个砍树的都快疯了,又见如此美女,失礼之处还请谅解。”我道:“有人说你们奸淫掳掠,这个总不会请人家多多谅解了吧?”“什么呀,没有的事。要有,还用得着不停砍树吗?”“你砍个树还这多理?”“救人一命,他们行了善、受了损失,我们可以赔他钱嘛。”“人家又不缺钱,你赔树吧?啥时候长高了再回去。”“你想玩我?”“你好玩吗?怕你也憋出病了,所以陪你多说几句而已。其他人呢?”“采购去了。再缓几天就走了。”“回去吗?又要三个月?”“不,路探清了,一个月足够了。”“那你们还来吗?”“来,再不来我探什么路!”“你是头儿吗?”“什么事?请吃饭吗?”“请啊。一般的头儿都很有风度。”“最好是再来点酒,那就更有风度了。”“看来我们有缘。”
西门燕如自怀孕后,天天像只慵懒而发情的母狮子,总喜欢偎着我,还不时拿头和脖子蹭过来,她才不管有人没人,把个西泰东看得难过到要死要活,我同情道:“走,哥带你去个合适的地儿消遣消遣。”燕如忽然跃起,一脚朝我屁股踢去,我还踉跄未稳,就又用剑身拍了过来,我屁股麻酥酥的,忙喊停,她竟又向我脸上拍来,我不敢还手,将左掌挡脸上,掌心却着了狠狠的一记,那声音,响得几里外都能听见,疼得我一边跳,一边结巴道:“带,带你一块,一块去!”西泰东吐吐舌头,估计对燕如是任何想法也不会再有了。
就在灌顶寺后面半里处,有一温泉,是梅庄男女常去泡洗的地方,凭西泰东的年轻壮美,肯定有本事带出几个去快活。恰逢陆前开讲儒学,我与燕如便听了起来:还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容,比之前在白鹿洞讲得更过激,他把天理直接归结到“大德”二字就再也不予理会,也不说大德是什么,便开始对人欲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唾沫乱飞、张牙舞爪,声音尖锐,神情峻冷,远远看去,就似一个带着传染病毒的干瘦魔鬼。
想那时我大哥极力要我去白鹿洞书院,说是程先生以经入理、以事入理,既贯通圣人经典,又格物致知,形成理学,堪称新圣。对比程前之前他所讲更冷静一些的东西,他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理”入“心”了,理是心之理,心是神之心,心成了与神并列的大主宰。想想学问这东西真是奇怪,哪一理只要深入贯通了,就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闭合的体系,这个陆前的心学也是自成一体,并不容易找出什么前矛后盾的明显谬误,其心学竟似平添一层神秘面纱,乍听好像还比理学高一层次似的,让人捉摸不透。
看燕如神情痴迷,不知是听得入神,还是在想其他事情,我碰碰她:“你信吗?”“有什么信不信的,听听而已,听不懂,不过感觉好像有点道理似的。”“你可别信他的,人生在世,讲的主要是在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完备身心,而不是光说别人不理会自己,义理不辨,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你再看那老头,好色、偏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燕如道:“就你好!别烦我!”说完还拿柳枝打了过来。我转身去找西泰东,心想,我虽言语过头、着急失仪,但你也不能好坏不分啊,这婆娘,不能再让她呆这里了,赶明儿中毒了,把谋害亲夫当作是大义灭亲,叫我多下不来台!
(2)惊起一滩鸥鹭
西泰东正乐不可支,也顾不上找个僻静点的地方,就地开战,动静还忒大,估计陆前那里都能听得见,更奇的是,他跟前竟然还有另外两个女子在聚精会神地观摩!我放大脚步声,没有反应,咳嗽一声,淹没在呻吟中,拿石子打他屁股,他一边揉揉一边继续忙活,我低声道:“小兄弟,悠着点,来人了!”西泰东忙里偷闲地瞥我一眼:“那位老虎姐姐没来?你也过来玩会儿吧?女人,太厉害就没味了!”妈的,我可怜他,他却把我和燕如想成什么人了?与我说着话,还舍不得停了那套机械运动,真是无礼之极,不禁怒道:“闭嘴!”谁知道无意中突然加大声音,惊动了许多认真办好事的人:不少人光着身子朝我这边走来,看是什么事,前面陆前也停止了讲授,最糟糕的是燕如拿着柳枝追过来,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
我四处逃窜,又惊吓到不少人,结果大家乱作一团,纷纷四散,几对男女赤身奔往老先生的神圣讲坛。陆前见我经过,一声怒吼:“逆徒!又是你!竟敢让老夫闭嘴?!”台下有人喊:“打死他!!!”真是众怒难犯,我仓皇往住处逃去,燕如一会就跟不上了,站那里捂着肚子。我过去扶她,她生气地甩开我的手:“你呀!咋忽然变得这么没素质呢!”
我无言以对,燕如又想靠着我,却让我背过身,只留她个肩膀后背,忽听她道:“走!你个禽兽!这里没你呆的地儿!”一回头,原来是西泰东过来了,笑嘻嘻地抱拳道:“你老公做错事了却来怨我。”“他不是我老公!”西泰东耐心地又拱手道:“是你男人做错事了却来怨我。”燕如不语,这时梅日也来了:“是你错了,牛公子!”我辩解道:“这个年轻人就在讲坛百余丈远的地方办那些丑事,还对我出言侮辱,我让他闭嘴,有什么错了!”“你声若洪钟,就算不是有意,也已触怒神灵,不是错是什么!”
封秀喘着气儿跑来:“这里已被围,现群情激奋,怎么办?”就“闭嘴”两个字,霎时间变成了一桩亵渎神灵的大事,我生气道:“你们是说他们想怎么办就打算让怎么办我了?”梅日阴阳着脸:“有三个办法,一是你当我们的武圣人,你女人是武圣夫人;二是找个地儿躲起来,众怒平息后再做打算,但需多长时间不好说;再就是离开。”我笑笑:“离开就离开吧,不过你们啥时候知道我俩的事了?”封秀嘟囔道:“他女人?”梅日道:“没想到你这么不待见我们。”“我不过是个野散的闲人,呆这里难免又要冲撞了你。”西泰东一旁道:“如有闲暇,何不去我们利雅坚府玩?”我看看西门燕如,见她挽着我的臂膊,却又别过脸去不理我。
梅日又客气一句就走了,封秀领着我们,走了他家丁围堵的那一边,燕如不知道生哪里的气,又偷偷踢我两脚。临上船了,封秀似有不舍,恭敬地行礼道:“丰神公子,尊夫人真姓实名可否见告?”我道:“她叫打人,成我女人后就随了我姓,叫常打人。”燕如白我一眼道:“全世界就你能,会开玩笑。别搭理那个没品位还自以为是的家伙,我叫西门燕如,多谢封先生盛情!”我看见封秀的眼里竟像有泪珠盘桓,不觉脱口道:“你不喜欢男的吗?”“啪”一声清脆的耳光,燕如下手好重,我的脸竟肿了起来,封秀低着头道:“她是我心中的美神,我不知男女。抱歉!告辞!”我愤怒地想,不知男女?妈的,难不成还要当面脱衣服验证了?!
这个封秀,临走了,突然表现得比我境界高了许多,或许是比我更会拍马屁?越想越气,对燕如道:“你打人也得分个场合吧?!非得把你男人打懵了、打傻了,像头站着的肉猪一样让你牵着到处走才好啊?”“谁让你乱说话,打你脸省得你烂嘴巴。”“那你也下手太重了吧?万一把你手打疼了!”燕如笑道:“打疼你怎么了,你又没少什么东西。”“是没少,倒是多了。肿这高!”她摸着我的脸,心疼地钻我怀里道:“谁知道你这么不经打。”想想她就是与我相好之前那个遗世独立、凛然不可侵犯的女神,突然生出一丝感动,抱起她道:“美神,以后咱打轻点,好吧?”燕如嫣然一笑,绝对一个初为人妇的风情少妇,媚笑道:“那还不如不打呢。”“嗯?你真好。可得说到做到!”
水上的日子真无聊,然而燕如好像很享受这种遐思。我问:“你想什么了?”“什么也没想。”“那你怎么老是在想的样子?”“好像有我这个人,好像我又在自己对面站着,不知道是想了还是没想,一会我是一个,一会我是两个。”“就不想想我?”“有时候想你比看你好,有时候看你比想你好,最有意思的就是现在,你在我跟前,我却可以静静地想你。”“我不相信。我天天戳你眼前,还有什么好想的。”“有时我看你的时候好像看见的是想象中的你,想你的时候你却比现在还清晰。”“这么复杂?你写诗吗?”“以前写过许多,自从与杰哥相识后再也没写过。”“那是,光快活呢,哪顾得上。你年轻时很漂亮吧?”“你这人哪,就这张嘴有时很讨厌。不过我那时倒真没现在好看,病怏怏的,就知道写几句诗,把男人都看得忒俗,谁知道最后还是跟个俗人,后来遇见你,终于重又像个饮食男女了吧,你却又越来越俗不可耐。总的来讲男人都是骗人的。”“男人确实比女人俗。特别在感情方面更是这样。能念两句你的诗吗?”“那次找向柳时去了我曾经的闺房,发现好多,烧之前又看了一遍,都很酸。倒是记得几句,怕你又妄加评论。”“不敢,好想聆听。”
燕如支起尖下巴颏儿,长长的眼睫毛忽闪几下道:“我是你忧郁泪水池沼,生养的白莲未开,风也不送来,太偶然的相遇,露珠不停住沉沦,滴去心思一许,泥浆里美艳的身体,让岸上的石头白到心慌。”我想笑,也很惊讶:“你的诗确实与众不同,却照样很美,你说美是什么东西?这么奇怪。”“那怎么说呢,美肯定有很多种嘛。”“可什么最美?”“这是很世俗的想法,问的很不美。”“你说大家为什么不去追逐美,却老是盯着权、利、欲,还高高兴兴地在里边闷死自己?”“欲望有时候也很美。你想啊,要是没有欲望,还能有美吗?”“那也不能把产生美的东西都说成是美,就比如烂泥塘,生了荷花,但你能说它美吗?”“欲望比较正当、自然和纯粹的时候会不美?”“而且是隐藏很深的那种美吗?我都准备赞同你了。”
“我赞同。”西泰东道:“需求就是美。你需要,你想了,就是不美也会让你想得很美。”燕如扭过头,我道:“你很实用啊。照你说是需求产生欲望,欲望产生美。”“你想的太拐了,需求就是美。”“那有什么可美的?得给它涂脂抹粉了,才会隐约看出点美吧?”燕如笑了道:“对了,需求很多时候并不美,但给它糊上一层又一层赏心悦目的想象,再加上心底的那个欲望就伪装成美了。”西泰东道:“需求就是美,用得着伪装嘛!”说着扔过来一坛酒:“你说它不美就扔进湖里吧,说不定鱼儿会看着它美。”三人一齐笑了。酒不错,是梅庄人的那种勾兑些蜜啊、花啊、果啊什么的,很香很浓艳,像个重口味的盛装歌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