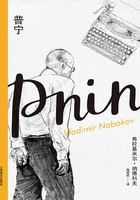斯奈费尔火山高5000英尺。它的双峰位于由粗面岩构成的海岸的顶端,这条粗面岩石带和冰岛的山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座山峰衬托在灰色的天空中,我看到的只是压在巨人额头上的一顶大雪帽。
我们排成一条直线行进,向导走在最前面,他在山路上攀登着,这条路很狭窄,两个人不能并肩通行,所以大家无法进行交谈。
在斯塔比的玄武岩壁的另一边,首先出现的是一种草质纤维性的泥炭组成的土壤,这是从前冰岛沼泽地上古代植物的遗迹。这些尚未开发的燃料总量,足以供冰岛的全部人口取暖100年。要是从某些山谷的底部开始丈量,这片广阔的泥炭层足有70英尺深,并且接连含有好几层被大块浮石或凝灰岩隔开的炭化岩屑层。
作为黎登布洛克教授的亲侄子,尽管我心事重重,但还是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展现在这个巨大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矿物珍品。我一边观察,一边在脑海中浮现整个冰岛的地质史。
这座奇特的岛屿显然是在一个不大久远的时期从水底冒出来的,也许它现在仍在让人不易察觉的上升中。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必然是地下火山运动的结果。那么,亨夫利·戴维的理论、萨克努塞姆的密码文件,以及我叔叔的看法也都化为泡影。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我仔细地观察地表的性质,很快明白了在这个岛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主要现象。
冰岛没有沉积土,完全由火山凝灰岩构成,也就是说是由一大堆石块和多孔岩石堆成的。火山爆发之前,它只是一大块绿石,受地球内力的推动而慢慢浮出水面。这时,地心的岩浆还没有喷发出来。
但是慢慢地从岛的西南至东北出现了一条横贯全岛的大裂缝,岩浆就从这条裂缝慢慢溢了出来,因此没有发生剧烈的爆炸,然而后果却是很惊人的。这些岩浆慢慢地四溢,有些形成广阔的平面,有些则高高地隆起。这个时期出现了长石、正长岩和斑岩。
由于岩浆的漫溢,岛的地层就大大地加厚了,它的抗力也随之增强。溢出的岩浆冷却后结成一道硬壳,并且将那条裂缝封住了,于是大量的岩浆积聚在地表下面。地心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地心的大气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使地壳逐渐隆起,进而形成许多火山管。于是,岩浆通过这些管道,冲破了岩层,很快就在山顶形成了火山口。
从此,岩浆漫溢被火山爆发所替代。开始时,从刚形成的火山口中喷出的是玄武岩浆,现在我们正在穿过的这片平原就是玄武岩平原的最佳典范。我们行走在这些沉重的深灰色岩石上,它们在冷却的过程中都变成了六边形棱柱。远处还能看到许多平顶的山峰,它们从前都是火山的喷口。
当玄武岩浆喷射完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熔岩、凝灰岩和火山岩渣。它们在火山上留下了一条条长痕,仿佛一簇簇浓密的头发。
这就是冰岛在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它们都是由地球内部的热能所引起的。有关地球内部不是一团灼热流体的言论都是谬论,要想到地心去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所以虽然我正朝着斯奈费尔火山进发,但我心里却感到很安慰,因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路变得越来越难走,地面变得越来越陡,一些碎石子噼里啪啦地滚落下来,我们必须很小心才能避开这些危险的坠落物。
汉斯像走在平地上一样平稳地前进着,有时他会突然消失在一块巨石后面,暂时离开我们的视野,这个时候他就会发出一阵尖锐的口哨,为我们指引方向。他还会时常停下来捡些石子,把它们摆成显眼的标记,以便帮助我们指明回来的路。这本身确实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办法,但在过后看来,毫无意义。
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后,我们才来到了火山脚下。汉斯做手势示意我们停下来,大家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我叔叔为了赶时间,吃饭的速度比平时快了一倍。但是吃饭主要是为了休息,所以他不得不等待。直到一个小时后,汉斯才愉快地挥手让我们继续前进。另外三个冰岛人和汉斯一样沉默寡言,而且他们吃饭很有节制。
我们开始攀登斯奈费尔的山坡,人在山中很容易产生错觉,看起来火山的雪峰明明近在咫尺,但要接近它,却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跋涉!那些石子既不依附在泥土上,也不跟野草依附在一起,而是不断地在我们脚下坠落,以雪崩一样的速度冲落到下面的草原上。
在这座山的某些地方,山坡和地平线所形成的角度至少有36°,根本不可能攀登上去,只好沿着边缘上那些陡峭的石子路艰难地爬上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借助铁棒,互相帮助。
应该说,我叔叔一直在尽量地靠近我,不时地关注着我,他的手臂好几次都给了我有力的支持。至于他自己,本生就具有良好平衡感的天赋,因为他从来没有摔倒过。那三个冰岛人尽管身上背负着很重的行李,但他们以山里人特有的敏捷往上爬着。
我远眺斯奈费尔那高高的山峰,觉得我们不太可能从山的这一侧爬上去,除非山坡不像现在这样陡峭。幸运的是,经过一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在覆盖到山腰处的一大片积雪中间,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一条梯级状的小路,这让我们的攀登省了不少力。这条小路显然是由于火山喷发出的熔岩流形成的,当地人称它为“斯蒂纳”。如果这条奔流的熔岩没有被山坡的地形所阻挡,那么它就有可能会直奔大海而去,形成新的岛屿。
这条小路帮了我们大忙。山坡更加陡峭了,可这些台阶却让我们的攀登变得轻松许多,甚至当别人在向上爬的时候,只要我稍稍停顿一小会儿,就会被落下很远,眼看着他们变得越来越小。
晚上7点,我们已经爬了2000级台阶,正站在一块突出的平台上,斯奈费尔的火山锥就耸立在这个平台之上。
在我们脚下3200英尺的地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我们已经越过雪线,不过这里的雪线并不算太高,主要是冰岛的气候常年湿润的缘故。天气十分寒冷,而且刮着大风。我已经累到不行,教授看见我那不听使唤的双腿,无论他有多着急,都决定要停下来。他做手势给向导,让他停一停,可后者却摇摇头,说:“上去!”
“看来我们还得上去些。”我叔叔说。
然后他问汉斯原因。
“大风。”向导回答。
“对的,大风。”另一个冰岛人带着恐惧的口吻重复了一遍。
“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急切地问道。
“你看。”我叔叔说。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朝平原看去,只见一道夹杂着碎浮石、沙子和尘土的气流柱像龙卷风那样旋转上升着,风在把它吹向斯奈费尔的山坡,正好就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气流柱就像一块不透明的屏风挡在太阳前面,在山上投下巨大的阴影。如果这个气流柱向我们这边吹过来,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当冰川上吹起大风的时候,冰岛人就称这种现象为“大风”。
“快跟上,快跟上。”向导喊道。
尽管我不懂丹麦语,也知道这是要我们尽快地跟着汉斯。向导开始往火山锥的后面爬,迂回地前进,这样上去比较容易。没多久,龙卷风就降临在山上,在它的撞击下,整座山都在颤抖。被旋风卷起的石子像雨点一样漫天飞舞。我们幸运地躲在了山坡的背面,因此没有遭遇危险。如果不是向导的细心,我们会被打得血肉模糊,碾成粉末,像颗不知名的陨石被抛落在很远的地方。
汉斯认为我们在火山锥的斜坡上过夜很危险。于是我们继续迂回地向上攀登,又花了近五个小时才爬完了剩下的1500英尺。不算那些迂回走的路,我们至少也走了9英里。我饥寒交迫,实在走不动了。稀薄的空气让我闷得发慌。
晚上11点,我们在黑暗中终于抵达了斯奈费尔的山顶,在进入火山口过夜前,我还能看到午夜的太阳落在最低点上,把它那暗淡的阳光洒在我脚下这个沉睡的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