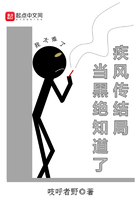去很快地吃完晚饭后,我们几个人尽量安顿好了自己。那是在海拔5000英尺的高度上,地面很硬,可以供我们歇脚的地方也不够大,条件十分糟糕。但在那个晚上我却睡得特别香,是这段时间以来睡眠质量最好的一次,甚至没有做梦。
第二天,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几乎被那凛冽的寒风吹得冻僵了,但阳光却很灿烂。
我从花岗石的床上爬起来,跑出去享受宏伟壮观的美丽景色。
我站在斯奈费尔南峰的顶端。从这里可以俯瞰岛屿的大部分地区。就像在其他地方登高俯瞰一样,海岸线看上去显得更高些,而岛屿的中央部分则好像陷了下去。这幅景色在任何人眼中都会说我脚下的是赫尔勃斯墨的模型地图。我看到深邃的山谷纵横交错,悬崖仿佛一口口刚刚挖掘出来的深井,湖泊如同水塘,河流宛若溪流。在我的右面,延绵着数不清的冰川和山峰,有些山峰被轻烟缭绕着。那无边无际的山峦高低起伏,山顶的积雪如同白色的泡沫一般,让我想起了波涛汹涌的海面。再向西看,无垠的大海延伸到远方,无比壮观,仿佛与泛着泡沫的山峰接连在了一起,无法分辨出哪里是陆地的尽头,哪里是泡沫的起始点。
我陶醉在高山之巅那波澜壮阔的奇景之中,这次我没有头晕眼花,因为我终于习惯了这样俯瞰。我被迷得昏花的眼睛沐浴在通体透亮的太阳光线里,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身处何地,我好像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风神、水神和土神。我暂时遗忘了不久后将要进入的深渊,完全沉醉在高度带来的快感中。我叔叔和汉斯也爬上了山顶,他们的到来把我拉回现实中。
我叔叔面朝西面,用手指着一缕轻烟、一片雾气,或是海岸线一个暗淡的陆地轮廓。
“格陵兰岛。”他说。
“格陵兰岛?”我喊道。
“是的,我们距离那里只有105英里,冰雪融化的时候,北极熊会待在漂流的冰上,从北极漂到冰岛来。不过这不重要。我们现在是在斯奈费尔的顶上,这里有两座山峰,一座在南面,另一座在北面。汉斯会告诉我们冰岛人管我们脚下这座山峰叫什么名字。”
问题刚被提出,向导就回答:“斯卡尔塔里斯峰。”
我叔叔得意洋洋地瞟了我一眼。
“到火山口去!”他说。
斯奈费尔的火山口就像个倒着的圆锥,开口处的直径长达1英里以上。我估计它有约2000英里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容器充满了雷电和火焰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圆锥体底部的周长不会超过500英里,所以它的坡度很缓,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下到下面去。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把大喇叭似的大口径火枪,这个想法令我毛骨悚然。
多么疯狂,我想,从火枪口里进去,如果它正好装着子弹,只需要轻轻一碰,我们就会被打出来。
可我不能回头。汉斯已经面无表情地走到了队伍的前面。我跟在后面,一语不发。
为了便于下去,汉斯带领我们在圆锥内壁上沿着一条长长的圆弧线前进。我们走在火山喷发出的岩石中间,由于洞口受到震动,有些岩石弹跳着坠入深渊,发出异常响亮的回声。
圆锥内壁的某些部分的确存在冰川,所以汉斯在越过这些冰层时总是极为小心,他会先用他的铁棒探测地面,看看是否有裂口。在一些可疑的地方,我们不得不用一根长绳把彼此连在一起,这样万一我们中间有人一脚踏空跌了下去,其他同伴就可以把他拉住。当然,这个办法只是出于谨慎考虑,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从这条汉斯自己也不太熟悉的斜坡下去,虽然十分艰难,但我们总算没有发生任何意外,除了一个冰岛人手中滑落的那一捆绳索,它以最短的路程掉到了深渊的底部。
我们终于在中午到达了目的地。我抬起头,望着圆锥上面的洞口,这个洞口划出了一块被缩减得极小的、圆得几乎完美无缺的天空。在这个天空的一点上,高耸入云的斯卡尔塔里斯峰清晰地显露出来。
火山口的底部出现了三条火山管,斯奈费尔火山爆发的时候,地心的熔炉就是通过这些火山管把熔岩和蒸汽喷射出来的。这些火山管的某些位置的直径大约有100英尺宽,它们在我们的脚下张着大口,我没勇气往里面看。黎登布洛克教授马上迅速地依次检查了它们的位置,他一面气喘吁吁地从一条火山管冲向另一条火山管,一面手舞足蹈地喃喃自语,但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些什么。汉斯和他的同伴坐在一排排的岩石上看着他,他们显然把我叔叔看成了个疯子。
忽然,我叔叔发出一声尖叫,我以为他失足掉进了某条火山管中,然而没有,我看见他正张开双臂,分开着双腿,笔直地站在火山口中间的一块花岗石上面,这块花岗石仿佛是死神雕像的庞大基座。他保持着这种姿势,表情看上去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可是不久,这种茫然很快转变成难以言喻的欢乐。
“阿克赛尔!阿克赛尔!”他喊道,“来,快过来!”
我赶紧跑过去。汉斯和那几个冰岛人都无动于衷。
“你看。”教授对我说道。
跟教授一样,我不知道该说自己是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惊讶,我在岩石西面的那一侧看到了几个卢尼文字,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已经被剥蚀了,它们就是那个被我诅咒了无数次的名字:
“阿尔纳·萨克努塞姆!”我叔叔喊道,“你现在还有什么要怀疑的吗?”
我心慌意乱地回到刚才坐着的熔岩上,没有回答他,我的脑子里全是这个证据。
我也不知道自己思考了多久。我只知道当我抬起头来时,就看见我叔叔和汉斯站在火山口的底部。三个冰岛人已被辞退,他们此时正沿着斯奈费尔外侧的山坡向下走,朝斯塔比方向走去。
汉斯在一块岩石脚下的熔岩流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床铺,他安详地睡在那儿,我叔叔在火山口的底部转悠,就像是一头掉进陷阱被捕兽器困住的野兽。我既不打算起来,也没有力气起来,我效仿向导,沉迷在无可奈何的昏睡之中,蒙眬中隐约听到一阵声响,并且感觉整个山似乎都在震动。
火山口底部的第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厚厚的乌云低低地压在圆锥顶上,天色阴沉。我会注意到天气,并不是因为山口里面一片漆黑,而是因为我叔叔的大喊大叫。
我很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因此我心里顿时又萌生一线希望。
在我们脚下的三条火山管中,有一条是萨克努塞姆走过的。根据这位聪明的冰岛学者在密码文件中所作的指示,要想知道哪一条才是正确的火山管,只有在6月的最后几天,看斯卡尔塔里斯的阴影投射在哪一条火山管的边缘。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座山峰看成一个巨大日晷的指针,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指针的阴影就会指出通往地心的道路。
目前,如果不出太阳就不会有影子,也就不会有阴影,更不会有所谓的指示了。今天是6月25日。如果天空再这样连续阴暗五天,我们的观察就要推迟到下一年。
我不想描述黎登布洛克教授那种无能为力的愤怒。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可是火山口底部仍然没有阴影出现,汉斯一直待在他自己的床上,他要是有哪怕一丁点好奇心的话,一定会猜测我们一直在这里等什么!我叔叔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他的视线总是向着天空,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远处。
26日,还是不见太阳,反而整整一天都是冰夹雪天气。汉斯用几块熔岩盖了一间小屋。看着成百上千条临时形成的小瀑布沿着圆锥边缘往下流淌倒也有趣,每当这些瀑布打在一块石头上,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我叔叔几乎忍无可忍了。就算是最有耐心的人也会被这种天气惹恼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功亏一篑。
然而,神往往爱把大悲大喜交集在一起,这一次他要给黎登布洛克教授的惊喜,绝不亚于其在绝望时的苦恼。
第二天,天空依然乌云密布,可是到了6月28日,星期日,也就是这个月的倒数第三天,月亮起了变化,天气也随之变了。大量的阳光洒进了火山口,每一座山头、每一块岩石、每一块石头,每一个突出的表面都在分享着和暖的阳光,并且把它们自己的影子投射在地上。最重要的是,斯卡尔塔里斯峰那尖尖的棱角也出现了,它的阴影和光芒四射的太阳一起慢慢地挪动着。
我叔叔也在追随着阴影一起转动。
中午,当影子最短的时候,它轻柔地舔着中间那条火山管的洞口边缘。
“就在那里!”教授喊道,“就是这里!通往地心的路!”他又用丹麦语补充了一句。
我看着汉斯。
“前进!”向导平静地说。
“前进!”我叔叔回答。
这时候是下午13时1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