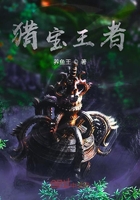‘普渡寺’是洛州城东最大的寺庙,一年一度的庙会总能吸引洛州城内素爱热闹的男女老少,今日盛况依旧,别说寺庙里头,就是寺外的几里长街也是满眼彩绸高挂,集市也比往日里热闹不少。
劭仪与陈秀菁走在前头、梁沛千走在两人身后,他的身后则跟着香雪,倚翠及成拓,一行六人,边走边瞧,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往“普渡寺”方向走去。
六人一进庙里,只见里头人山人海,各种祈愿问卦的小摊依墙靠树,满排而开,另有一些摊位卖着各种开运转运的器物,摊前人头拥挤。
劭仪对五人提仪道:“人多易失散,若走散了,未时在这儿等着汇合。”众人赞成。
香雪与倚翠两人这摊看看那摊摸摸,不亦乐乎,成拓边两眼扫看边紧跟着梁沛千,劭仪边逛边照看着秀菁,秀菁时不时回头找梁沛千的身影,而梁沛千十足悠闲地游览,亦能游刃有余地在穿梭往来的人群中与劭仪和秀菁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
秀菁正在一个摊前观玩转运风车,劭仪站在一旁半举着风车吹了吹,彩色风车呼啦啦转动起来,透过风车彩页,劭仪目光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却是一个不可能出现在这的人。
她轻拧了拧眉,思忖一瞬,回头找了下梁沛千的身影,然后对正颇有兴致挑拣把玩的秀菁道:“在这等一会儿,别走开。”
秀菁点头。
劭仪挤到梁沛千处,指了指隔着人群不远处的秀菁道:“我有点事,秀菁交给你照顾下。”说完便朝另一个方向急急而去。
梁沛千看了眼秀菁,又看了眼即要隐没于人群的劭仪的背影,伸手迅速拉过成拓,道:“照顾好秀菁!”说罢身子已向着劭仪消失的方向疾往而去。
劭仪绕了大半个圈,却是再没看见方才的身影,难道真是眼花看错?她自嘲一笑,娉婷姑娘怎么可能在这。
停步往四周看了看,已是寻不到其他五人,罢了,到时庙前汇合便好。
她慢步缓踱,自顾自地逛了起来,不经意间走过寺庙角落处的一棵大树,只见低矮些的枝权上已缚满红色纸笺,树下只有一个白须老人闭眼坐在一个方桌之后,桌上整齐地放着几叠长条状的红笺纸,旁边一只盆钵。
劭仪有些好奇问道:“老先生,您这生意怎么做?”
老人仍闭着眼,右手微抬道:“姑娘请坐。”
劭仪坐于方桌前,老人道:“老夫身后的是许愿树,姑娘在红笺之上写下愿望,缚在树上即可。”
“纸笺多少银子一张?”
老人笑道:“愿给多少便是多少。”
劭仪一愣,这老先生倒是有趣,她看了眼那盆钵里零星几枚铜板,心想,难怪树上满、钵内空。
“您就不怕亏了本?”
“姑娘放心,亏不了。”
劭仪讶异于他的笃信,却也不再多说,她本是好奇而来,如今不许个愿倒有些说不过去,许愿之事本也只是心内一个寄托,此时她已身在家中,惟一心有挂牵的便是远在益州书院的师傅,李玦,和徐朔。
她开口道:“我要三张笺纸。”
“姑娘请便。”
劭仪边写边问:“恕我冒昧,您的眼睛……?”
老人面带笑容道:“老夫这双眼睛只看它自己想看的,便是老夫自己也做不得主啊~”
劭仪笑了笑,只觉他说的话奇怪,倒也没多想,她写好纸笺,掏出一锭银子欲往盆钵内放,转念一想,他若真看不见,银子让坏心眼的拿了去,可不妥,于是直接塞进了老人手里,然后走到树下去了,没有瞧见老人睁开了睿智明亮的双眼,捋着胡须看着她。
劭仪缚完两张,已是再无空隙可挤,只得去寻个高一些的枝头。
梁沛千兜兜转转了好一会,就是不见劭仪的影子,这会儿也绕到了这树下,只欲乘个凉,歇一歇,劭仪抬着头在枝隙间寻找合适之处,连退了几步不料撞上了人,相撞的两人蓦然回首之间俱是一愣,“劭仪?!”“梁公子?!”两人惊讶过后只是默然相视,气氛怪异。
梁沛千扬了扬唇,先开口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劭仪边开始缚纸笺边回道:“系许愿笺。”
梁沛千看她就快踮直了脚尖,却仍是够它不着,无奈走过去,在她身后接过她手中纸笺,笑着道:“让我来吧,我为何每次都能遇上你探高不得的时候。”
劭仪看着他小心翼翼系纸笺的样子,心里浮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是无法言喻的微甜。
红色纸笺之上是她写的娟娟墨字,梁沛千避无可避也不想避地看了个大概,“愿李玦一切安好……”李玦……是谁?似是个男子的名字,他的心里竟也浮上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却是无法言喻的酸涩,这算怎么回事?
两人欲离开时,白须老人在背后唤道:“姑娘请留步。”
劭仪转身后不由意外,原来他并不盲,她与梁沛千步至老人面前,只听老人道:“我与你之间的缘,今日来今日去,只留你两句话。姑娘,你即将遭遇一场难避之劫,不过,务必记住,'是劫是缘难分辨,苦尽甘来雲中见'。”说完老人又闭上了眼睛。
劭仪心里琢磨一遍,最终只是一笑置之,梁沛千倒是上了心,两人离开笺摊后,他见劭仪已将方才之事抛诸脑后,有些不放心地问道:“他说你在劫难避,你不想知道是何劫难?”
劭仪诧异道:“你怎还在想此事?”
梁沛千苦笑不答,自己本不信神卦之事,现关乎于她,竟不自主地在意起来。
劭仪不知他所想,只淡淡地解释道:“若是高人之意,本就难悟,若是胡诌之言,则不必在意,说来说去就是让你我不必费神思量了。”说罢朝他莞尔一笑。
梁沛千无奈,她的话为何听来总是这般有理?
劭仪从庙会回到“沐岚院”时,申时已过,她回到屋里便开始给孔裕和李玦写信,回洛州后发生了太多事,竟未曾得闲问候他们,她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正如今日纸笺所寄,只愿他们一切安好。
益州城,一匹快马掀蹄嘶鸣,急急停在“善水书院”门前,信使从贴着马肚的邮包里取出两封信,“书院里有人吗?……有人在吗?”
他站在门前唤了两声,不见人来,便试着往里走去。
“你找谁?”声音从信使背后传来,他转身瞧见一绿衣女子从门外进来,正是宋梓宁。
信使道:“姑娘是这书院的人?”
宋梓宁点头。
“可认得孔裕和李玦?”
宋梓宁又点了点头。
信使松了口气,天黑前还有许多信等着送,这下可以省点时间了,他递出手中之信,道:“那正好,这有两封信是给他们的,麻烦姑娘转交。”
“信?”宋梓宁接过看了眼,洛州寄来的,“行,我来转交便好。”她突然狡黠一笑,李玦,看我这回怎么整你!
“李玦——李玦——”宋梓宁找遍了书院,却愣是不见李玦人影。
突然,她想到一漏网之处,于是迈着颇为笃定的步伐寻去。
茅房外,宋梓宁清了清噪子道:“你不用躲了,本姑娘知道你在里头,我找你有事,再不出来我可进去了!”
茅房里一阵悉娑声响,然后门被急急推开,一个显然不是李玦的儒生两眼惊恐,提着还未系紧的裤头看着她。
宋梓宁当下也是一愣,随及装作若无其事般调头就走,转身后不由暗骂自己大意。
她心里嘀咕,好你个李玦,这些日子躲我就像耗子躲猫,我可还没消气呢!别让本姑娘逮到!
李玦此时正躲在书库最隐蔽的角落里,以昏暗为屏,以书架为障,避开宋梓宁耳目,他捧着本书,屈膝坐地,借书架间透进的光线阅字记读。
外头宋梓宁叫唤的声音李玦听得清楚,他将额头无力地磕在膝上,静埋着头,这暗无天日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他仍是想不通,自己究竟是怎么莫名其妙惹上了这么个刁钻棘手的姑娘,这段日子以来,他吃过她“好心”为他盛的盐拌饭,喝过她“好意”倒的辣椒水,能用来整他的计谋点子恐怕都用遍了,他如今每日见她就躲,只盼着她玩腻收手,可她似是越战越勇,乐此不疲,令他郁闷不已。
“李玦——”宋梓宁声音再次传来,只听她道:“有你的信,洛州来的——”
李玦猛地一惊,心胸剧跳,思绪骤乱,站起身就往书库外跑去。
宋梓宁此时正坐在檐下石阶上,百无聊赖地轻点着脑袋,口里如同念经般重复着:“有信啊有信,怎地还不来……”心里如同念咒般叨扰着:“鱼儿啊鱼儿,快快上钩来……”
当李玦气喘嘘嘘跑至她面前时,她正迷糊盯着脚下,一副快打瞌睡的昏样,愣是没瞧见他。
“我的信?”直到李玦出声问她。
宋梓宁闻声倏地站起身来,一扫方才的颓靡,精神百倍道:“是啊,是啊!”
她光彩飞镀的笑脸只持续了片刻,这会儿她已耷拉下了脸,抬手指着最高的那方屋瓦,说道:“可是……方才一阵风袭来,只怪我没能抓牢,害它被吹到那儿去了。”
李玦抬眸远远看去,果然,在屋瓦夹隙之内信封一角隐约可见,他已顾不得其它,急急转身欲走,宋梓宁一把抓住他衣袖,诧异道:“去哪儿啊?”
李玦回道:“我去寻个梯子来。”
宋梓宁暗松口气,放开了他,又伸手指着一处墙角道:“不用寻,不用寻,那里就有一个。”
李玦顺其所指一看,果然有个梯子靠于墙角之内,正隐露出一截梯脚,他此时万没心思注意宋梓宁这过人的'未雨绸缪'之能,只速速走去,搬来了梯子,架稳攀上。
宋梓宁殷勤道:“我来替你扶稳。”说着已是两手紧抓两边梯柱,一副保驾护航的忠诚模样。
待李玦双脚离梯触瓦的一刻,她双手聚上内力,用力一拉。
李玦只听身后噗隆咚咚一阵乱响,他回头一瞧,不由一惊,方才好好的梯子竟已散作一堆废墟,只剩两根梯柱仍握在宋梓宁手中。
她此时半仰着头,一脸不可思议地冲李玦道:“啊呀,梯子好像被你踩坏了,这可如何是好?!”
李玦欲哭无泪,就凭他这副血肉之躯又不是什么铜皮铁骨,如何能将好好的梯子踩成这般模样?!
宋梓宁安慰之声传来:“没事没事,你不用内疚,我去找人修修,你等着啊,很快的!”说完她将梯柱搁在一边,蹲身抱起那堆散乱的梯级匆匆而去。
李玦愣看着她消失,顿感绝望,这没有梯柱的梯子她得修到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呀?!
方才为信所急没有多想,李玦此时却已意识到,他可能又被她戏弄了。
那不远处的信封稳稳地被压瓦下,与其说是被风吹来,倒更像是怕被风吹走,人为之嫌已可落实。
然而他并不在乎,内心反而涌动着难言的雀跃,只因劭仪给他写信了,光是这份浓重的喜悦就能让其他一切都变得黯淡。
宋梓宁边跑边止不住笑出声来,她放缓腳步,卸下怀中梯级,拍了拍双手的尘土,心情大好,“哈,中了本姑娘的'上屋抽梯'之计了吧,伯伯不是说你是天才吗,你就自个儿想个办法下来吧!”
心情一好她顿觉肚腹空荡,于是踩着轻快的步伐找好吃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