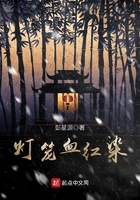书院内,孔裕与劭仪正在屋内相谈,“蛇已经出洞被捕,接下来你打算如何做?”
“此人意志坚定,从他口中得不出什么,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所以……我打算把他放了。”
孔裕笑着捋了捋胡子,“哦?看来劭仪的第二步是欲擒故纵。”
劭仪轻点了下头,只听她又道:“只是我还没想好如何来纵,据董大人所言,此人似乎异常精明,不好蒙混,我可得好好筹谋……”
然而,当天夜里郡首府便出了大事。
半个时辰前,郡首府地牢内。
关崇刚被灌了一碗汤药,他只觉四肢有些许无力,看来是为了防他逃走,他看了看锁着自己的铁链,又看了看牢门外那八个看守,心里苦笑,他们还真是多此一举,未免太看得起他。
突然,外面似有骚动,进来一个士兵与其中一人耳语几句后,五个人便出了牢房大门。
关崇心下有些疑惑,而眨眼间发生的一幕令他更为疑惑,只见剩下的四个守卫在一阵闪过的剑光之后频频倒下,牢门被打开,一个蒙面黑衣人站在关崇的面前。
来人一剑斩断铁链,又扔过来一身夜行衣,“把衣服换上,跟我走,快!”
是个女子的声音,关崇似乎并不认得,女子半搀着他离开地牢,只见郡首府内乱成一团,董鹏的寝室和书房同时着火,此时正火光冲天,雄雄烈焰映红了半边天。
他侧头望向女子,问:“是阁主让你来救我的?”
她没有回答。
关崇心里有些怀疑,难道是欲擒故纵之计?但这把火放地可真够狠。
女子转头看了眼后方,说道:“他们追来了,我们得分头走。”
她伸手从怀里掏出三本册子,竟然是密函!关崇大惊,此人究竟是敌是友,此事究竟是真是假,他只觉完全无从分辨,女子把密函塞给关崇,说道:“把名册交给阁主,他不会再怪罪你。……我把他们引开,你往北郊方向跑,应该能躲过。”
她最后深深地望了一眼关崇,仿佛蕴藏着千言万语,然后一转身朝另一边跑去。
就在那一刹,关崇记起了那一双眼睛,在蓝翎阁蒙着面的部众里他见过那双眼睛,是一双光映秋水般明亮有神的眼眸,他此时方确定此事乃并非一个计中计。他朝这个不知长相亦不知名字的女子最后消失的方向望了一眼,继而转头朝北郊方向而去。
他穿过林子后又不知走了多久,体内的药力开始完全发作,双腿瘫软,几乎无法行走,不料突然被石块绊了一下,脚下一个踉跄,终于力不能支地从山坡上滚了下去,失去了意识。
第二日一早,大街小巷早已传开,郡首府昨夜走水,火整整烧了大半夜,刺客逃至城外最终被捕。
劭仪一接到消息便秘密面见董鹏。此时她正看着地上用白布遮着的尸体,问道:“就是她?”
董鹏点了点头。
劭仪蹲在一旁掀开白布,一身黑衣包裹下的是一具年轻玲珑的身躯,脚上,背上中了数箭。
只听董鹏说道:“她本来不会死,不过,为了掩护关崇,她中了箭还拼命地想要引开我们,直到失血过多倒下。……她把名册交给了关崇。”
董鹏说话间劭仪已伸手揭去她蒙着脸的布巾,少女年纪与她相仿,此时苍白灰暗的脸色下是一张静秀谐美的脸,但她曾经或许美丽的双眼却再也不会睁开。
劭仪淡淡地道:“你觉得她是因为名册才如此拼命?”
董鹏反问:“难道不是?”
劭仪没有回答,她说不上来,但是心里隐隐相信,也许她只是为了救那个她爱的男人,这份相信或许只是同样身为女子才有的那一点点灵犀,但如今,她内心的真相是再无人能真正了解了。
待关崇睁眼醒来已是两日之后,朦胧间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猛地伸手往胸上一探,密函还在,顿时舒了口气,他侧头一望,瞥到了一抹淡粉,飘飘忽忽地挪动,又渐渐向他飘来。
这时一个温婉柔美的声音响起:“公子,你醒了?”
关崇看清来人,是一位陌生的女子,面若秋水,身姿袅袅,此时正递来一杯清茶。
他撑起半个身子,接过茶水,神色有些警惕,问道:“请问姑娘,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为何会在这里?”
女子不紧不慢道:“这里是益州北郊最偏远的一个小村落。之前,我去村外的林中寻笋,便发现公子你倒在路边,你好像是不慎从山坡上失足滚下的,手脚都有轻重不一的骨折,头也擦伤了,是我找人把你抬回来救治的。”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他边说边打量女子,见她的穿着气质,言谈举止并不像一个农家女子,不免留了几分心眼。
女子坦然地回视他,笑着道:“公子还有什么疑问请尽管问,只要别把小女子当成是拐了公子的人贩子便成。”
这回反而是关崇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忙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有些好奇,这村落里的姑娘是否都和姑娘你一样?……”
“一样什么?”女子诧异问。
关崇吞吞吐吐:“……一样……一样不像村落里的姑娘……”
女子闻言噗嗤笑出声,从她听来这话应该是正夸她呢,自然高兴,只听她娓娓地说:“我本是原益州城一户富人家的绣娘,因为……”她似乎有些难以启齿,“因为某些原因逃了出来……后来遇到战乱,躲藏间无意发现了这个村落,我喜欢这里的平和,就住下来了。现在在这里用绣品和村民换些东西,过得很好。”
关崇似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我昏睡了多少时辰?”
“时辰?你整整昏睡了两日。”
“两日?!”关崇有些吃惊,他们还没有找到这里?他有些迟疑地问道:“这两日……没有人来找过我?”
女子也显得有些疑惑,“没有啊,你是指你家人?这山坳里的村民都自己自足,从不出村,村里人家又少,恐怕连现任官衙都不知道这还有人家,你让一般人怎么找来?”
她顿了顿,又说:“不如我出村替你和家人报个平安?”
“不用!我没什么家人,只是担心朋友联络不到我,没关系,待脚能走了,我再出村找他们便可。”
女子点了点头,“也好。”
这时有人叩响了屋门,关崇全身警觉,女子拉开了门,门外传来一个妇女的说话声,关崇松了口气,只听她说:“姑娘,这是我刚做的芝麻饼,可香呢!拿一篮给你尝尝!”
“谢谢马大娘,那我就不客气了,您等等。”她进屋搁下篮子又拿了一块绸布回身塞给马大娘,“这很衬您,您收下。”
马大娘展开一看,当场喜不自禁:“唉呀,这太好看了,比上两次的更让人喜欢,姑娘真是巧手啊!”
女子也是满脸笑意。
关崇听着马大娘走出老远还在嘀咕:“这可真好看,太好看了……”他也不禁觉得好笑,又有些好奇,“莫非姑娘的手艺当真是天下无双?”
女子灿然一笑,道:“别的不敢说,绣牡丹,天下无双小女子当之无愧。”
“哦?”
女子见他不信,指了指盖在他身上的锦被,关崇仔细一瞧,一株牡丹娇艳欲滴,栩栩如生,姗姗吐蕊,碧叶凝露,真可谓天下一绝!
女子突然问道:“对了,不知公子如何称呼?”
关崇从呆愣中回神,回道:“我叫关崇,姑娘又如何称呼?”
只见她嫣然一笑,答道:“小女子,牡丹。”
书院内,劭仪在屋里展开从白鸽身上取下的字条,上面只有四个字:“一切顺利。”
看完后字条被放在烛火上燃尽。现在开始她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等!等着将蓝翎阁连根拔起!
屋外这时响起叩门声,来人正是孔裕,劭仪有些意外,这时辰正是孔裕给李玦授课之时。
孔裕也不卖关子,开口道:“为师有一事要请劭仪相助。”
“师傅但说无妨。”
孔裕却看着她笑了起来,说道:“劭仪可知伐柯应当如何?”
劭仪不知孔裕有何深意,心下一想便答:“自然是匪斧不克。”
“没错,劭仪可愿当一下这斧啊?”
量劭仪再绝顶聪明也猜不透她这师傅话中之意。
直到此时她坐在李玦面前她才明白她这把“斧”要伐的“柯”正是李玦的心魔。
孔裕交待她,在每天他为李玦授课的同时,劭仪需要做的事是:进出屋子一次,在屋里沏茶倒水二次,故意走近李玦三次。在她弄明白自己的任务就是防碍打扰李玦时,真有些哭笑不得。
原来孔裕发现了一直以来克制李玦才能大现的症结。在他认识的人中也不乏记忆超常甚至过目不忘之人,但李玦的记忆速度之快,记忆程度之细却凌驾所有人之上,他的问题在于只要稍有打扰,记忆能力便一塌糊涂。
而这两个月来他更发现对李玦最大的干扰便是劭仪,只要她经过或出现,一时,李玦对学习内容的记忆便与一般人无异。如果他能克服这个魔障,则再也没什么能阻碍他的非凡记忆。
他不知道李玦这‘君子’是何时发现了劭仪‘窈窕淑女’的身份,不过这等儿女情长的小事他显然并不关心。而劭仪也并不清楚她这个‘斧’对于李玦的特殊性。
此时劭仪就坐在离李玦不远的红漆木椅上,她手捧一本《茶经》,看得异常仔细,秀眉微蹙,羽睫时不时闪动,说不出的动人。
而李玦同样手捧书册,只是他看得异常仔细的是眼前的劭仪,孔裕卷书成棍,猛敲了下李玦的头,说道:“心有杂念!如何成事?!”
李玦顿觉羞愧,心思在沉静与慌乱之间无所适从,好不容易他将注意力放回书上,劭仪便走动沏茶倒水,他又抬头望向她,视线久久不能移动,孔裕的书棍子再次敲来,“不抵干扰!如何成事?!”
李玦惭愧。劭仪再次起身倒水时,李玦望了一眼,随及低头阅书,站在他身后的孔裕点了点头。听到李玦与孔裕时不时的对答,劭仪惊讶不已,从认识李玦到现在不过两月有余,他的进步竟然如此神速!
她站起身走到李玦案边,翻看放置一旁的李玦写过的字,越看越觉不可思议,不能想象此乃出自一个月前还不识字的人。
劭仪身上散发一股如兰一般清幽恬静的香味,李玦看着手中书册,半天没翻上一页。孔裕见状摇了摇头,随及再次挥棍,道:“不能自持!又如何成事?!”
出了门劭仪再也忍耐不住,终于笑出声来,她笑着道:“师傅一向温和,没想到……”说着又不可抑制地笑起。
只见孔裕故作无奈道:“劭仪向来乖巧,何需老夫如此操心!”
劭仪道:“可见师傅已将'因人而异'的授业之道运用地如火纯青啊。”两人又是一阵大笑。
深夜里,床塌上,李玦正辗转于梦魇之中,梦里到处都是孔裕挥着书棍,不停地问他,“如何成事?!”“如何成事?!”……
他终于惊醒,发现自己满头冷汗,他擦了擦额头,想起梦中孔裕的脸,突然觉得好笑,忍不住苦笑连连。
李玦一下没了睡意,他踱到窗前,推开窗户,趴在窗棂上,望向远处对面的厢房,只望见漆黑一片,她此时正在酣然熟睡之中吧……李玦脑海里浮现劭仪今日在屋里的样子,在她装作淡定漠然的表情下,时不时流露出那一丝无可压抑的笑意,虽然几乎不可察觉,可李玦还是能感觉到,此时,他就像一个回味着美味糖果的孩童,趴在窗棂上吃吃地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