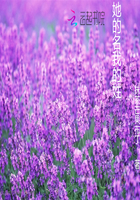之所以还是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兴趣不减,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旨在改善生产激励的基本策略。说这样的改革策略是事先设计好的,那是不可信的,大有事后诸葛亮之虞。它更像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改善国有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改进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的生产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与竞争,这些都是经济学的典型问题。有意思的是,在经济体制没有发生基本变革之前,改善生产者的效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带有“帕累托改进”的特征。在早期,这个绩效的改进常常就被解释成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
我自己也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2001年,加入了观察和研究中国企业改革与绩效的行列。尤其是1995年初夏从美国结束博士后研究回到复旦大学,我的学术研究开始聚焦在中国工业部门的改革方面。我对工业组织的变动、利润率、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和经验都非常有兴趣。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得到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的主任Athar Hussain博士的支持,并在他的推荐下,我在1996年年底取得了英国学术院/(英国)皇家学会“王宽诚研究奖学金”(British Academy/The Royal Society K.C.Wong Fellowships),使我在1997年秋天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研究工作,并对中国工业部门发生大规模亏损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模式的研究论文Market Size,Scale Economies,and Pattern of Loss-making in China's State Industry(中文版为《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一个产业组织的分析》)。
当时我选择这个题目从事研究主要是因为中国项目组的主任Hussain博士的建议,在此之前,他和当时在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研究中心工作的庄巨忠博士(现已去了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的亏损模式,但主要是考察亏损企业的地区分布并试图解释亏损的地区特征。在我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后,开始从Hussain博士那里接触了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的大量数据,经过反复斟酌,最后我决定选择亏损变动的时间模式来进一步分析亏损发生的系统性原因。
这篇论文的初稿曾应邀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报告过,报告会由当时在该研究所负责亚洲事务的David Wall教授主持,Hussain博士亲自陪同我参加了这次为我主办的专场报告会。1998年下半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这篇论文的中文稿(因为篇幅所限,发表时做了较大压缩)。我知道,自《经济研究》发表了这篇论文之后,我的解释在经济学界引致了不少评论和不同意见。据说,在该论文申请“孙冶方奖”的评审过程中也因为有不同意见而在最后时刻与“孙冶方奖”失之交臂。
但是,这篇论文后来被英文杂志East Asian Review??受,发表于2000年春出版的千禧年卷的首篇。2000年6月,我应邀参加东京大学的中兼和津次教授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主持的一个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高级研讨会,在会上我也报告了这篇论文,并得到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石川滋教授和美国匹兹堡大学Tom Rawski教授的点评。
我在这篇论文中试图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在改革以来会变得如此严重?关于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经济学家有过不少研究。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研究并没有去观察国有企业发生亏损的时间模式。刚刚提到的Hussain博士和庄巨忠博士对中国国有企业亏损的研究集中于亏损发生的区位模式方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不过,我更关注的是亏损发生变动的(时间)模式,并试图解释这个模式。因为我注意到,亏损的指标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太大的变动,而国有企业真正出现大规模的亏损似乎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并且从此不断恶化。正如图6-5所显示的那样,由于亏损企业的亏损额猛增,国有部门的净利润(赢利企业的赢利扣除亏损企业的亏损)在80年代末之后不仅陡降,而且从90年代中开始甚至变成负的了。
为了从整体上解释国有企业亏损的这个变动模式,我在论文中构造了一个
工业组织的简单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我把市场的规模或者需求因素以及厂商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我这样做的基本考虑是,虽然单个企业都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出现暂时的亏损,但是整个部门的大规模亏损在我看来显然应该只可能是一个“转轨现象”。也就是说,发生这样的行业性亏损必定与中国的工业改革和转轨过程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我需要从转轨过程中的重要参数来寻找解释亏损发生的变动模式。我认为,市场规模或者需求的变动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我将另一个因素“锁定”在厂商的规模上。我相信还有其他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从经验观察中注意到厂商规模变动或者工业组织变动的相关性。因此,我决定尝试将厂商规模纳入到我的解释模型中去,从而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工业组织模型。这个模型的均衡条件是:
在我构造的这个解释模型里,市场可以维持的厂商数量n(即保证每个厂商都不亏损)是(1)需求规模的增函数S;(2)是厂商规模变动的减函数。在这里,厂商的规模在短期是由固定成本(F)与边际成本(C)的关系决定的。显然,这样的理论结果大大简化了我们对中国工业亏损问题的解释逻辑,而且大致上又捕捉了工业改革和经济转轨过程的基本特征。在转轨过程中,随着市场的自由化,原来在计划经济下累积起来的超额需求必然推动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这在20世纪80年代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投资的增长和生产能力的改善,市场规模的扩张必将趋于缓慢。通常,在一个不存在超额需求的“古典竞争”状态下,厂商规模的差异将会影响和改变市场的结构。规模显著的厂商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维持原来的均衡状态就不再可能维持原有厂商的数量。换句话说,这时候,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厂商将因为厂商规模的差异或由此导致的市场结构的变动而失去赢利能力,成为“亏损企业”。我认为,这一点可能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工业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那种大规模亏损现象是很重要的。事实上,我始终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工业统计中总是存在着“亏损企业”这样的统计项目?“亏损企业”似乎是中国工业(不仅是国有的)企业的一个重要的部门。
另外,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部的村上直树(Naoki Murakami)教授开始与我进行个人的学术往来,并通过他,我结识了很多日本的经济学家和在日本工作的多位中国经济学家。我在前文提到过,在此之前,我已注意到村上教授等人针对中国工业改革所发表的多篇研究论文。当时,村上教授、大琢启二郎教授以及刘德强教授即将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工业改革》,而我则有幸提前阅读了这部著作的打印稿,并为该书中文版的出版进行了努力。
1998年年底,我在村上教授的帮助下获得东京都立大学招募基金的资助,来到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部与村上教授合作研究,并有了面对面地与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大琢启二郎教授讨论中国问题的机会。这次访问的结果之一是有了与村上教授和梁坚博士合作的那篇关于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决定的英文论文。同时,我开始对度量中国工业企业的效率变动和规模经济等问题产生了兴趣并成为我之后几年的主要研究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