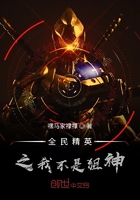四十岁那年他送十三岁的女儿去城里上初中。
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女儿站到他面前:“爸,我要走了,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老莫看看女儿,仰仰头看看已经过时的木质房顶,看看房梁上两只即将南飞的燕子。老莫说:“把你的画夹拿来。”
女儿从小爱画,有画画的天赋,她的画在学校有些名气。女儿有些疑惑地拿出画夹,画夹展开是一张洁白的画纸。
女儿看着父亲:“爸。”
老莫拽拽上衣,捋捋头发,屁股在椅子上挪了挪,坐得端端正正。
“没有什么要交代的,我要你画一张画,画我的眼睛。”尔后两眼静静地看着女儿。
女儿和父亲对视着,慢慢地执起画笔。女儿画得很认真,画笔显得很凝重,渐渐地父亲的头部轮廓出现在洁白的纸上,再慢慢地画那双深沉似海的眼睛。画的过程中,她几次凝视着父亲的脸,凝视着父亲的那双眼睛,甚至停下了画笔。老莫看见女儿的眼里渐渐地蓄满了泪水,直到老莫提醒女儿,女儿才又重新画起来……
画完了,终于画完了。几乎花费了将近两个小时,女儿才完成了这幅叫做《父亲的眼睛》的画。扔下画笔,她再也抑制不住,扑进父亲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老莫抚着女儿的头,一种如山的父爱和岁月的沧桑袭上心头。
好久,好久,女儿由恸哭变成抽泣,偎在父亲的怀里像一只猫。女儿擦擦眼泪,娓娓地说:“爸,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这样仔细地看你的眼睛。
爸,你的眼里藏着很多东西,真的,那么丰富的内容。爸,你老了,你的眼角有了那么多的皱纹……”他仰着头听着女儿的叙说,泪水再一次从眼眶里溢出。慢慢地,女儿偎在他怀里睡着了。
女儿走了,女儿在城里的振兴中学。
女儿每周回一次家。周末的傍晚,老莫和妻子蹲在路边等着女儿从那辆城乡中巴上走下的身影。
这年初冬老莫进城去文联开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结束,老莫去了振兴中学。
老莫走进振兴中学时下午上课的铃声刚响。老莫站在校园里,有些迷惘地在匆匆的人流中寻找:善女儿的影子。忽然他听见一声喊:“爸。”女儿气喘吁吁地站在他的面前,脸红扑扑的。女儿说:“爸,你吃饭了吗?”
老莫点点头。老莫看一眼女儿:“你上课吧,我走了。”女儿拉住父亲的手,女儿把老莫领到她的寝室。女儿说:“爸,你歇会儿,等我下课了你再走。”
老莫看见女儿的寝室收拾得很干净,在女儿床头桌子的玻璃板下,他看到了那幅叫做《父亲的眼睛》的画。
老莫很久很久地看着这幅画,他眼角的鱼尾纹画得很逼真。老莫翻看了女儿的书,看到了女儿的日记本,日记本里竟也有一幅题名《父亲的眼睛》的画,规矩地夹在日记本的中间。隔一页老莫看到了女儿的日记《父亲的眼睛》:不是父亲让我画眼睛,也许我一生都不会这样认真地看他的眼。那是双充满内容的眼,有一种深沉的父爱,有对女儿的期望,有一种慈祥,从父亲眼角的皱纹中我读出了父亲的艰辛。十三岁,不小了,这双眼睛让我学会思考,告诉我不要辜负父母的希望……
从此老莫没有再去过女儿的学校,只是每个星期天,总要亲自下一次厨。
女儿顺利地考上了县一高,在学好课程之外,依然执著地爱着画画。
暑假里骑一辆自行车去西山写生,有时老莫也孩子似的陪着女儿去。
三年后,女儿考入省美院。大二的时候,女儿的作品开始发表,那幅《父亲的眼睛》被登在北京一家权威杂志上,受到好评。
大三的那年冬季,省美院为女儿举办了一场个人画展。女儿提前约父亲,请父亲一定参加。开展的那天下着小雪,展厅外一片洁白。为等老莫,典礼推迟了一个多小时。老莫到底没有来,女儿无奈,把一幅大大的题款《父亲的眼睛》的画放在主席台上的一把空椅上。
仪式结束,客人们涌进展区,她怅然若失地踱出展厅。雪已经把这个城市变成了银白,有一只鸟儿从低空掠过,她觉得此刻自己像这只鸟儿一样孤独。然而刹那间她眼睛一亮,眸子里盈满了泪水,她看见了那双眼睛,还有母亲的身影……
雪在无声地下着,世界一片纯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