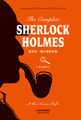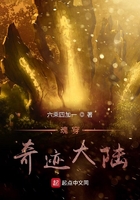捏掉头顶的一片树叶,秋天了。
瞎子那年说:“我想认个干娘。”瞎子每走一个村都这样说着他的愿望。
瞎子唱的是地方戏,小段子、整轴子的戏都唱。唱得累了,停下弦子嘘口气,瞎子说:“俺想认个干娘。”瞎子说:“俺娘死得早,俺……瞎子很伤心。”
瞎子再接着唱。瞎子连个干娘也认不下啊。
瞎子不服气,不服气的瞎子那年终于认下了一个干娘。
那是在瓦塘村,瞎子听见树叶落进水塘的“噗”声,瞎子拉完了最后一个音,似一种断帛之声,瞎子擒住了一片树叶,几滴泪落在那片叶儿上。
瞎子的两手还执着那把弦子。瞎子知道面前还蹲着一个人。别人都走远了,蹲在跟前的人说:“孩子,我是个寡妇,你愿认吗?”瞎子的手颤了一下。“你愿认吗?”瞎子这次听准了。“娘。”瞎子扑通一声跪下,弦子“哽”地响了一声,像从心里跑出的一个音符。
干娘去扶他。干娘说:“给娘拉一曲吧,算认娘曲。”
瞎子说:“娘,阿炳也是瞎子,我就给娘拉阿炳师祖的《二泉映月》。”
场地静着,稍息之后,弦声骤起。尔后弦声悠悠扬扬起来,一泓泉水在瞎子的弦声中流淌着,一弯月儿映照进池塘。瞎子看不见,但瞎子知道干娘的身边又站满了人。
曲终。干娘起身说:“孩子,娘给你做饭去,从今再来瓦塘,你不用吃百家饭了。”
“娘!”瞎子的泪“哗”地流出来。
那年瞎子二十一岁。
瞎子依然到处去拉他的曲子,唱他的坠子。瞎子习惯了游走,瞎子脚下的路就是手里的那根棍子。瞎子和干娘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双月的十九回一次瓦塘村。瞎子说:“娘,我不能天天待在瓦塘,我还要出去唱坠子呢。”
干娘说:“记住,娘等你。”
每一次走时,干娘都把他送到村外的十字路口,问干儿往哪个方向去,然后孤独地瞅着瞎子远去的身影,看天上的几只鸟儿叫唤着伴着干儿往前走。那是她家房檐下的鸽子。
有一次,是夏季,十八的中午雨就下来了,十九还未停。干娘打着伞在村外的十字路口等瞎子。不见瞎子的身影,干娘心里急得慌。干娘沿着一条路往前走,走一段再回来;又沿着另一条路往前走,走一段还不见瞎子,再回来……
从另一条路回来时,干娘看见路口站着一个雨人。干儿说:“娘,我踩着脚下的路知道泥路上站过一个人,娘,我连累你挨淋了。”干娘攥着儿子的手往家走。回了家,干娘为他换衣裳,又赶紧为他做姜汤。
每次回来,干娘都给他烙那种很香很香的饼,把身上的衣裳洗了换了。干娘好啊,干娘让他的心里有了娘,干娘使一个瞎子在漂泊的路上有了一个温暖的驿站。
瞎子的心就动了。
那天瞎子说:“娘,你想听一个孩子的故事吗?”瞎子说:“十三岁那年我接连失去了爹和娘。在一个雨天干爹把我拉回了他家,干爹说要从此养我做儿子。那个女人就是因为干爹收留我带着他们的女儿离开干爹的,从此爹就一直养着我,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干娘紧紧攥着他的手。
干娘说:“儿的命苦。”
瞎子说:“爹知道我认了个好干娘,一直想当面来谢谢干娘的。”
干娘握着瞎子的手点着头。
瞎子的干爹和瞎子一起来瓦塘是一个秋日。瞎子和干爹走进院子时,一群鸽子又往高处飞,又在院子里旋着不远离。瞎子听干爹干娘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脸上就有笑漾起来,后来瞎子对干爹干娘说:“爹,娘,你们都是苦命人,你们握握手吧。”瞎子说着把两双手往一起拉。
两双手就紧紧地握住了。
瞎子把手也握上去。
三双手紧紧地握住了。
干爹和干娘的脸上都有了泪。
瞎子坐下来静静地展开弓,一曲乐儿悠悠地漾起来,时光慢慢地从他的脸前滑过去。
瞎子依然走在路上,手里的棍子就是脚下的路。瞎子走着走着就禁不住想:我终于找到能和爹在一起的娘了。
瞎子想着,棍子击地,竟然在路上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