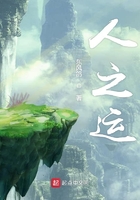别人的报道与我有关
历险归来后,我和邓世祥各自写了一篇有关暗访的长稿子。后来在编辑部的要求下,我们两人又将此稿综合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全面修改,后面大部分文字都是邓世祥完成的。这篇由署着我们两人名字的长约七八千字的文稿,由任天阳交到报社几名正副主编认真审阅后,送到了头版编辑案头上。
当时我在编辑部看到,这篇稿子的题目为《记者暗访王圣堂出租屋被黑帮劫财后险遭灭口》,在文前还特意将王正的那封长达好几页的举报信,以“读者来信冒险大举报”为标题,摘录了近千字,当时程益中和任天阳还亲自写了“编者按”。
看到我们联手写的这篇稿子后,要闻部几位编辑都激动地拍着桌子说:“你们这样的采访真是太伟大了!如果全文发出来,我相信,这篇稿子一定会轰动整个羊城,轰动整个广东省,轰动全国呀!”
“石野,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作为记者,你们能这样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去暗访,实在是了不得哇!我们几个在编这篇稿子时,一边看一边都心惊胆战,背后冷汗直冒,如果发出来,肯定会让所有读者触目惊心……”
几位富有正义感的编辑也先后多次要求有关领导早日见报。主编关健、南方日报社委会成员李民英和任天阳等人,刚开始时都一致建议用两个整版的版面来刊登这篇独家新闻。
起先,我们以为报社肯定会在近几天发出全文,没想直拖了好几天,还是不见动静。我跑到编辑部询问原因,一位编辑悄悄地告诉我说:你们暗访的事早在外传得沸沸扬扬了,有人说你们的这种形式已违反了新闻纪律,最好不要发这篇稿子。
报社也有知情人士告诉我说:广州火车站那一带,一直是禁区,也是广州的形像,有人说如果将稿子发出,将会大大影响整个广州地区的良好形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更令人沮丧的消息随后传来:上面早就有人向《南方日报》领导做工作,不要发这篇稿子……
这天下午,邓世祥来到办公室告诉我说:“我们王圣堂历险的稿子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肯定发不出来了,刚才任天阳也说了。我看,还是另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吧,这篇稿子一定要在自己的报纸发出来,否则,我们两个人不是白死了一次么?”当天夜晚,我正在办公室里苦苦思索时,邓世祥又把我拉到任天阳的办公室里,商量着有关对策。
身为采访部主任的任天阳是我们这些记者的主管领导,是我们顶头上司。那时与我们的关系还不错。再说,我们这次重大采访是他直接领导的,他更是此次事件的主要策划人,我们两位骨干记者因为采访差点命赴黄泉,而现在时间已过了这么久,这么一篇代价巨大、极具新闻性的独家新闻竟然就这样被压着不让发,这实在于情于理都不容。这个结局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更令我们这两个历经生死的当事人无法接受!
见我和邓世祥又一次上前询问有关发稿之事,平时不大爱抽烟的任天阳,此时心事重重地点燃了一支“红塔山”香烟,随手给我们各分了一支。
为了驱逐心中的郁闷,平时不抽烟的我此时毫不犹豫接过了这支烟,点燃后,狠狠地连抽数口。
任天阳好言好语地安慰了我们两人一番后,说:“也没想到这次采访会出了这么多事,弄得报社压力很大,这篇稿子只能等候一个合适的时机再说了。我也知道你们二位一时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但这都是上面的指示,《南方日报》社都向老关他们特意为此事打了招呼,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实在希望你们理解……”
我们能够看出来,任很为难。在讲了一番大道理后,任又向我们提议说:“如果这篇稿子实在是我们这儿发不出来,我看,还不如拿到外面去发……”
他沉吟了一番对我说:我看这样吧,稿子先放在我这儿,如果《南方都市报》彻底没戏,我就想法给外面的报纸,我先找一找香港的报纸看一看吧,你们的心血也不能就这样泡汤……
第二天,香港某报的一名记者打电话到报社告诉我,他已从任天阳和邓世祥那儿得到了我们的稿子。其实他们早在几天前就听说了我们这次历险之事。他们认为这实在是一篇好的社会新闻,他们的报纸表示愿意做。我马上想起这个热心的记者了,事发第三天他曾向我电话询问有关情况,但我不便告之,只是承认的确发生了这么一回事,同时很委婉地拒绝了他提出的独家采访。对于任何一家报社的记者而言,获取独家新闻是最重要的使命,此宗我们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重大新闻,在自已的报纸尚没有见报之前怎能轻易泄露给其他传媒呢?
没想到几天后,邓世祥突然兴冲冲地跑到我的办公室,神秘兮兮笑了笑,咬着我的耳朵说:“老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事情已上了香港的报纸啦!本来是我们的独家新闻,谁叫我们的报纸到现在都一直不敢发,现在人家的报纸刊登出来了,不知我们报社的领导有何感想?怕是后悔莫及了!”
说着,他把藏在背后的一只手亮出来,一份复印件递到我的面前:“快看看,虽然通篇没指明我们两人的名字,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事情。瞧,这上面还有人家特意配的一幅插图呢?香港记者就是会做新闻。”
我一看,这是香港某报头一天的报纸,虽然是复印件,但图片清晰,文字一目了然。虽然篇幅不多,只有千余字,但写清了有关我们历险的过程,配发了一幅该报记者拍的王圣堂全景图片,同时还特意安排了一两幅漫画插图,画的是几名手持刀枪的歹徒正将我们洗劫一空的情形。
不知怎的,看着这篇报道,我心中没有丝毫欢欣,沉甸甸的悲哀反而立即像一只乌森森的枪口顶在胸膛上。凝结着我们心血的这次暗访文章,不仅没有在自己的报纸上刊发只言片语,而且至今没有一位报社的领导向我解释半句;相反,当我几次三番地去向他们询问详情时,对方不是躲躲闪闪,就是支支吾吾,或以打呵呵的口气进行推脱搪塞。我实在不明白,我们这篇为了揭露罪恶的报道究竟在哪些地方触犯了有关部门的利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当我们与黑恶势力作斗争时,怎么就一不小心站到了有关部门的对立面呢?舆论监督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舆论监督正是公众监督权实现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意义就在于让公众了解他们应该了解的情况,公众在知情后及时反馈消息表达他们的利益和愿望。所以,当记者在报社领导的领导下忠实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为什么却不能够有效达成我们良好的初衷呢?
更令我没想到的事还在后面。就在邓世祥送给我那份香港某报报道的当天下午,报社一位领导把我召去,颇为不满地质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我或邓世祥向他们提供的消息?因为这篇发在香港某报的报道,有关部门后来还曾对我的背景进行过一系列调查。
我们的历险之事虽然已有其他媒体刊登出来,但《南方都市报》对此固守沉默,一直不见任何要发稿子的动静。
对于一名新闻记者而言,为老百姓说真话,为弱者伸张正义,为了及时揭露我们这个社会中的邪恶和黑暗面,我曾多次遭受到对方的粗言恶语,推拉驱逐,威胁辱骂,恐吓围攻,以及此次在王圣堂遭受黑帮刀枪劫持,历经九死一生,凡此种种,我都没有怨言。对于这些来自外界的种种压力,打击报复和艰难险阻,我堂堂一条汉子都能够承受得住,但是令我难受至深的是来自报社内部的重击,特别是这次,面对报社有关人士的冷漠和胆怯,只顾追求四平八稳,不敢下情上达,不敢将他们亲自策划、几乎是以两条年轻的生命为代价而换来的独家新闻却不能及时发出,这令我无法不痛心和悲哀!
风雨中的悼念
为了调整情绪,我决定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看望久违了的父母。心力交瘁的时刻,恐怕难以找到能比家乡与亲人的怀抱更温暖的怡人之地了。历经逃里逃生后,一向不顾家的我,不知怎的,此时特别渴望早日见到家乡一草一木,渴望能陪同早已对我望眼欲穿的父母亲好好呆一些日子。我请了半个月的假,特意抽两天时间在广州的几家大商场为家中每一个人都购买了礼物。从部队出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始终随心所欲四处流浪,刚开始常常连生活都过不下去,从来没有为父母亲添置任何东西,别说手头有钱寄往家中了。自从我进入《南方都市报》后,我暂时结束了以往的窘迫状态,真心实意地做起了一名记者。我是如此热爱这份职业,整天骑着那辆除了车铃不响其他任何部位都响的破旧自行车,穿梭在广州城大街小巷,四处寻找新闻线索。由于我工作非常努力,我每月的发稿量都名列前几名。我除了每月800元固定工资外,每月稿费的收入还是不错。
这样一年多下来,我也总算略有积蓄。这次我总算可以毫不犹豫买上一张卧铺车票,像那些农村外出打工挣了两个钱的同胞们一样,能人模狗样地回一次家了。
到家的第二天,父母欣慰的泪眼未干,我就前往离我家六十余里的殷祖镇去看望家乡的文学老师殷显扬。此时的显扬老师因患癌症,刚刚从武汉化疗回来,正卧病不起。已经有好几年不见面的他,不顾病痛,叫家人扶他起来,倚在一张沙发上与我聊天。虽然此时绝症在身,还是那样亲切随和,谈笑风声。
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当他听我说出心中郁闷的源头时,震动不已。老人一把紧紧拉着我的双手,感动地叹息着:做记者的本来就不容易,你现在能做到这个境界更是难得可贵了!感慨不已的老人当即来了兴趣,要将我此次的历险传奇写成报告文学。
老人不顾顽疾之痛,竟然就这样坐在我的对面,认认真真地对我进行采访、记录,一直坚持了近两个小时!
我在广州王圣堂暗访历险之事,除了报社的同事和《南方日报》有关领导知道外,外人一般大都无从知晓。我尤其想到,如果我的历险让我那远在千里之外湖北乡下的父母耳闻,他们不知将会遭受多么大的惊吓!如果此事让我的父母知道了,他们肯定不顾一切冲到广州来,将我拉回家去。虽然记者这一职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社会地位较高,名声也不错,但对于一直生活在平静农村的父母而言,他们是宁可让我回家种田喂猪,也不要自己的儿子做这种命悬一线的工作的。所以此次回到阔别经久的家乡,我刻意对工作闭口不谈,直到好几个月后,我的父母亲才从老人发表在我们家乡的报纸上读到有关我的历险事迹,他们才知道真相。听家人讲,当时我那善良的母亲捧着关于我的历险报道时,不由浑身颤抖,无声的泪水哗哗直流,怎么也止不住。
十多天后,当我返回广州,老人又多次来电询问我近况,要求我将那篇我和邓世祥共同合写的胎死腹中的采访纪实寄给他。同时,他又通过我与邓世祥电话取得了联系,先后又对其多次采访,完善每一个细节。
邓世祥了解到这位老人是在身患癌症的情况采访我们时,也很感动,他不但积极配合老人的采访,而且还主动及时为他提供新的有关情况。
接着,邓世祥应老人的要求,特地挑选了几张近照寄给了他。6月初,他的这张笑容可掬的照片,连同我的两张照片随同相关文章一起发表在1998年6月份的《华西都市报》上。因为邓与我一起前往王圣堂暗访时,曾以表兄弟相称,所以在6月24日这天的连载中,编辑还特意在他的图片说明上加注“这就是表弟邓世祥”字样。后来,这篇题目被改为《记者卧底历险记》的新闻连载发表后,还真的有少数热心读者把他当作我的表弟呢。
花费了巨大力气好不容易完成这次特殊采访后,老人又花了十余天时间,一边忍受着病痛折磨,一边靠在床上,一笔一划的,完成一篇长达四万余字的报告文学。
这篇长文不仅消耗了老人的大量体力,同时,由于劳累过度,甚至险些诱发其他病症。后来,据他的长子殷章雄告诉我,这篇长稿子写完后,老人又大病一场,直到家人将他送往武汉同济医院急救,终脱离危险。
几天后,这篇报告文学被当时全国报纸之中稿费最高的四川《华西都市报》特稿部看中,时任特稿部主编的张健新慧眼识珠,以高价“买”走,并从1998年6月13日起,开始在该报特稿部“连载精选”专栏上以《记者卧底历险记》为题,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连载。
在这篇长达六万字的长篇连载中,显扬老师采用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小说形式,以大量较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写了我这几年在南方做记者时节许多历险过程。其中文中所占篇幅最大的就是1998年4月1日我和邓世祥在广州王圣堂暗访时遭受到那群匪类劫持的历险全过程。
这也是自从我们脱险后,除港澳地区外,国内第一家有关党报较为详尽地予以正式公开发表。这篇具有轰动效应的特大新闻在当时全国都市报中发行量最大的《华西都市报》刊载后,旋即全文又被陕西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华商报》及《重庆晚报》等报纸全文转载,山东烟台的《生活周报》等数十家报纸也刊载了。
同年8月,《黄石晚报》以《大冶记者羊城历险记》为题,以整版的篇幅,特意又一次披露了我在王圣堂的历险过程;同一月,我家乡的《大冶日报》第一次破天荒以新闻连载的方式先选发了其中重要章节,致使本来默默无闻的我一下子就成为家乡老百姓心目中的侠义英雄。以致后来,家乡只要有人来到南方,大都要特意寻到《南方日报》看望我;同时,从老家来南方打工的老乡只要在南方碰到了不平事,也都会跑到广州来找我援助,还有人特意从家乡过来看望我。
一个多月后,老师又给我写来了一封信,还给我寄来了他在病中完成、于1998年8月发表在《黄石日报》上的一篇千余字的随笔,他以简洁的笔调,乐观的态度,在此篇题为《我的心目无癌症》的文章写道——
……1996年7月我病倒了。10月15日被送往省城肿瘤医院,是中期偏晚的支气管肺癌和肺部转移癌,住84天医院就好了。出院前主任医师问我为什么比别的人康复得快?我笑着说,我每天要唱三首歌,我的心中无癌症。谁知春节过后,突然出现双颈淋巴转移癌,据说转移癌到了7个月就要死人的,我却过了8个月才去肿癌医院搞放射治疗。医生说我去晚了,效果没有上次好。我说走着看吧。又住71天医院,效果却比上次更好!我的心中无癌症,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很少去想什么“癌”。
脸上那死黑色也褪光了,恢复了以前的老样子,精神一好,手指头发痒了,那爱好写作的“毛病”又犯了。有人说,得癌症的人一操心就会死。我想试一试,死了拉倒!不怕死那是假话,谁叫自己有“爬格子”的爱好呢。先写了千字短文一试,自我感觉良好,再写两千字和三四千字的小说,投寄到报刊都发了。这下一发不可收拾了。
今年5月花了十来天时间,写了一个三四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南方都市硝烟香》,竟被发行50万份的《华西都市报》以稿酬千字350元买去先发表。这时有人看了我的底稿后说内容有问题,意思是有“毒草”之嫌,说得我有点忐忑不安。直到首都的《北京青年报》来电话通知也即将连载,我才放下心来,6月底我接一位远方朋友的来信,他在西安买到一份发行40多万份的《华商报》,在“连载精选”的专栏中,全文转载了那个中篇报告文学,不过题目改成了《记者卧底历险记》。既然是连载精选,也该是本人的一个“精品”吧。《华西都市报》在连载前的介绍中有一句话是“石野是黄石市作协会员”,他为黄石市争了光,我那文章中的主人公让我也搭福了啊。
要是有人问我的“精品”是怎么写出来的,大概是我得了癌症,放开了思想,无拘无束之故吧,才写出了主人公的真感、真情、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