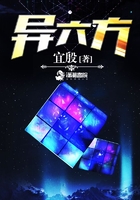春末夏初夜风寒,古城木楼清水淡。问谁堪比红日早,集商晨书渔家船。河水潺潺的仓桥,清晨的阳光还没来得及带走绿叶上的露珠,起早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忙碌忧劳的一天,大街上人影浮动,河岸边青草葱葱。
杨陌一手拿着油条,大口喝下半碗豆腐花,一副狼吞虎咽的吃相。昨天体力消耗太多,赶了一晚上的路,饿坏青春期少年了。
早餐店很小,只能容下六七桌客人,生意却是非常之好。杨陌和老俞坐在靠路边的一张小桌上,这是另外添加出来的,这样的摆设,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虽看上去不协调,却是别有一番民间小餐馆的风味。
味道不错,就是好像少了点什么,我还是喜欢老家渡口那里的馄饨。杨陌嚼着油条口齿含糊。话说接我们的人呢?怎么还没到。
老俞细嚼慢咽地吃着一碗牛肉面,右手夹着一根燃了半截的香烟,热气和烟雾交织在一起,迷茫了双眼,模糊了记忆。离开了太久,我早已忘记了故乡的模样,所以每个曾经停留的地方,我都会将它当成故乡。所以每个地方,都是故乡的味道。入乡随俗吧,小子,做事情要有耐心。
来来往往的人群,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赶路的人们要去哪里,又从何而来,无人问津。大家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生活中,彼此交集,又互不干扰,日子过得井井有条。原来所谓生活,就是各自过活。而所谓故乡,就是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小餐馆的客人已经换了几批,对于没点几个菜却长期占着座位的,不出意外,便会迎来老板娘的白眼和与他人拼桌的下场。这是一种风俗,你已经融入其中。
哎呦,不好意思了两位,小本生意多担待,客多人手少,见谅拼个桌。老板娘一边面带着歉意的微笑一边已经拉着两个新来的客人,动作熟练地收拾干净了半张桌子,硬生生将一对男女安排在了杨陌一桌。
这是杨陌第一次与石林和林梦云见面,一次终身难忘的偶遇,一个无心之举造就的一段友谊。若干年后,当别人来询问当时的情景时,徐娘半老的老板娘甚至完全毫无印象。当然后面发生的一些不愉快和小矛盾除外。
四人各自开吃,各怀心事。作为当事人中唯一的女性,林梦云从始至终倚靠在石林的身边,细嚼慢咽,端庄秀气,低着头一言不发,一副标准的江南女子闺秀模样。在杨陌的眼里,两人的情侣身份是再也明显不过了。所以当后来林梦云称呼石林为师哥的时候,一口老血被杨陌生生咽了回去,差点憋到内伤。
路的东边是一座古石桥,过了桥便是西林禅寺,高耸的西林塔仿佛近在眼前,杨陌仿佛已经听见了寺中的梵音。这是很难跨过去的一座桥,老俞告诉杨陌,这桥名叫秀野桥,他有个朋友就住在那里。杨陌心想,这年头的怪事真多,一条黑鱼说他竟然还有个朋友,这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殊不知自己早就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
四人无言,埋头吞咽。一个莽夫带着四个彪形大汉突然出现在桌前,抬起右脚踩在边上的长凳上,一副标准的纨绔子弟大少爷德行,满脸横肉,高仰着头,言语跋扈道:还不快滚,这桌子爷要用。姑娘挺不错。
嘴真臭。石林面无表情地斩钉截铁道。
脚酸吗?杨陌则是半问半答的问了一句。
莽夫被打断了话语,听着两人不冷不热的嘲笑,愣神后才反应过来。什么酸不酸的,听不懂人话。两个臭小子找死,不知道大爷我是,啊!
一声惨叫从莽夫嘴里嚎了出来,话未说完,人已飞远。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一个巨大的身影带着一嘴的血撞倒了一棵树,瘫坐昏死在了对街的地上。牙齿碎了一嘴,半截小腿还留在了长凳上,血流如注惨不忍睹,喧闹的风景刹间变得场面恐怖。
尖叫声此起彼伏地响起,四个彪形大汉楞了一下,随后拿起身边的家伙便冲打了过来。长凳方桌漫天飞,油条豆浆洒一地。满目碎屑,人群大乱,慌不择路,抱头鼠窜,呼爹喊娘,场面难看。老板娘拍着大腿哭喊大叫:别打了,都别打了。我的店啊。老头子你快去叫人啊,你们别打了。这可叫我怎么活啊。
这是仓桥人民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连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只维持了没几天。当然深受其害心留阴影的老板娘除外。后来林梦云问谁打的嘴巴,谁剁的腿。杨陌和石林很有默契地异口同声,只承认打了嘴巴。事后剁腿这件让人不和谐的事情,便理所当然的落到了老俞的头上。正所谓黑鱼精背黑锅,一路黑到底,众望所归。
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