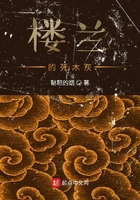风雪大冷,此人死于病疾,与唐仙无甚关系。
他叹息一声,走到了船头握住那渡人手中的桨,轻道一声好走,将他推入了河中。
唐仙从北门重新回到了听雪楼,走的时候还故意在城里面晃悠了几圈,仿佛生怕某些人看不见他,不能够注意到他。
……
城中风雪漫漫,苏寒山沏了一壶热茶,在悬崖上与一名道人对饮,棋盘上已经染上了漫漫飞雪如花,边角掩埋,如同道人的鬓间那悬挂沾染的晶莹,苏寒山指尖的黑子已经冰冷刺骨,但他迟迟未落,静静注目棋盘上的一切。
道人目光袅袅,不解问道:
“先生为何迟迟不落子?”
棋盘上局势均衡,僵持显著,苏寒山没有更好的选择,那子……只能落在一个地方。
苏寒山浅啜一口热茶,白气在嘴角幽幽,那被冻硬的黑子已经收回了掌心,冰冷刺骨的感觉未能够让苏寒山有任何不适,他看向远方被飞雪笼罩的王城说道:
“此子尚不能落。”
道人蹙眉。
“为何?”
苏寒山淡淡道:
“下棋的人,想要下棋的人……远不止你我二人。”
“王城的势力纷杂,龙不飞既然开了局,我便要杀很多人。”
道人闻言,眼睛转了转,埋头盯着棋盘,眉头紧锁,露出了沉思者的模样。
“要杀很多人?很多是多少?”
苏寒山目不转睛,眼神里面似有浓云玄雾,笼罩了整座模糊的王城轮廓,他声音淡淡,甚至嘴角还露出了一抹若隐若现的笑容。
“晋国的王族……我要杀一半。”
此话一出,道人顿觉天寒地冻,身子忍不住蜷缩起来,一个劲儿的哆嗦。
他扔掉了手里的白子在棋罐里头,嚷嚷道:
“唉,不下了不下了,天太冷了,这棋没法下。”
“回头我去酒楼里同食观仙讨一点烧酒喝,这个天不喝酒简直活不下去,以前我在玄清道观的时候,每日就算少吃一顿饭,我也得喝二两酒,夏天喝女儿红,冬天喝烧刀子,偶尔还会搞一只香喷喷热腾腾的烤鸡来吃。”
回忆起了这神仙日子,道人忍不住砸吧两下嘴,听雪楼别的没有,吃的真不少,这些日子他在听雪楼待了没有多久,胖了一圈。
也怪他从前时候太瘦了,但无论如何,道人确实觉得这里要比玄清道观带着舒服许多。
除了没有那个诚挚又可爱的少年,耳畔也没有虔诚的诵经声。
道家与佛教不同,但亦有道经可诵,那孩子每日清晨起来担水做饭诵读道经,已然成为了道人生命之中难以或缺的一部分。
他从积雪覆盖满满的地面站起身子,非常僵硬地伸手拍了拍裤子上面的雪,从山道离开,道人走后不久,玉面狐又从远处出现,踩着绒靴出现在了苏寒山面前,将手中的暖炉递给了苏寒山。
“唐仙已经被杨一家族的人放回来了,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事情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苏寒山轻轻抚摸着暖炉,一旁的下人将棋盘与棋罐子用一个大罩子罩住,防止积雪在上面覆盖,玉面狐靠在了一边的凉亭柱子上,问询道:
“咱们需不需要再加把火?”
“只是给太子演了一出戏,兴许他不会上钩。”
苏寒山微微摇头。
“生死大临,太子如此疑心过重之人,不会放过他看见的一切可能,咱们做的越多,就越容易引起太子猜忌,反之咱们若是尽可能做的隐蔽起来,杨一家族的人便会面临更加可怕的危险。”
“咱们现在得有一些耐心……对了,林家那边儿怎么说?”
玉面狐余味深长地回道:
“林家的胆子很大,那么大一块肥肉,他们已经决定搏一搏,从太子的嘴边抢走。”
“琉璃巷子只怕是西十二街里面最肥美的肉了,这都敢吞,也许林家在朝廷里面还有背景。”
苏寒山笑道:
“那一定是攀上了些关系,不然林家这样的家族,万万不致于能够往王城里面挤,万事总要踏出第一步,他们的做法早已经昭示着他们野心。”
“王城的势力已经很多年没有有过大的变动了,听雪楼的入驻让很多江湖势力看见了苗头,他们认为只要自己能够给王城里面的大人带去足够的利益,他们就能够成为王城的一份子,光宗耀祖,抬起门楣。”
玉面狐想了想道:
“难道这世上就不会有第二个听雪楼?”
苏寒山笑道:
“短时间内应该是不会有了。”
“听雪楼的成功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个世上没有第二个蔡千机,也没有第二个封不劫,百年之内,你只怕见不到第二个听雪楼了。”
提到了蔡千机,玉面狐又来了兴趣,她嘿嘿一笑,带着浓烈的好奇问道:
“当初点苍山那一战,你真的赢了蔡千机?”
苏寒山沉默了许久,回道: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
玉面狐怔然。
“为何?”
苏寒山摩擦掌心暖炉,平静道:
“小寒山剑有一剑名为【镇海冲云】,此剑自我悟出之后再也没用过,当世兴许无人可挡。蔡千机的武功通天彻地,他或许能挡下,或许不能,但我不会对他出这一剑,以前不会,日后也不会。而我当年离开点苍山的时候,他亦没有用全力和我交手。”
“若只是论武,我不及蔡千机一半,这个世上只怕也没有人能够胜过蔡千机半分,若是杀人……也许只有封不劫能杀蔡千机。”
“但现在封不劫已死,蔡千机当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真要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
玉面狐沉默,关于蔡千机的实力究竟几何,这些年来不断有人猜测过,但蔡千机已经数十年没有出手过,究竟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威震天下的游侠谁也不清楚。
人是会老的,材质再无双的一柄剑,如果失去了锋芒,对人的威胁自然就小了。
运河外的某条林荫小道上,穿着一身破绒袄的左桂生缓缓召回了天上的一只飞鸟,将它小心塞回了胸口的温暖衣服里头,这才转身朝着道路的另一边离开。与此同时,王城内的另一处街道上,先前那名在运河边上的杨一家族的下人,竟然七拐八弯去到了太子府里,更有意思的是,无人发现他是在什么时候变幻了自己身上的装束,甚至连脸都改换了模样。
这是一个相当厉害的易容大师。
进入太子府邸,他没有被人拦下来,腰间的那块血玉已经昭示出了他的身份,他进入太子府不久,左桂生便也随之而来,二人一前一后到了太子的长宁殿中,对方高坐在台阶上,奴婢捧着夜光杯,递至唇畔,他若不饮,奴婢便微微收手,数息之后再试探。
白帘似雪,风鼓寒透彻。
那名易容者到长宁殿阶前跪下,对着太子说道:
“殿下,听雪楼的的确和杨一家有所勾结,他们的动作很隐蔽,甚至看上去有些像江湖仇怨,听雪楼的人在大运河畔被杨一家族的人用麻袋装走了,大约两个时辰之后,那人又被重新放了回来。”
左桂生出现在了长宁殿内,跪在了易容者旁边,低头沉默,一言不发。
太子伸手拨开了嘴边的酒杯,微微挑眉看着左桂生,问询道:
“左桂生,为何你不说话?”
左桂生的心底闪过豺二狗与他说过的那些话,回道:
“董雨龙所说的事情都是事实,奴才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唯一担心的事情,大概便是这一切都是听雪楼的阴谋,兴许他们只是使用了反间计,目的便是岔开太子殿下的注意力,为真正的那名拿走了太子殿下密信的人掩饰。”
太子闻言皱起了眉头,他细细一想过先前的事情,眉头又舒展开来,笑道:
“就算听雪楼能够算计到后面的事情,他们总不至于能算计到谁会去他们那个地方吃饭吧?”
“那么多去吃饭的人,偏偏只有杨一家族的人和本太子有关系。”
“再者,如果他们想要栽赃给杨一家族,只怕需要做的明显许多,本太子在王城那么多的眼线,最后只有你们二人发现了,这足以说明听雪楼并不希望外人看见这件事情。”
“杨一家……很好,非常好。”
他的笑容已经染上了帘外飞雪的狰狞,那双隐藏在袖袍下面的拳头攥紧,愤怒溢满了胸膛,作为一个未来的一国之君,未来君临天下的皇者,夏武宁无法容忍自己下属的背叛。
“荣扈,杨一家的人在王城呆了多久了?”
那名倚在窗边的老人如实回道:
“三百四十三年。”
“就是说,他们赚运河的钱,赚了三百四十三年?”
“对。”
太子仰头,深吸了一口气,杀意凛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么简单个道理,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占了运河三百多年,便真以为这个地方是他们自己家的东西了?”
左桂生盯着地面眼神微动,开口道:
“殿下莫要意气用事,那杨一家族的手里面还掌握着一些对殿下不利的证据,现在殿下暂时还不能够和他们翻脸。”
太子闻言面色阴沉了下来。
诚然,左桂生的话相当难听,但非常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