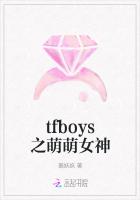刘南渊身为长公子,前脚刚踏入家门,下人们便将预备好的麻衣递了上去。
“母亲,父亲为何暴毙?”
刘大夫人朝身后使了个眼色,心腹王婆子领会,屏退了灵堂里的下人,将门关上退了出去。
“南渊,家中有些事情如今也不能瞒着你了,自从七年前刘贵妃上了位,你父亲便接到宗族的一封信,具体写了什么我并不知道,只是从那时起,刘家便秘密开采了徽川银矿”。
银矿,刘南渊早料到父亲经营的牲畜场不足以维系如此庞大的家业,没想到竟然是银矿。
刘大夫人见儿子未言语,继续道:“众所周知银矿乃官矿,不允许私自开采,而徽川银矿更是锦国之秘,外人不得而知,起初我以为你父亲受宗族胁迫不得已私开银矿,后来,他接二连三的纳妾,替那贱人赎身,我才知道是我太天真了……”
说道此处,刘大夫人便哭了起来,刘南渊知晓母亲近些年的苦楚,轻声安慰了几句。
“渊儿,你可知母亲的不易,若不是为了你,我奈何受这屈辱。”
刘南渊的目光落到刘纵的尸体上,脖颈处似乎以后一个痕迹,一个规整的圆形痕迹。
“母亲,我去看看父亲。”
刘大夫人止住哭声,嘴上说着“自从娶了三姨太,便断了夫妻情分”,手一松,还是放开了儿子。
刘南渊朝刘纵磕了三个头,起身上前,轻轻拉开了父亲的外衣,亵衣,看清胸腹处的伤口时,瞳孔骤然紧缩。
刘大夫人感受到儿子的不平常,关切道:“怎么了,可有什么异样?”
刘南渊看了哭肿眼的母亲,却未多说什么,“母亲,我要回房休息。”
“好好,你回房吧,跑了一天一夜,肯定累坏了吧,晚些时候再来”。
回房的路走到一半,刘南渊折返到了交易场的后院,他的二十多个手下和半路抓来的主仆二人都在这里。
“钱叔,可问出了什么?”
钱长水吸了一口烟袋,道:“是池家医馆宗族的药师。”
刘南渊又问了一遍:“只是一个药师?”
一封印了池家医馆印章的信递了过来,刘南渊接过一目十行的看完,深吸了口气,道:“父亲是被排箭打死的,我看了那伤口,铜弹应该还留在身体内。”
钱长水放在鞋底上卡了卡烟斗,重新填上烟丝,“死者为大,况且还是你的生身父亲,池家医馆看似是医馆,本家确实开国始祖晟帝的子孙,招惹不得。”
“池家宗族遥居沄州数百年,极少听闻,忽然冒出是一个毛头小子自称宗族药师,未免过于蹊跷。”
“信中所言详尽,南渊,今日便放他回去吧。”
“我去审讯一番”
刘南渊抬脚便往里走,臂膀处一紧,“钱叔?”
“南渊,这个人古怪的很,身上不知还会不会藏着剧毒,没有必要与他较真。”
“及冠小儿罢了,纵然祖先荫祐,能保永世不成。”刘南渊目光淡然的扫向被捆绑在柱子上的少年人,既然钱叔有话,他也不强入,问道:“那个土堆里埋着的人是谁?”
钱长水又吸了一大口,刚填上的烟丝被他吸进了一大半,“是个傻子,前天夜里从牲畜场跑出去的,那排箭也是从他手里掉落的,到底是谁修复了排箭目前还没有线索,只知道那人是竹林送来的。”
钱长水拍了拍衣袍上尘土,接着道:“胡广才估计是遇到了那对主仆,中了息毒,现在还在昏迷,这息毒也是池家的秘药,可通过鼻息皮肤入体,若是不及时解毒,毒入人心,这个人便是废了”。
言外之意就是胡广才他们是无药可医了!
闻言,阴狠的目光再次落向那少年,若不是钱叔,自己也会中那息毒,握拳的手指微微一颤,似是心有余悸。
耳边传来钱长水的长叹声,“胡广才是三姨太带来的,倒是没什么可惋惜的,可惜的是刘商啊,在老爷身边养了那么多年,如今却成了个傻子。”
池玉清感受到背后的阴冷,微微侧身,望向了门口。两人目光对视,一个鹰锐,一个清傲,似乎都想从对方的眼中寻找到什么。
“事到如今,有些事情便要落到你身上了,你们刘家是东郦刘氏的支族,虽说隔着远,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就近了,我跟随你的外祖父多年,对你父亲的事情倒也听闻些许,如今你也看到了”。
刘南渊收回目光,说道:“父亲向来不喜谈论刘氏家事,在母亲送我去越州的那一刻,便是为的今天,母亲已经告诉我一些关于生意上的事情,此处不便,我们改日再说。”
池玉清见他们走了,换了两个戴着面罩的男人进来,这群人的身形普遍高大壮硕,四肢孔武有力,都是功夫高强之人。他踢了踢正在发呆的杜文,杜文突然坐直了身子,那俩守卫见状,脚下一软,险些被地上的杂物绊倒,双手紧紧的捂住了口鼻。
“公子,怎么了?”
池玉清高挑眉峰,道:“没事,只是有些渴了。”
“知道了,我去要一些水。”说着,杜文拧巴着身子,朝那俩人喊道:“两位壮士,能给我们一点水喝吗?”
两人隔着面罩看不清对方的表情,都不愿意起身送水。
见那俩人纹丝不动的站在那里,杜文又喊了一遍,两人依旧装作没听见。
“公子,怎么办。”
池玉清轻叹了口气,声音已经有些沙哑,“你家公子我想过千万种死法,从未想过会被渴死。”
杜文一听,这不是在指责自己照顾不周么,继续朝那两人喊道:“两个大哥,我家公子要渴死了,要是医馆的人来了,发现公子渴死了,刘家大少爷定然饶不了你们。”
一听刘家大少爷,俩壮汉才慢腾腾的起身,倒了两杯茶水,可两人都不送来,而是寻了一根木棍,将茶杯一点一点的蹭到两人的脚边。
“当我们是什么了,手脚被绑着呢”。
杜文气结,他不知两人都被钱长水嘱咐过,刘商胡广才现在还在没醒过来,他们宁愿被少爷责罚也不会靠近池玉清。
“杜文!”
池玉清闭上了眼睛,沙哑的声音中带了一丝疲惫,“安静吧,等十七叔来。”
苏子慎从羊舍出来,便瞧见浩浩荡荡一众人绑了两人往羊舍的地方走来,正要返回到羊舍,却瞧见那个四处搜寻的伙计进了羊舍,情急之下就跳进了盛草料的竹篓。
好在四处都是牲口的鼾啼声,并未被发现,眼瞧着众人从眼前走过,竟觉得那被捆住手脚的灰衣男子有些眼熟,这不是杜文吗?那位华衣的莫非是马车上的那位?
脚步声消失,她从竹篓里出来,顺手抄起一根木棍,潜入了羊舍,伴随着一声闷哼,男子的手吹落了下来。
“你”苏子慎的手中还举着沾血的木棍,见那女孩惊恐的看着自己,她微微一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善可亲,继续道:“你快把衣服穿好,别着凉了。”
在羊群的咩咩声中,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声,苏子慎也换上了伙计的衣物,将张扬的短发包进了头巾,扭头出了羊舍,朝远处走去。
门外传来敲门声,其中一人去开了门,“干什么的?”
“大少爷吩咐小的送来的”。
他低头一看,不过几个馒头而已,“你进来”。
“干什么?”伙计一听,也有些害怕,下意识的后退一步,却被一把拉了进去。
“去给他们送过去。”
“啊?可是我”
“让你去你就去,要喂到嘴里。”
伙计拿着馒头,往里看了一眼,无奈的叹了口气,慢腾腾的走到池玉清的面前。
“给”
池玉清睁开眼睛,看着他,顺势咬了一口到嘴边的馒头,低头看了眼地上的水杯,道:“水”。
苏子慎不知他有没有认出自己,见他似乎真的渴了,险些呛到。
“公子,你慢些喝”
杜文见公子受罪,还以为这伙计手脚不利索,嚷嚷道:“你能不能慢一点,都呛到了”。
苏子慎眼皮一跳,扫了他一眼,道:“都被绑上了,还想找人伺候?能有口喝的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要当少爷回家当去,这里没人伺候。”
“你说什么?你你”
杜文想骂回来,可是,他瞧见一把闪着寒光的小匕首落到了自己手边的草堆里,整个人如同煮熟的虾子,你你你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什么来。
苏子慎喂完了池玉清,来到杜文身边,报复性的将茶水倒进了他的嘴里,起身拍干净身上的草屑,道:“喂完了牲口,还得来喂你们,就会这么喂,不想喝就别喝。”
“小兄弟火气这么大,小心长不大”
池玉清笑眼看着她,那眼神让苏子慎有些不舒服,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
那两个门卫听见了,朝苏子慎吆喝道:“快过来,这个人可不好招惹,小心把小命搭进去。”
苏子慎拿着杯子回来,问道:“不就是个文弱书生,有何可怕”。
“傻小子,你可知他是谁?沄州池家的药师,一身的毒,沾上可就没命了。”
苏子慎一怔,生气道:“那你们还让我去喂水?”。
两名大汉见苏子慎恼怒的模样,哈哈大笑起来,“真是个鳖憨”。
话音刚落,两人忽然齐刷刷的倒在地上。
“谢谢你”
身后传来一道清爽的声音,苏子慎一回头,见方才还气若游丝的小公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