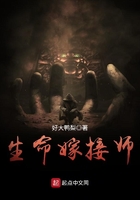都写到这里了,我还未能写到,那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早晨,大姐为何趴到炕上哭,还有母亲为何愁眉不展。
其实,应当说,现在,我仍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我想说的是,通过那个早晨和紧接着发生在我家的一系列变故,让我七岁的脑瓜里,突然有了许多想法。
在我们村子里,说一个孩子心眼多,大概说得就是我后来的样子。
所以,当我看到王小憨手臂上的抓痕时,尽管心中一惊,两腿一软,但我还是快速走开了。
快速走开,在我想来,是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好不让王大憨察觉我已发现他手臂上的抓痕。
不让他觉察,一方面是我一时还不敢肯定,王大憨就是那晚掐住我脖子,想要我小命的那个人;另一方面,若那个晚上的这个人,果真就是王大憨,此时一旦被他觉察,我一个七岁孩子,以后想对他做些什么,怕是比登天都难了。
不过想想,一个喜欢沉默寡言的七岁孩子,又能够对他做出些什么呢?
说心里话,当时,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不过,自从亲耳听到母亲被王有发欺负,亲耳听见王小脚背地里提到我母亲时的那种口气。还有,自从被人掐死,然后扔到王建设家的茅房里之后,那种要报复一个人的火苗,一点一点地,已在我小小的胸腔里莫名的燃烧起来了。尽管在当时,我对身边的每一个大人,都还心存惧怕。
可是,正当我苦思冥想,接下来要对王大憨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家里却出事了。我母亲被邻居王眯糊家的“八狼二母”给打了,而且打得相当地惨。这也让我们本来相当友好的两家人,从此结下仇恨,摩擦不断,这是后话,暂且不说。
我所提到的王眯糊家的八狼二母,我要说,这也是后来,我对王眯糊家八个儿子两个闺女的独有称呼。
事情的起因其实相当简单,人们也往往喜欢把最简单的事情,弄得无比复杂起来。
这天后半晌,母亲和王眯糊的媳妇——那个我们称眯湖娘的五十多岁的女人,一起去生产队的秧苗炕上间红薯秧苗。据说,二人一开始还是有说有笑呢。关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移。事情的突然变化,还是在中间。中间,母亲突然感到肚子一痛,便急忙往茅房跑。大概是母亲去得时间不短,再回来,就见眯糊娘正贴着相邻女人的耳朵说着什么。
按说,咬耳朵的话,母亲是不应该听到的。可是,与眯糊娘相邻的女人耳朵有些聋,不大声一点,根本听不见。如此以来,眯糊娘与相邻女人本来是咬耳朵的话语,却是越说声音越大,最终都句句钻进了刚从茅房回来的母亲耳朵里。
一开始,母亲还微笑着朝两个老女人跟前走,但走着走着就停住了,笑笑的面容也一下冷成了雪霜一样。
不用说,眯糊娘咬耳朵的话语可谓句句都扎到了母亲的心窝上,更是句句都能要了母亲的性命。所以,当眯糊娘还正说得起劲的时候,就见早已气得脸色蜡黄愤怒至极的母亲,只一个箭步就扑到在了眯糊娘身上,先是张嘴死命地咬眯糊娘的肉,紧接着,又狠命地撕扯眯糊娘的头发。可怜眯糊娘头上本来脱得剩余不多的几缕头发,被愤怒的母亲只几下都扯光了。直到咬完扯完,堵在母亲心口的那口气也才吐出来。
但母亲的气肯定仍没有彻底出出来,她将眯糊娘狠狠地压在自己身子下,声音不高也不低地开始问道:“眯糊嫂子,你说,谁的X痒痒了,憋不住了?”
眯糊娘的嘴几乎啃到了地上,当然回答不出。
母亲又接着问:“你说,是谁被弄得狗一样嗷嗷乱叫?”
眯糊娘的呜呜了几声,仍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出。
就听母亲又接着问:“还有,眯糊嫂子,你说,是谁的闺女当母狗一样被公社的干部送给了县上?”
……
应该说,眯糊娘显然是被母亲的突然袭击完全吓蒙了,窝在母亲身下,光见她嘴唇哆嗦,满嘴呜呜,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
不但眯糊娘给吓蒙了,一起间秧的其她女人也是半天才缓过神来。等七手八脚将母亲从眯糊娘身上拉开,就见眯糊娘竟是一下跳起,怕再次挨打似的一下跳到了八步开外。
这一天,被拉开的母亲和眯糊娘都被生产队长早早劝回了各自的家。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就见母亲正在做饭,一副懒得理我的样子。
这时候,我并知道,母亲已经和眯糊娘打过一架,甚至当这天傍晚,我站在我家屋前的台阶上,隔着我家与王眯糊家的矮墙,看到下工回来的王眯糊家的八狼二母,都进到他们家屋里停留了一会儿,紧接着,又突然纷纷抄了家伙朝我家走来时,我都没有想到,他们是来打架的。
在此,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母亲正在我家院里——前几天才刚刚砌成的灶前做饭,有气无力地拉着风箱,二姐上学还没有回来。我呢,当时也不知正站在台队要干什么。反正是,王眯糊家的八狼二母,眨眼间冲到母亲近前,举手中棍棒就打的时候,我是呆呆地看过足有两袋烟的功夫,都一直没有回过神来。
应当说,母亲也是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就见她先是下意识地举双手护着头部,挨了不知多少下打,。待回过神来,这才猛地站起想跑。但哪里还能跑得脱。八狼二母已把她围得严严实实。王眯糊家的小女儿甚至都扯住了她的头发,就见她双手猛用力,母亲也一个跟头裁倒了地上。
“快来人呀,打死人了!”很久以后,我都以为第一声喊叫是我发出的。事实上,这声喊是刚刚放学回到家的二姐发出的。
二姐边喊叫着边向王眯糊家的八狼二母扑去,她先是一头将王眯糊家的老三撞倒在了地上。紧接着,又一头将王眯糊家的老六也撞倒在了地上。王眯糊家的老五刚掉转身来,想要将二姐按倒在地上,不想,他的手腕反被二姐死死咬住了。
应该是,在当时,我是受了二姐喊叫的启发,才最终从惊恐中醒过神来,才一边大哭一边大声喊叫起来。
随后的结果是,不但喊来了更多的乡邻,也把民兵连长王有发,大队书记王振林、妇女主任兼村卫生室赤脚医生王小脚都喊来了。
打成重伤的母亲被送进了陈庄公社卫生院,同样被打成重伤的二姐也被送进了陈庄公社卫生院。紧接着,我就听说,她们在当天夜里又被紧急送往了县上的医院。
而王眯糊家的八狼二母呢,先是被我们村的民兵五花大绑着关在大队部里,紧接着,又被押往公社。直到第二天后半晌,他们才一个个蔫头耷脑的回到家中。
这期间,我一直由王小脚看护着。一开始,王小脚是一直坚持要把我带往她家的,我坚决拒绝。所以,母亲和二姐出事的那个晚上,王小脚就睡在了我家。
我说过,王小脚除了脚小和手小之外,却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女人。不但人长得高大,屁股也肥大。这些,在平日,我们也只是看个外表,这个晚上,可以说,我却是真真切切地见到了。尤其我想说的是,这个王小脚,不但人长得高大,屁股大,身上也白。
当然,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些,最关键还是,她既不象母亲她们这个年纪的人,喜欢光着身子睡觉,也不象大姐她们这个年纪的喜欢穿着背心睡觉。这个晚上,我可是见到了,王小脚却穿了一件说是背心又不是背心,可以说,是一件露着整个肚子和大半个白脊梁的小背心。
我要说,这样的穿着还不算稀奇,最稀奇的还是王小脚穿的那个小裤头,可以说,是我活过七年以来,见过的最小裤头,简直小得前面捂不严,后面更是捂不住那对大屁股。
在我后来的记忆里,我仍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并不十分闷热的晚上,王小脚就是这样,挑亮我家那盏煤油灯,抽出我们家里最新最干净的一床被子,铺摊开来,手里摇着我母亲经常用的那把蒲扇,一蒲扇将煤油灯扇灭,然后就很大方地躺在了我的身边。一股年轻女人身上那种特有的香气,也直往我的鼻孔里钻。我想打一个响亮的喷嚏,却一直打不出来。
“一个孩子家,别光闷着了,精神起来,跟婶子说说话。”黑灯瞎火中,就听王小脚先这样问道。
从傍晚母亲和二姐挨打,到王小脚躺在我身边,好几个小时过去,我的嘴巴一直闭得严严的,一句话都没说。晚饭当然也没吃了。不过,我心里可是一刻也没闲着,主要还是担心母亲和二姐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从母亲和二姐被村民兵七手八脚拉走时的样子看,肯定是活不成了。
“告诉婶子,你有发叔是不是经常来你家?”见我未说话,王小脚把手中蒲扇又重重地在我上方空气里扇了两下,这样问道。
王小脚的话,在这个晚上,听上去,却是格外地温柔。但我始终大睁着眼睛,看着黑暗的一个地方,仍是一声不吭。直到王小脚问得不耐烦,似乎很生气的扭身睡去,我仍是没吭一声。
第二天一早,我仍是一声没吭,爬起来就上学去了。王小脚也再没理我。
这时候,其实我还不清楚,关于母亲和大姐的事,早已在我们袁家坟村民中悄悄传播开了。但他们并不提王有发,也不提大队和公社的干部,只说母亲一个寡妇家,如何勾引村里的汉子,甚至连王眯糊家打着光棍儿的老大老二老三,他们也说母亲都勾引过。而大姐呢,他们更是说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中午,王小脚没来,我狼吞虎咽了两个剩棒子面饼子,就又朝学校去了。我并不清楚这么早去学校要做什么,反正是,一个人呆在家里,总让我有种恐怖的感觉。
可是,这一天下午,还没等我走进学校,就被几个大年级的孩子堵到了一个墙角的位置。
其中,带头的王老喘的大儿子,首先笑嘻嘻问:“给我们说说,你娘是怎么勾引男人的?”
我几乎没等他们说话笑完,早已弯下腰去,抓了两把细土快速朝他们眼里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