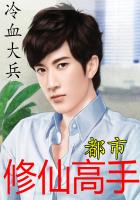予澈懒散地倚在竹榻上,就着灯光执卷夜读,嘴角喊了秀逸无双的轻笑,读至精彩处,击节拍案,饮上一杯应时桂花酿……
夜深,风凉,烛火飘摇。人,也有些薄醉了。
或宿醉未醒,或薄醉微醺,酒真好,喝到恰如其分时,总能替他挡去一些不想参与,又不得不参与的头疼事。
予涵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帝王宝座,北伐也已经提上了日程,只有予汶的事情悬而未决,顶着齐废帝的头衔,在七尺斗室内饮酒唱曲儿,倒也乐得自在。
街头巷尾的那些传闻早已入了予涵的耳,他甚至还来了含芳堂一趟,安慰了他一番,“定是朱氏余孽从中作梗,试图破坏咱们兄弟的关系!六弟,你可别放在心上。”
予澈不由得轻笑,他自然不愿将此事放在心上,只怕,有人已经惦记上他了。
玉宇无尘,银河泻影,夜风送来酴醾的芳香。
予澈垂眸,望着倚在怀里的漓裳。
漓裳睡得很沉,嘴角微微翘着,像个酣睡的婴儿。烛火摇曳,长长的羽睫颤了颤,在凝脂般的肌肤上投下极为轻浅的眼影,竟是说不出的撩人。
“阿漓!”他弃了手中书卷,轻轻地将她抱起,层层帐幔无声无息地在身后落了下来。
凸凹有致的胸口平稳地起伏着,床.上的人儿睡得极是安稳。他的面上漾起轻浅的笑意,柔软的唇瓣和着桂花酿的芳菲落了下来,极娴熟地纠缠着,推送,滑动,渐次深入。
睡梦中的小人儿有了小幅度的回应,这丫头,定是以为是在做春梦呢。
纤长的手指透衣而入,沿着姣好的曲线滑行,揉捏着,轻浅而从容,顷刻之间便让睡梦中的小人儿在悸动中惊醒过来。
“王……王爷……”漓裳眼涩神饧,慵懒中透着说不出的委婉轻妩。
予澈的胸口急剧地起伏着,眸中焰火跳跃,瞳孔愈显幽深,“阿漓,醒了吗?”
“六哥!六哥!”
这一声轻浅问候随着一连串的六哥在耳畔炸响。
帐幔起伏处,予泠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予澈急忙拉上锦被,话语里不可抑制地透了愠怒,“八弟!你懂不懂规矩!半夜三更的朝我的床帏里闯!”
彼时,予澈的衣衫散乱,清隽的面庞染着沉溺于情.欲的绯红,饶是予泠再愚钝,也看出了头绪来。
他挠了挠头,讪讪地道:“那个……六哥,我……我不是故意的,是……是废帝……要见你!”
初进京的那天,予涵和他探讨了一个下午的,就是要如何取下予汶项上的那颗头颅!他执意不肯,一直拖到了今天。
陡如冷水浇头,予澈顿时从沉溺的****中惊醒过来,“皇上他,终于动手了?”
予泠摊开手,很不屑的样子,“废帝一直嚷嚷着要见你!要我说,随他吵吵去,理他做甚!皇上倒是心软,非让我过来找你,说也算全了废帝一个心愿!”
予澈搓揉着眉心,“容我整理一下,马上就到!”
予泠撩起帐幔,“我出去等你!”
“王爷……”漓裳从被褥里探出头来,担心地望着予澈。
予澈给了她一个安慰的浅笑,将她按回至被窝里,“阿漓,你先睡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去看看就回来。”
说着,他已从床榻上跳了下来,略微理了理头发,便已飞了出去。上了辇舆,这才得下闲来打理凌乱的衣衫。
“九弟说了什么没有?除了我,可还见了别人?”
予泠的神色隐在暗夜之中,看不甚清晰,雪白的牙齿相击,蹦出的每一个字都刻薄至极,“我也正纳闷呢。他害的你还不够吗?也不怕你一时按耐不住,上去一把掐死了他,倒是省了一壶好酒!”
予泠早已认定了予汶便是杀害傅昭仪的凶手,难免对他恨之入骨。
这个认知未免太武断了。二王、三王、七王的母亲不就他那温婉沉静,与世无争的母妃下的手吗?这样的话,予澈自然无法向予泠提及,他轻叹:“八弟,你别这样。傅母妃到底死于何人之手还不一定呢?九弟,也许,并没有咱们想象中的那么狠。”
予泠啐了他一口,“六哥,你是不是没睡醒呢?这个时候还替那个混蛋说话?!”
予澈知道辩解无用,无奈地摇摇头。
明朗的夜空忽然冒出了几点浮云,风吹云动,流云遮月,夜色渐次黯淡了下来。夜风侵衣,竟然疏疏落落地洒了几个雨点。
宫人的脚步急促的敲击在甬道上,时交三更,更鼓之声掠过暖风帘幕,层楼叠院,声声击打着昭明宫沉寂的空气,亦击打在予澈的心膜之上。
两个人在玉竹殿左侧的假山从中下了步辇,就着疏疏落落的灯火,在宫人的引导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进了隐藏在假山中的地牢。
阴风习习混着腐烂霉湿的气息铺头盖脸地铺了过来,予澈伫立了片刻,方才勉强压制住呕吐的欲.望。
一灯如豆,暗沉的地牢里闪烁着熹微的光线。
“光线太暗了,多点上几只蜡烛来。”予澈吩咐道。
身畔的宫人闻言,急忙捧了烛台过来。
光线骤亮,地牢内的一切尽数扑入眼底。
四壁苔藓横生,墙角上铺了一层发潮变黑的稻草,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予汶身上所戴的脚镣手铐乌黑发亮,极沉重不说,那铁链竟然穿透墙壁,深埋在石墙深处。
予澈的眼底忽然泛起一阵湿意,纵然心中有恨,一刀了结了也便罢了,何苦这般折磨与人?
想予汶自幼娇生惯养,手无缚鸡之力,被押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本就度日如年,那样沉重的镣铐怕是早磨烂了他一层皮吧。
“九弟!”予澈轻唤了一声。
予汶转头过来,盯着他有些发红的眼圈,并无落魄愤懑之感,反而笑了,“到底是六哥多情!”
二十年来,这大抵是予汶第一次叫他心平气和地叫他六哥吧。予澈回以浅笑,“多情自古空余恨,倒是无情好!”
予泠抱着肩斜倚在楼梯的栏杆上,不冷不热地道:“哪那么多废话!人也来了,有什么话,只管说来,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清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