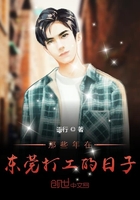过了几日,宜和被安排进了更加幽深的倚兰宫,偌大的宫里,只有她和红若两人。
她们刚踏进来,身后宫门便缓缓关上了,主仆二人转过身默默地看着最后一抹风景消失在门缝里。
“我们是被囚禁了吗?公主。”红若问她,她一直以来都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王爷尽心尽力救她,那表情不可能有假;可是她肚子里的孩子也绝对不是王爷的,公主受委屈之后,王爷的所作所为,明明一切有好转,却又把她送到这里关起来,这到底是怎么了?
“应该是吧。”这种高门大院,她在宫里见得多了,背后都是一段秘辛的往事不可与人说。
她曾经在这样的院外,听到过里面有女子凄厉的叫喊,或者弹琴唱戏打发度日,或者一日一日里没有任何声音,就像活人冢一般阴森可怕。宜和信步朝宫里走,这里比之前的寝宫要大,只是更加冷清,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外都驻着重兵,不是囚禁又是什么?
日子波澜不惊地过着,又快一个月了,宜和的身子还是很灵巧。虽然关着,日用倒从来不少,按时按需地送来,例行公事地问她还缺什么。
自从住进来就再也没见过南宫千了,不用面对那种尴尬,让她心里松快又隐隐内疚。没有人打扰自己的时候,她就在想:最终,他肯放过自己吗?如果他肯放过,她接下来要怎么过?要接纳这个陌生的男人吗?从来的路上到现在,一切都不由得她把控,这种不能预知明天的感觉非常无助。
倚兰宫与扶阳王的兴庆宫其实挨着,那日送她们走,南宫千特意让他们绕道,感觉走了好远,其实不过一墙之隔。
他总是通过相连的门遛到倚兰宫,躲在一丛翠竹后面看她们主仆二人日常嬉戏。
她们荡秋千,做些小点心,锄草,洒些花种耐心浇灌,或者在院子里起舞,或在已经落败的荷塘边抚琴。宜和会的舞曲真多,可柔媚可刚毅,配合着武功,身段十分柔和,她的声音空灵婉转,好些不知名的词曲,听她唱来令人心旷神怡。
“红若,你不是一直都想学踏花行吗?趁我还能动,教你吧?”红若在绣婴儿的肚兜,宜和晃了几圈,实在无聊。
“可是,我没有武功。”娘娘跳踏花行那叫一个风华绝代,宫里盛大的宴会上,她曾远远见过,惊为天人,公主的舞步少了娇媚,多了些灵气,正合她的年龄。
“我就教你一些步法,不用会武的。要不要试试?”宜和折了两根花枝递给她一根。
“行!那我试试,如果不好看,您可不准笑话我!”
“肯定好看!”
主仆二人在荷塘边一招一式翩翩起舞,一粉一青,像两只大蝴蝶,红若陪练这么多年,还是有些功底的,她不及宜和轻巧,舞步更显扎实。跳到兴起,宜和拉住她的手臂将她抛起,两人空中旋转得如一朵并蒂莲花,原来这就是踏花行。
“公主!公主!不跳了!不跳了!快放我下来!”
“啊?”
“快放我下来啊,快快快快!”红若伸手拉她。
将红若稳稳放下:“怎么了?”
“不是奴婢说您,您太大胆了,刚才多危险啊!”
“哪里就危险了?我虽力道不足,但内力还行,摔不到你的。”宜和怪她扫兴。
“我不是担心自己,我是说您啊!现在都三个多月了,可不敢这么莽撞的。”
“哪有那么娇气?”宜和看了看自己平坦的肚子,默默地说。
一天那么长,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见公主意犹未尽,红若赶紧从里屋抱出琴,点好香炉,一个恭迎的手势,逗宜和抿嘴一笑。
“你呀,有耳福了。”宜和提了裙摆朝凉亭走去,顺便还亲昵地刮她鼻子。
“是——,谢公主赏赐。”红若调皮地福了福身子。
风传曲音,流水和声,传到敬阳宫里,引的南宫千信步来到墙根,侧耳倾听,好一首岁月和美!
南宫千抚摸着眼前的墙砖,干净的指甲划出一道细灰。他心理很挣扎,不知道怎样面对她。
不介意是假,介意的结果他也亲眼目睹了,阿诺是个决绝的女子,若真是心存芥蒂,他就只能失去她,这么多年来辛苦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相对于得不到,得到再失去让他更痛苦。
可是阿诺对这里并不留恋,她的开心那么敷衍那么表象,不是来自心底的快乐。无论多么欢乐的人群中,她都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像是一个认生的孩子突然被放到了新的环境,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她不想融入陌生的环境,鉴于尊贵的身份,周围人也并不主动接纳她。阿诺的欢乐或者痛苦在那张波澜不惊的脸上察觉不出任何痕迹,南宫千要的,从来不是这样的人。
南宫千以愚笨的方式包裹自己,也同时保护她,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建设去接受这个孩子,更无法承受她的离去。能隔着墙或者躲在角落里,看到她不敷衍不紧张地生活,他就觉得很好——或者借着这个让他内心复杂的孩子,他能得到阿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