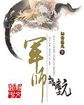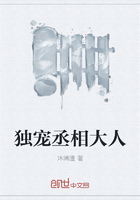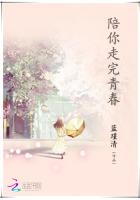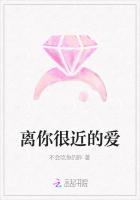活久见。
李清见到了传说中的黑衣宰相姚广孝。
前世民间是他说不尽的传奇故事。
有人称他为怪僧,说他长着一对三角眼,面貌十分古怪,形如病虎。
也有人称他为妖僧,智近乎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计谋百出,被传说得神乎其神的为跟刘伯温齐名的明初两大谋士之一。
人类不解之迷之一,密谈都喜欢在夜里,就如两人说秘密时,即使明知一公里内连个鬼影都没,都不自觉的放低声音靠近说。
米黄的蜡烛火下,李清看到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头和尚,甚至都没有影视中那仙逸的白胡子。
至于三角眼,这倒是有,单眼皮的人睑皮下垂后,眼睛看着都像是三角眼。
作为伪历史爱好者,僧道衍这种大神的故事怎么可能放过。
浓浓迷雾记录背后,李清唯一读出的是,这是一位博学的智者。
颇有几分和鲁迅相似。
他出生医学世事,自幼聪颖近妖,又有大毅力,十几岁爱上佛学,当即不顾家人反对,剃度为僧。
努力的学霸,老天都怕,他一生到时拜访求学,其学识涉及的领域很广,涵盖了儒、佛、道、兵、法等多家学术之言,并跟各个学派的学术领袖关系密切,从中学习了不少智谋。
是不是正因为博学,他看穿了儒家那一套,也看穿了朱元璋的分封藩王制度,才有传说他见到朱棣时,要送白帽子?
李清依稀记得,僧道衍好像写了一本书,诋毁以往的儒者,以至他姐姐和好基友都和他绝交了,说明他并不信奉儒家那套。
“钜子,这位是法号道衍大师……大师,这位是墨家当代钜子李清。”
朱棣给落座的李清和僧道衍互相作了介绍。
西瓜汁都没消化,李清就被朱棣的亲卫侍从请来了书房,听得朱棣的介绍,晓得朱棣是要他以墨家钜子身份来谈事的。
一学术门派之宗首,地位可不一般,所以才有朱棣先介绍僧道衍,再介绍李清,也是暗示僧道衍别轻视李清。
李清的年轻出乎僧道衍的意料,此时他已是过花甲之年,再大的意料在他面前也是风平浪静,人世之事,也早已洞透,闻言知意,立刻站起来躬身正礼道:“贫僧道衍见过钜子。”
李清连忙躬身回礼:“墨家第八十八代钜子李清见过道衍大师。”
等两人重新落座,朱棣轻声道:“不瞒两位,钜子,你那晚说的那句话,大师在十四年前和本王说过;大师,你十四年前和本王说过的那一句话,钜子在大半个月前初次见本王时也说了那句话。”
僧道衍闻言,惊异的看向李清,燕王之前有和他说过关于李清的一些的事及言语,但没有提及那句话。
那句话,是他用积累了近五十年的学识和见识才得出,是他对儒家的不满让他毅然迈出了这一步。
墨家同样得出了那句话,僧道衍心里震撼,墨家不愧为曾与儒家同为世之显学之一,墨家这是重新要入世争锋了吗?
墨家自秦汉以来,早就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刚才朱棣和他说及墨家现世时,他是抱着是骗子的怀疑态度的。
等朱棣把卫生条例的细菌说等说出来,本身是医学世家出身的他,立刻对以前医学上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顿开茅塞。
再等朱棣说完世界是圆球的、李清对儒家在朝廷中角色的分析及对北方之策略等后,僧道衍对墨家的态度已经升级为仰望。
他一生求学遍当世显世之学儒、佛、道、兵、法,了解这些学派之学术大都只是停留在学说理论上,说穿了玩就是文字游戏那一套。
墨家却已经身体力行,总结出了这么多学科。
僧道衍心底起波澜,他从不在意功名利禄,当他做出那个决定时,他只想告诉世人,儒家是不对的。
他是一个一生在求知践行的人,要以所学去证明自己的想法。
朱棣却继续道:“俩位都是有大学问之人,本王在此先感谢俩位的鼎力相助,本王也希望俩位能勿生间隙,相持相扶,助本王度过祸患,将来必有厚报。”
俩人连忙连称必尽力相助。
朱棣苦笑道:“两位,目下形势,本王该如何自处?”
“贫僧就抛砖引玉,说一说贫僧浅薄之见。”
僧道衍沉吟了一阵,看了李清一眼,沉声道:“王爷,陛下虽年老,但余威犹在,陛下心之坚定,已不可再争,贫僧认为王爷当韬光养晦,潜龙在渊。”
朱棣颔首,又看向李清问道:“钜子认为呢?”
“道衍大师所言极是。”
李清点头道:“王爷,古语有说,爱屋及乌,皇太孙是陛下对太子的感情寄托,皇太孙之位,陛下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护,此时任何一点异常都可能被陛下注意并以雷霆手段铲除。”
朱棣闻言,沉默了一会,叹息道:“父皇心思……唉,两位所言极是,是本王应死心了……两位怕是不知,五月底,父皇已令后军都督府,于沙峪立开平中屯卫,并令本王抽调北平都司属卫军士,与海卫山五所官军到开平修建卫城,设立开平卫。”
鞑靼残军,都像兔子一样被明军追着跑,此时修城立平卫确实能屏守北大门,但其中意义谁知道是不是仅为防守呢?
开城设卫的时间又选在此次北征大胜的途中,整个过程没问过他这个节制整个北平都司的藩王。
开平卫建立,北平已经被四周林立的卫所包围。
李清恍然大悟,难怪朱棣这么心急,刚班师回来,晚上还举行了庆祝宴席,才刚吃饱立刻就召集他和僧道衍。
李清不知道,朱棣心里已经绝望,开平筑城屯卫之事,让他对朱元璋彻底放弃了幻想。
此次北征,在彻彻儿山大败北元军后,他之所以要率主力骑兵部队乘胜追击溃军残部,最后在兀良哈秃城围城耀威。
就是想告诉皇帝,他这个儿子的优秀。
结果没迎来皇帝的赞赏目光,迎来的是开平筑城屯卫的旨意。
父皇的威严震慑力,他比谁都清楚。
争已无可争。
连僧道衍和李清都明确告诉他,父皇这边,就不要想了,才真的觉得悲愤。
僧道衍俩人又都预测了将来朝廷必定会行削藩之策,他集合两人所说的,梳理一番,也认定了将来消藩不可避免。
被削藩了,皇帝开心下能当个纵情声色的闲散王爷,皇帝一旦不开心了,就可能是被贬为庶人,甚至赐上一杯毒酒。
至于迈出那一步,历史就没有成功的先例。
区区一燕之地,如何抗衡朝廷百万大军?何况这北平治下,到时能有几个愿跟着他以身涉险?
前路,绝路!
哀莫大于心死,朱棣悲怆道:“两位,父皇心思我已明白。将来之路,亦似是绝路,区区一燕之地,如何抗衡朝廷百万大军?”
朱棣能逆袭上位,不单天下人想不明白,就连后世很多学者也想不通。
燕地可是距离京师有着千里之遥,以藩王发动叛乱,就如同一条大鱼去撼动巨舰,是一艘各方面都气势最盛的巨舰。
这样的君主,这样的统帅,这样掌权的学者们,空有山东强将,结果还是被逆袭了。
只能说,一旦儒家登台上位,什么事都有可能。
朱棣此时可不知他将来面对的,都是猪队友组建的敌人,绝望之情难免。
李清从他声音中听出了失去信心,这可不行。
看了眼僧道衍,见他还在沉思,李清连忙沉声道:“王爷宽心,朝廷虽强,但也不是强到不可撼动之步。”
李清顿了顿,吸引了朱棣和僧道衍的注意力,继续道:“王爷应知,这些年来,天下基本安稳,已由儒家登台主政。而儒家那一套,最喜欢的就是马放南山,钻研锦绣文章、吟诗作赋,以彰显所谓才情,实则是对天下无一文之利,以至边地以内,此时基本上已经是文恬武嬉之态。”
李清此时仍不忘在朱棣面前插儒家一刀。
“特别是各都司卫所将士,当年跟随陛下征战四方的将士大都已老去退役,现在各都司卫所将士,基本上都是新生一代,是并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新兵。”
“所以说,到时朝廷看是拥兵百万,实纸老虎也,不堪一击。”
“而王爷麾下将士,连年与鞑子交战,都是经过铁血洗礼的老兵,实战经验之丰富,足能以一抗十。”
“所以说,王爷之忧,不足为滤。”
李清说完,僧道衍拍掌激动道:“王爷,钜子之言通透,大善。”
听这么一说,朱棣想了想,实情确实如此,边地以内,十数年不曾有过战事,他本身就精通军事,明白将士一旦松弛下来,战斗力就所剩无几。
至于李清说的是儒家原因,他虽然不全信,但也再次对儒家印象减一分。
这才宽心不少,信心微微拾回,朱棣颔首道:“钜子言之有理。”
顿了顿,朱棣继续忧心道:“不过,内地将士可能武备松弛,但边地将士都和本王麾下一样,常年征战,战力不输本王麾下,到时朝廷一纸调令下来,只得听令发兵围攻北平。况且到时之事,燕地之将士能有多少人愿意跟本王以身涉险?”
僧道衍想都不想,直接道:“王爷无须忧虑,到时朝廷行的必是以削藩之名义来对付王爷,兔死走狗烹,各边塞藩王难道不怕王爷之后,重涛覆辙?所以,届时即使朝廷发令给各边地藩王们,藩王们也必定会找借口拖沓不敢参与。”
李清插道:“王爷,道衍大师所言通透。咱们只要不被列为在削藩顺序上首位,届时,历历在目的例子之下,藩王们必感同身受,激起各地藩王的恐惧,至藩王暗地与朝廷决裂。”
僧道衍道:“至于王爷担心到时麾下,王爷也无需忧虑,贫僧以为,不宜过多拉拢,授人以把柄,陛下尚在,时间亦尚长,人心易变,当以王爷麾下三护卫为主力,将来再随机应变行事。”
朱棣听俩人一波分析,才觉前路非绝路,心大安,激动站起来,朝俩人躬身道:“二位大才,我之张良诸葛亮也!能得二位鼎力相助,侥天之幸!我朱棣立誓,将来事成,必与二位共富贵,若违此誓,人神共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