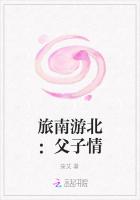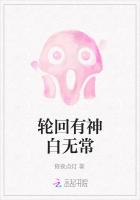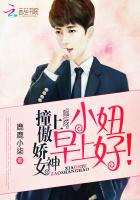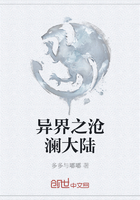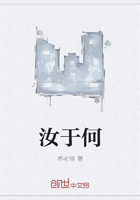分别之三,隔与不隔。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 “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 ”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简单地说,就是情趣和意象相互契合,见景即生情,就是不隔;意象模糊凌乱、空洞,情趣浅薄粗俗,不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境界,便是隔。
分别之四,即大气象和小气象。这种分别没有实质的意义,但可以看到诗人的胸襟和气度。不能以此作为诗歌优劣的标准。正如王国维所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三、达到诗歌最高境界的三境界。前二者为诗歌本身而论,这里的三境界着重指的是成为大诗人须经历的三种境界。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第一境界,即对现状的不满,对理想的渴望;第二境界,即艰辛的努力,韧性的坚持;第三种境界,即苦苦追寻后的发现,长期修炼的顿悟。
诗歌舞乐
文化渐进,三种艺术分立,音乐专取声音为媒介,趋重和谐;舞蹈专取肢体形式为媒介,趋重姿态;诗歌专取语言为媒介,趋重意义。三者虽分立,节奏仍然是共同的要素,所以它们的关系常在藕断丝连。
——《诗论》
诗歌、音乐、舞蹈本就密不可分,有很深的渊源。
原始人类歌舞是一体的,唱歌就必须跳舞,跳舞也离不开唱歌。在博托库多民族歌舞用同一个字表示。近代欧洲文“ballad”一字也兼含歌、舞二义。而抒情诗则沿用希腊文lyric,原意是说弹竖琴时所唱的歌。按照阮元的说法,《诗经》的“颂”原训“舞容”。这就显现出很明显的颂诗是歌舞的混合的痕迹。惠周惕也说“《风》、《雅》、《颂》以音别”。汉魏《乐府》有《鼓吹》、《横吹》、《清商》等名,都是以乐调为诗篇命名。这些事实都证明诗歌、音乐、舞蹈在中国古代艺术中是相混合的。
《诗经》中的诗大半都有乐,但除《颂》之外几乎都没有舞蹈。即便《颂》中的舞蹈也是经过朝廷乐官的形式化,不复有原始舞蹈的面目了。《楚辞·九歌》之类为祭神曲,诗、乐、舞仍相连。汉人《乐府》,诗词仍与乐调相伴,“舞曲歌词”则独立自成一类。因此可以看出这三个成分中分立最早的大概就是舞蹈了。
中国旧有“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的分别。“我歌且谣”的毛传人“徒歌”完全在人声中见出音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声音的曲折随情感的起伏,与手舞足蹈诸姿势相似,“乐歌”则歌声与乐器相应,意识到节奏、音阶的关系,而要把这种关系用乐器的声音表出,对于自然节奏须多少加以形式化。所以“徒歌”理应在“乐歌”之前。最原始伴歌的乐器大概都像澳大利亚土著歌中指挥者所执的棍棒和妇女所敲的袋鼠皮,都极简单,用意只在点明节奏。《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激’”之说,与澳大利亚土著风俗相似。现代中国京戏中的鼓板,和西方乐队指挥者所用的棍子,也许是最原始的伴歌乐器的遗痕。
诗歌、音乐、舞蹈都是表达人们内心情感的不同形式,彼此辉映,相得益彰。
《乐记·乐象篇》中说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无论诗、歌或舞,都是由人的内心出发的,然后才表露于外。艺术形象本于人的内心,然后才有乐舞等的外在表现。
在《诗经·大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充分说明三者都是人们表达情感的形式。舞蹈的本质与诗歌及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三种艺术形式都不仅仅是思想情感的发泄,更是情绪的宣泄,在意境上,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是音乐的回声,诗歌是舞蹈的内容,舞蹈是诗歌的升华。
中国舞蹈家吴晓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作了验证。他认为: “任何舞蹈在艺术形象上都必须通过音乐,才能把它的‘意思’完整地表现出来。”如舞蹈《春江花月夜》,我们可以看出,假如没有音乐,这样的舞蹈该是多么的干瘪无味。同时,通过舞蹈所表现出的诗歌内容,是多么的丰满与深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诗歌、音乐、舞蹈有共同的起源,在最初是混合的。在人类发展和进化过程中,它们担负着共同的使命,其中节奏它们所具有的共同命脉。在原始时代,诗歌可以没有意义,音乐可以没有和谐,舞蹈可以不问姿态,但是都必有节奏。后来三种艺术分化之时节奏仍保存在其中。但于节奏之外,音乐尽量向和谐方面发展,舞蹈尽量向姿态方面发展,诗歌尽量向文字意义方面发展,于是彼此距离遂日渐其远了。朱光潜先生认为,节奏是诗、乐和舞蹈三者的共同因素。而诗与乐的关系尤其密切。论性质,在诸艺术之中,诗与乐也最相近。它们都是时间艺术,与图画、雕刻只借空间见形象者不同。节奏在时间绵延中最易见出,所以在其他艺术中不如在诗与音乐中的重要。诗与乐所用的媒介有一部分是相同的。音乐只用声音,诗用语言,声音也是语言的一个重要成分。声音在音乐中借节奏与音调的和谐而显其功用,在诗中也是如此。
中国重“情”,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曲,诗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与音乐密不可分。毛诗大序中写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足以说明诗与乐之间的联系。
古诗之于古人,最大的用处之一就是用来吟诵。诗仙李白就说过: “余亦能高咏”(《夜泊牛渚怀古》),只是“斯人不可闻”。古人的诗本身就具有了音乐性,以吟唱的方式,借以抒发自己的怀古感今的情怀。
不同体裁的诗的题目与乐是相通的,如歌(《长恨歌》)、行(《琵琶行》)、曲(《圆圆曲》)、调(《清平调》)、操(《烈女操》)、引、乐、谣等。因为满腔的豪情或悲情需要抒发,中国历史上许多英雄无意中成为了诗人,如项羽在《垓下歌》中吟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在四面楚歌声中,唱出英雄末路的挽歌;而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则是得酬壮志的豪迈心声。胜利者刘邦的这首歌中也响彻着类似焦虑与前途未卜的悲音,这就难怪他在配合着歌唱而舞蹈时,要“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在宋诗中有一首姜夔的《过垂虹》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过垂虹》中小红低唱的“新词”指的是《暗香》和《疏影》。这两首词是姜夔在过垂虹之前刚刚应范成大之约写成,并专门为其配曲的。词、曲珠联璧合,传唱不衰。此种例子,不胜枚举。
看过了中国的诗与音乐,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西洋的诗乐。
在西洋神话中,有几个主要的大神,比如宙斯、朱庇特、雅典娜,还有一个重要的神就是阿波罗,他也是青春之神,并掌管诗与音乐。可见诗与音乐是十分接近的,并且也象征着年轻。据希腊神话所讲,众神之首宙斯的手下有“九缪斯”,分别掌管情诗、史诗和天文、历史等各方面的事情,其中一个手中抱琴的女神就是负责掌管抒情诗的,这就表明诗神与音乐之神是一个人,也说明诗与音乐在远古的西洋是等同的。
中世纪的时候,西方出现了行吟诗人,即最早的嬉皮士。他们不守礼节,自己写词、作曲,并且自弹自唱,他们把诗向音节化发展,更拉近了诗与音乐的关系。在英文中“number”是数字的意思,但它的复数“numbers”就是诗的意思,也是音乐的意思,也可以用来表示计数、音节。
英文中诗的题目和音乐的题目很多是一样的,比如说英文中“song”这个词,表示歌曲,但它也有诗的意思。像莎士比亚有百首短诗,称为“song-let”,也可以译为“小歌”,所以说,诗的形式通曲的形式,并且诗与歌是不可分的。中国古代称呼诗为“诗歌”,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称为“歌诗”,比如《李长吉歌诗》。
诗与乐密不可分,古人经常用诗来谱曲,以诗入乐。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王维的《送元二史安西》:“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来入曲,成为《渭城曲》或《阳关三叠》。还有李白的《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也是很典型的例子。
另外,在西方,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苏格兰的民谣,有一首很古老的诗被谱了曲子,后世传唱,但后来彭斯发现民谣曲中的诗词不是很好,于是诗人又对其进行了改写。古往今来,这种从诗变为音乐,再由音乐回到诗的例子很多,所以说诗与音乐的确密不可分。
以诗状乐可以说是诗与乐的另一种关系。但中国诗的平仄、五声,拿来形容音乐还是不方便的,所以诗人的筹码不多,直接来描写音乐恐怕不太容易,文字的声音再美还是比不过音乐,那就往往只能拿诗文来形容听音乐的人的感受了。最有名的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已经有四个动词了;“拢、捻、抹、挑”;“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已经有拟声法了;“嘈嘈切切错杂弹”已经有声音出来了,然后有形象“大珠小珠落玉盘”,虽不是直接对乐声进行描写,但也有音乐在里面了,这是用文字来描写音乐。
李白在他的律诗《听蜀僧睿弹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中直接运用比喻,将琴声比喻成从深谷里传来的松风,这还是有点写实的形容。“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这句就是写他做客时的心情了,听过蜀僧弹琴、经过流水清涤之后,心好像流水一样,这是一种象征,已经是写音乐带给听者的感觉了。“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李白写音乐的方式和上面提到的白居易是明显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诗本身的音乐性,也就是文字本身的音乐性。李清照一首很著名的词描写她迟暮的心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字,写得再好也不见得比音乐好听,可是她的可贵之处在哪呢?在这几个字,它不但有音调还有它的意义在里面,能够用音调来切合心境就非常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