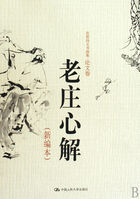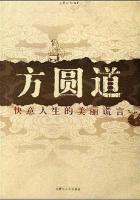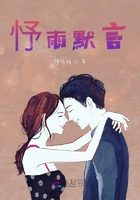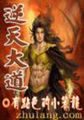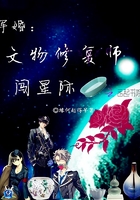世界上任何一项艺术都有它的一个原则:太整齐了往往就会显得单调,变化太多就会变成混乱。在整齐与变化之间作一个适当的安排,来求得一个平衡点。所有的艺术都要考虑到一个这样的美学原则。我们举一首唐诗作例子,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如果我们把每一句减掉一个字,它的意义完全一样。“少小离家老回,乡音无改鬓衰。儿童相见不识,笑问客从何来?”这样的六言诗并不好,因为它太整齐单调了。六言的太乏味了,七言的有偶有奇、有正有反,整齐中有变化,变化中又有约束使它整齐,这就是诗的一种艺术,诗的韵律,诗的节奏。这也是作诗所必须遵循的规则。
诗画相映
诗与画同是艺术,而艺术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情趣化。徒有情趣不能成诗,徒有意象也不能成画。情趣与意象相契合融化,诗从此出,画也从此出。
——《诗论》
同作为人类的艺术结晶,诗与画经过各自的发展与交融,互异又互补,延伸着艺术的精神和生命,共同追求着“美”的艺术表达,从“形”到“神”,从“物”到“心”,景与情,境与意,诗与画关系是如此紧密,“诗中的画”和“画中的诗”是对艺术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双重吸引。
谈诗与画的关系,不能不提到王维,只因为苏轼对其诗与画的评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不仅是因为王维诗中的禅意与画境,还因其对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开创性贡献。王维独创泼墨山水,发挥了水墨在山水画中的重大作用,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画类形式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西方的风景画相区分。
区别之一:诗中有画。
朱光潜先生说过,诗画同是艺术,而艺术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向的情趣化。诗和画都是人类对自然对生活的艺术表达方式,自古诗画同源,它们统一于人的审美感知和个人所具备的审美表达能力。郭熙在《林泉高致》云:“更如前人言,‘诗是无形画,画是有行诗。 ’哲人多谈此言,吾之所师。余因暇日,阅晋唐古今诗什,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董其昌云:“诗在大痴画前,画在大痴诗外。 ”王维或许不是最先将诗与画结合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至今为止把诗与画结合得最完美的人。“诗人与画手,兰菊芳春秋。又恐两皆是,分身来入流。
”王维并无分身之术,但正如苏轼在《题王维画》中所说,“摩诘本词客,亦自名画师。平生出入辋川上,鸟飞渔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声活上流肝脾。行吟坐咏皆自见,飘然不作世俗辞。高情不尽落缣素,连山绝涧升重帏。 ”他既是一个称职的诗人,也是一位不错的画家。画意在王维诗中的体现就是他对诗的情与境的营造。例如他的《寒食汜上作》:“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 ”后一句完全可以入画。又如《终南山》画,“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两句又将人物的动态也融入了画意。他许多诗中的断句,画意则更浓。《青轩诗缉》中“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之“带”字、“当”字极佳。这一联画出了孤城拥斜阳,行人依稀见的景色,非得画中三昧者不能下此二字。
长期的贬谪与隐居,加上王维自身特有的画家素质与禅学修养,使他对山水的审美感受力有很高的灵敏性和深刻性,笔下的景物达到了与自然契合无间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后人多重视的是王维的山水之作。例如他写的落日夕阳之景,黄昏时的光影变幻,云色浓淡,时常引发读者的诗情画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出了边塞古诗的艺术典型。《送邢桂州》分野中锋变,阴晴众壑殊。”是最难着笔又分阴阳向背的青绿山水是一幅色泽鲜明的画卷。而“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都艺术地表现了落日时的景色,此时也亦是诗人诗情最浓的时候吧。王维诗中的画意多来自清新而得自然之天趣的。但有时他也写得相当日落江湖白,湖来天地青”,描述的整个大地仿佛被白光青色充满,“壮阔,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
有诗人那种澄心关照的审美态度,才有王维诗中的禅意,从静观自然中获得美趣,从而他写出的诗往往具有禅境、画境。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写出了无限的静感。正如皎然所说“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穴不鸣,乃谓意中之静”。王维参禅悟到妙处时也说“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此种闲适之趣即为“禅趣”。可见禅寂,由王维之化,已然成为了一种艺术观照,一种审美态度。
区别之二:画中有诗。
画中有诗的情况,始自中国山水画。
清代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曰:“盖山水画学,始于唐,成于宋,全于元。”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魏晋时利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这些都是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虽然稚嫩,但是为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勃然兴起,出现了一批山水画家、山水画作以及第一批山水专论。据史料记载的有《剡山图》、《吴中溪山邑居图》、《九州君山图》、《秋山图》、《大山图》、《山居图》、《山江树图》等。我们可以从宗炳的《山水序》,王微的《叙画》等山水论中认识到当时的山水画发展情况。
宗炳提出山水画的“畅神”功能,提出“人以神法道,山水以行媚道”的观点。画家眷念自然山水,饱游沃看,寓自然万趣于心,用笔墨巧妙地表现,“类之成巧”,观画时“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其论及景物远近与视觉关系有,“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行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以寸眸,诚去稍阔,则见其弥小”。同时他还论及了山水画的一些具体表现手法“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迟,体百里之迥”。同时,宗炳亦“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蘅岳,困结于衡山,怀尚平之志”。在他年老的时候,不能再游历于自然山水,但他用画笔表现他心中的山水,“凡所经历,皆图于壁”,“卧以游之”。而王微提出了情与景的关系,“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
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山水画成熟并全面发展的时代。此时出现山水画的主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笔墨”理论, “三远”画理和思想的建立,以及重视心迹与精神的文人画理论,如“萧条淡泊”,“闲和严静”,“萧散简远”,“参禅识画”,“平淡天真”,“高古”等的提出与形成。至元代山水更向逸取发展。代表人物五代有荆浩、李成、范宽、董源、巨然等,北宋出现了卫贤、郭忠恕、黄文贵、高克明、许道宁、郭熙、王冼等山水画家,还有如苏轼、“三宋”(宋道,宋复古,宋子房)、晁补之、米芾父子,南宋则有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南宋四家”以及赵伯萧、赵伯驹、萧照、马之和、梁楷等,“皴法大备,形成山水之极峰”。明清山水大家有戴进,沈周,吴伟,唐伯虎,文徵明,仇英等人。
在文人山水出现以前,“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人们看到的诗与画主要是它们的异,朦胧的意识到诗与画内在的同。达·芬奇说,诗是听觉的、抽象的艺术;画是视觉的、形象的艺术。在直接的表达美感的形式下,画是胜于诗的。这极大地提高了绘画在西方的地位!但在论及诗与画的关系时,他认为诗与画的区别就如想象与实在之间的影子和投射影子的物体之间的关系,这就人为地提高了画的地位,而将诗放于画之下,认为诗用语言把事物陈列在想象之前,而绘画确实地把物象陈列在眼前,使眼睛把物体当作真实的物象接受下来。诗缺少一种形似,不是像画一样依靠视觉产生形象。他甚至提出一个艰难的选择:既然绘画为哑巴诗,那么诗也可以叫瞎子画,哪一种创伤更重,是瞎眼,还是哑巴?
这与中国的诗话比较就有些不同,中国在“和”与“同”的思想的指导下,看到诗与画的差别,是为了更好地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清代沈宗骞认为“画与诗,借诗人陶写性情之事;故凡可以入诗者都可以入画”。画家意识到诗与画各有所长,各有其短,于是直接将诗题跋到山水画里,以互补其短。南宋吴龙翰云: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诗中本就有画,现在画中也有了诗,这使诗与画亲密的结合成为可能。宋代的文人参与绘画,大都题诗在画前或跋在画后。中国的题画诗,把文学和美术二者结合起来,在画面上,诗和画,妙合而凝,契合无间,浑然一体,成了一幅美术作品的构图上、意境上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诗情画意,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可以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种极其特殊的美学现象。关于诗画结合的开端,过去论者意见不太一致。有的人认为可以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便是古代诗画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有的人认为题画诗滥觞于宋代,理由是宋代以前绘画作品大都缺少题跋。钱杜的《松壶画忆》便说:“唐人只小字藏树根石罅,大约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始有年月纪之。”中国画和题画诗都是一种独到的艺术形式,它们虽为美术和文学两个范畴,但画为视觉的艺术,诗为语言的艺术,两者在构思立意上有着不可替代之妙。清代孔衍拭《石村画诀》说:“画上题款诗,各有定位,非可冒昧,盖补画之空处也。如左有高山右边宜虚,款诗即在右。右边亦然,不可侵画位。”以上“补画之空处”、“不可侵画位”这两句话,就是给题诗款在画面上,下了极明确的定义。 “补空”二字,也就成为画家题诗款时的一个谦虚名词了。
这里,题画诗和单为破除画面上单调与平凡所加的题款亦是有区别的,前者因画不能尽意,借诗以名其意,诗画互相补充、互相阐述,称之“画写物外形,诗传画中意”。后者通常都是为便于查考,只题上作者名号和作画年月,有的大约诗不美、书不工,以避开弱点所至。题画诗溢满着画幅的风采,因此长于文辞书法的画家,常将长、短不一的诗文搬到画幅上去,使其产生一种诗绘并工、附丽成观的艺术效果。画家为题画诗创作所发生的美感,常在郑重的注意和研究之中。有的在一幅画画成之后,再考虑诗句的长短与题诗的地位如何与画面相配合。有的则在一幅画的落笔前,也将题画诗的地位同时酝酿在内,或因先有长诗预先多留空白,为题写之用。诚然,诗文有精粗美丑之分,书法有工拙高低之别,若诗跋繁芜,书法不精,这类画作大都会被人们淡忘。
据中国美术史记载,宋元时期普遍出现题画诗形式时,中国画即披上了浓厚的文学色彩,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便成了赏析文人画的一种创作追求或审美理想。画家既作诗又作画,不仅能起到开阔视野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丰富画面的意念和启发观赏中国画的想象作用。
孤寂诗人
诗人所以异于常人者在感觉锐敏。常人的心灵好比顽石,受强烈震撼才生颤动;诗人的心灵好比蛛丝,微嘘轻息就可以引起全体的波动。常人所忽视的毫厘差别对于诗人却是奇思幻想的根源。一点沫水便是大自然的返影,一阵螺壳的啸声便是大海潮汐的回响。在眼球一流转或是肌肤一蠕动中,诗人能窥透幸福者和不幸运者的心曲。他与全人类和大自然的脉搏一齐起伏震颤,然而他终于是人间最孤寂者。
——《谈美》
每天我在写着诗歌,可却不知写些什么?除了思念就是苦痛,好像人间没有快乐。人生如梦多少牵袢,诗人心里总有寂寞,忧国忧民又有情愁?化作首首天上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