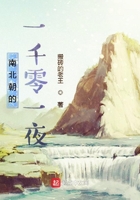悬崖上,两个人影独立,对峙。
我双手捏着银针,牵着一根紫金细线,体力渐渐不支。鲜血慢慢穿过针孔,从线上滴下落到泥里,一滴,两滴,三滴……
“宫主,别再挣扎了,您都杀了这么多人,也算是报了仇了,”绝月明比剑慢慢横过眉端,魅惑的双眼扫着剑上血迹,口气勾引暧昧,嗔道,“您的仇报了,月明的仇可是还没报呢,您就别反抗了,从了月明的愿吧。”
“休想,”我退守崖头,擦去嘴角的血,“是本宫瞎了眼,养了你这条毒蛇,我自己作的孽,我自己清理门户。”
“清理门户?哈哈哈哈哈,我知道我现在不是你的对手,”她知道我今天在劫难逃,所以要好好利用这点时间,折磨我一番,“不过,追功散的药效已经快发作了,趁着现在我良心尚在,你乖乖地过来求饶,别逼我出手。”
我轻蔑地看着她:“贱人,就凭你这下三滥的招就想杀本宫?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这本事月明还真没有,”她身姿轻佻地在我面前走着,并没有生气,“不下三滥的招月明倒是有,如若宫主想看看,那月明也不妨给你看看,让你死前也多看看人事。”
“要死的人是你,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本宫的一条狗!你娘也是。”
听到我提起她娘,她气急,猛睁艳目,把手里的剑扔下:“仇千槿!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要!哼,我倒要看看,你撑得了追功散,能不能也过得了邪真这关!”
她嘴里轻轻念嘬蛇语,身旁的草丛突然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一条两指宽的黑皮大蛇游出来,嘴里嘶嘶地吐着信子,朝绝月明脚上攀去。
她逗弄毒蛇一会,便把它从臂弯里取下,放在地上:“想看真相吗,我会让你看明白的。”
那条蛇对我似乎有所忌惮,迟迟不敢过来。
“出来吧,墨尘。”
在绝月明的话下,她身后出来一个俊逸男子。
伏墨尘从她脑后移出,用一双冰冷的眼睛盯着我,像在看一只即将被收服的野兽。
“是不是很精彩?”绝月明拍拍手,笑容是从未有的畅快,“昔日枕边人,如今变成了分外眼红的仇人,听上去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
“邪真怕她身上的魂气,只要你弹奏倾魂曲,把她的魂气压下去,她就死定了,”她对男子说完,便疯狂大笑道,“我等了这天,等了整整二十年!仇千槿啊仇千槿,你知道每天背着灭门之仇,眼睁睁看着仇人好好地活在面前什么都不能做,自己却还要靠着她苟延残喘的感觉吗!”
见伏墨尘走到悬崖一边坐下,一直抱琴不动,她上前质问道:“怎么回事,墨尘,你不会还舍不得这个女人吧?你舍不得她,她可舍得你,你别忘了,你爹娘——”
“——够了,”男子声音似乎也压抑许久,“开始吧。”
男子摸琴,诡异的琴音在我耳边响起。
耳膜钻心地疼起来,我捂着耳朵,看着这对男女。
那条蛇见我身形潦倒不堪,张开盈盆大口,见机飞快地从地上朝我窜来。在它跃到我眼前的那一刻,我在那双那黄幽幽的竖瞳里,看到自己痛苦的脸色,头顶颊边影影交叠。
“是影魂分离!”那女人叫道,“她果然练了芦花风雪。”
我使出最后的气力,退后一步,侧身躲过,趁它尾巴卷缠上我双腿之际,转脸左手绕线扯住,把蛇七寸之处钉入地面,另一边把针尖狠狠弹进蛇口。
银针染红刺出,蛇身上的针孔里缓缓流出绿色乳液,我连忙翻身滚到一边,接着伏地摇晃站起。
那蛇摔到地上,震得灰尘扬起一片。
“邪真!你居然!”
伏墨尘见状把琴弦重落,曲音到达高潮,捂耳收效甚微,我感觉自己脑子在不断地渗血,瞬间天旋地转起来,站不住地往后倒去。
在直直坠落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那绝月明抱着蛇在疯狂地大笑,慢慢地,那张如毒红罂粟般妖冶的脸被雾气模糊,最后居然变成了南苍的脸。
我惊醒,摸到被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松口气,原来是梦。
掀开被子打算去倒杯水喝。
门被打开了,单相随急急地向我走过来,脸上全是担忧:“公主,您没事吧?”
“没事,”我回想刚刚那些交叠在一起的画面,有点苍白无力,“就是做了个梦。”
那梦实实在在,那些声音真真切切,都是我上辈子的梦魇。
可是我没想到,那么单纯善良的南苍居然也会欺骗我……每个人都披了一层皮,这世界上,到底还有什么是真的?
“你去睡觉吧,我等会就好了。”我知道自己此时的笑肯定很惨然。
他站着看我对他这般笑,更加不愿离开:“相随不困。”
我看了眼窗外,知更不鸣,夜锣不响。
今天的黑夜是一个十分透彻的黑夜。那番没有一丝杂质的黑,至尊至贵。然而,这番黑给我一种凝固的感觉,我和单相随都被凝固在这黑夜里,不能动弹。只不过心脏还在跳动,呼吸仍在微微匀长。
单相随在房里陪了我一夜没睡,我虽过意不去,但是居然也说不出什么劝辞。
看我在天破晓时终于睡着了,他才悄悄掩门离开。
“公主。”他看我一动不动地,一直盯着一株干死的牵牛花上面的一堆蚂蚁忙忙碌碌地看了半个时辰,眼里是浓浓地担忧。
我失去了往常般的神采,在他叫我的时候也是慢半拍地看过去:“嗯。”
“公主,你想去打猎吗?”
他似乎觉得这样的我很不对劲,要做点什么让我振作起来才行。
“打猎,”我注意力分散了一点,捕捉到亮点,反问,“你说打猎?”
他看到我来了点兴趣,走过来和我一起坐到台阶上:“是啊,公主之前很喜欢去打猎呢。”
“可是这前不着山,后不着野的,哪里来的猎打?”我泄气,又把念头压下。
单相随将手先在我眼前摆了摆,然后在那株紫花上方一抹过,洒下了什么东西:“你看。”
我随他手的方向看去,那株花居然一改颓态,干枯的花面慢慢充盈起来,接着整个翻转展开,像一把插在沙漠里的油纸伞突然打开,生机勃勃地再次支棱了起来,
什么变戏法,好厉害。
见我兴致已经被打开,他道:“这个叫如梦令,会刺激枯萎的植物的叶肉,让它们暂时起死回生。”
我问:“那是不是等会它就会再次回复原样?”
“嗯。”他眼里尽是温柔。
“这么神奇?那用在死人身上岂不是也可以让人暂时复活?”回光返照确实挺吓人的。
“这个倒是不行,”他说,“生死有命,人死重生有违伦常。人和植萃之间差异太大,这株花也是刚刚枯萎不久,尚存一丝气息,所以如梦令才能起作用。”
重生有违伦常?原来我是不伦之人。
不过,换个想法,老娘就不是常人!
“好了,”小随站起来,把手递给我“公主现在想去打猎了吗?”
“想是想,但是不知道去哪里打呀。”
他说:“公主这么快就把公主府忘了,它可还在刍山呢。”
“对哦,”我恍然大悟,把手放到他手上,被他拉起,“走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