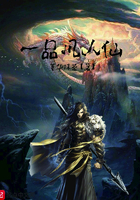吃了面,二人心满意足地往东桥去,看了半个时辰的戏曲之后,屈则申提出建议,又去集市买了东西。
“中午有什么事?”楼敬甚至看见屈则申一些布匹,好像是要去装饰什么似的。
“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想不想和我去刑部?”屈则申生硬地岔开话题,道,“刑部都听尚书大人的话,下面还有三位侍郎大人;虽然我只是督卫,但很多时候我都在外面跑,而且只需要听尚书大人的话,别人都管不着我。你要是来了,我们兄弟俩就天南地北地跑,多自在。”
楼敬想了一下,这种吃官家饭坐官家车水睡官家床好像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怎么说嘛,给个准信。”
楼敬想了想,实话实说:“我想先去一趟紫流林。”
屈则申扭头瞧着他,眉毛一高一低:“去哪里干什么?你不会是想着继续学武吧?”
“三哥,学无止境啊。”楼敬被他滑稽的表情逗笑了,“我这紫流林功夫,要是不去寻根,很容易就走了歪路,走火入魔;到时候再去找紫流林大师就没用了。趁现在我还能驾驭那些蛊术,还是要未雨绸缪的。”
“诶,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学这个紫流林。师父那么多绝学,八大门派无所不极,刀枪棍棒样样精通,怎么就不学点别的呢?你若喜欢刀,逸盘山有的是刀功刀法;喜欢剑就学天剑门;喜欢棍棒学珂舟棘;腿脚掌法属百木崖一绝;不想打架就学薇香山或者异燹教;想学仙术就去神武楼——说起来前年神武楼的安广厦还来我们苇崖山找二姐呢。笑死人了,说什么当年被打败一次,这次一定赢回来;也不想想二姐那功夫到了什么地步,要不是她不乐意参加什么比武大会争夺武林盟主,哪里还轮得到他们叫嚣?”
他本来数着江湖的八大门派,突然又把话题扯到二师姐身上:“二师姐那才是真正的高手,淡泊名利,心无旁骛,一心追求武术的至高境界。什么名头都不放在眼里。我要是能学这个心态,倒也不至于进刑部,四处奔走。”
楼敬忽然想起白鹿歌,道:“那涧瑶峒的折柳大师,很强吗?”
“啊?谁?”屈则申正在观赏一幅画,有些不太专心。画摊老板带着斗笠,低着头,看不见脸,但是可以看见花白的胡子从斗笠下面露出来,老先生好像在打盹。
“折柳大师,铁麟枪的折柳大师。”
“呵……折柳小儿……”
老板冷不丁地说了一句,带着不屑。
他的斗笠打量了一下楼敬,又望着屈则申,沙哑着嗓门道:“十文钱,这画给你。”
屈则申低头看他,说:“这画值半座奋谷城。但我没钱,所以就看看。说实话这玩意儿最好挂在没太阳的地方,晒久了里面的松树就褪色了。”
楼敬抬头看了看那幅画。枫霞师父闲着没事会给他们一些书画,然后大夸特夸,告诉他们哪里好哪里妙,从选墨的深思熟虑到作画的起势,再到整幅画的细节和气魄,从头到尾点评一番,津津有味。久而久之,几个徒弟对这些东西都有些研究。屈则申这些年跑来跑去,又在刑部,恐怕对这些东西更加了解。
而眼前这幅画,和以往那种见过的山水画区别在于对一些细节的不同。
楼敬看了看,想起师父说过的一句评价,就是“闻得到画里风的味道”。
“这是赢韩先生的鹰……”楼敬看得少,不甚明了,只看得出略有不同。
“啊,这鹰画得确实好。你看,别人画的时候,一直在画神,画鹰的洒脱和奔放;翅膀朝上,最后都喜欢甩一下;但这只鹰,翅膀朝下,也不甩。”屈则申说着回头看着楼敬说,“你也看得出谁画的?”
楼敬有点不好意思:“赢韩先生的鹰让我印象深刻啊,画得准。”
“确实,要不是我去过这里,我都不知道这是剑坞山。”屈则申又看着画,半天感叹一声,“这鹰好啊。”
“为什么?”楼敬问道。
“剑坞山的鹰一点都不洒脱奔放……”屈则申笑了一下,“都是冤魂。”
楼敬看着师兄,又看看老板,才发现老板的斗笠摘了,苍老的不成样子。
他的眼睛像泥潭,黄得浑浊。双手叠在摊位上,布满伤痕,像一块树皮。老树被风吹过,在熙熙攘攘的市井中攒动。
“你叫什么?”
“屈则申。”屈则申一手提着布料,一手抱着酒罐。他扫了一眼摊位,说,“渐金节快到了,那可是个喜庆的日子,画点菊花都比你挂山水画强,牛头不对马嘴。”
老先生却好像没听见他的劝告,只是囔囔地重复着屈则申的名字,他最终咧嘴一笑,道:“可是去抓小猴子的屈大人呐?”
“谁?什么猴?”屈则申身子往前一曲,像没听清楚一般。
老先生连连点头,笑得更欢了:“下次见着小猴子,告诉他,老苏家的姑娘在槐山剃度出家了,他活该!哈哈哈。”
“啥?”屈则申一头雾水,看看大笑中的老先生,又看看楼敬,那眼神仿佛在问楼敬“这老板怎么回事”。
楼敬摇了摇头,但感觉是在说传说中的江洋大盗,候不息。
屈则申看了楼敬一会儿,又看着老板,不明就里地说了一句:“有机会一定啊。”
“他活该!哈哈哈哈……老先生看起来笑得很开心,笑声却越来越小,感觉随时都会断气。
屈则申头皮发麻,示意楼敬赶紧离开小摊,楼敬虽然很想问清楚,但这老板还是在笑,却已经不咧开嘴,只是肩膀在不断地耸动着,满眼像坠进昔日去的模样。只得追上屈则申,小跑离开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