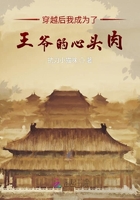次日凌晨,楼敬猛地惊醒,才发现窗没有关,遥远的传来打更的高唱,城外高山有阵阵枭鸣,月亮还在天边,月光斜着洒进来,在角落停住,隐隐约约,只见一双长靴摆在角落的月光中,长靴的主人坐在房间角落的板凳上,咕噜咕噜地喝着酒。
“三哥?”楼敬揉揉眼睛,惊喜道。
男子回过头,露出一口白牙,随即转过身来,悄声说道:“六弟,好久不见。”
眼前的男子披散长发,额头上有一条泛光的护额,黝黑的皮肤紧缚着健硕的上身,微凉的夜色划开他的衣物,露出垂到胸口的晶石挂坠。
他的名字是屈则申,楼敬的同门师兄,顺位第三,今年二十五岁,在师父那里学了七年和意楼的掌法,下山时正好是楼敬入门第二年。下山之后从东洲跑到漠北,哪里有擂台就往哪里去,很快就打出一片名声,在大师兄的引荐下招安,顺利进入刑部。
嗜好酒肉,却很少品出个所以然,入嘴皆是“爽快!”,每年中秋和大师兄一起回苇崖山,拉着一车酒罐,再到山里猎了几头猪。一边赏月一边和师父五师兄一起谈天论地。
楼敬少年的记忆中,明月高悬,月华金黄,万里无云,而他在卧榻上,看着四个大老爷们嘻嘻哈哈,苇崖山的梨花酒香赢溢,在楼敬的卧榻前闲逛,哪怕他强提精神,但也在安逸中沉沉睡去。
那月亮,和今晚的有些相似。
屈则申上下打量,突然大笑,一改方才的悄声:“好小子,气息又稳又沉,看来是功力大涨啊!去年回去没见你人,七弟说你闭关了,我还以为是要下山,紧张了;现在看来,你这闭关可是突飞猛进了。哈哈哈哈!”
笑声未落,隔壁破口大骂:“他娘的大半夜鬼叫什么!让不让人睡了!”
屈则申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伸手一指窗户,楼敬心领神会,拎起长杖翻身出窗,跃到房顶。抬头看见屈则申的酒壶挂在屋顶的锦旗上。
星光犹如一层轻柔的银纱,从遥远的苍穹落了下来,像一个轻功极好的女侠,笼在梦乡中的奋谷城——说是说梦乡,但似乎之后会有什么较大的节日;比如那个“渐金节”,奋谷城的一些角落略有烟火,城墙脚下的穗子湖算是一道去处,那里的竹林被灯笼从下方照亮,在夜风中摇曳着;两三条街道外的酒楼乐馆被灯笼映射得甚是明亮,夹杂着一两句酒话,大舌头到听都听不清楚。楼下还有冒着腾腾热气的小推车,一位老汉坐在推车后的石墩上,手里捧着一碗茶水,和一个中年男子低声聊天。那名男子楼敬是认识的,他是这家客栈的老板,两道八字须和额头下的一字眉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其实吧,去年就想找你喝酒了,可惜师父不肯,说什么都要让你下山才能喝。”屈则申从后面爬上来,拍拍楼敬的肩膀。上前撩下酒壶,“嘭”地撬开木塞子,他慢慢摇一摇,一股不知名的醇香被牵到楼敬鼻尖处,有种说不出来的酸甜味。
“我怎么闻着像陈三叔的红枣水啊?”陈三叔在苇崖山下的白芦村卖各种稀奇古怪的零嘴,红枣糖水也算是独一份。
“东洲木康城的归云酿,专门诓你们这些没喝过酒的,闻着像糖水,一口气七八瓶,后劲一上来可以把你摁在地上。来,试试。”屈则申露出坏笑,把酒壶递过来。
师父已过花甲,一直叨唠着楼敬不得沾酒,因为当时好奇偷偷嘬了一口直接发了五天高烧,差点把刚打通的经脉全部给烧回去了,幸亏楼敬学的是紫流林的蛊毒之术,烧了五天之后突然恢复。师父当天早上打开他的房门,见他活泼乱跳,惊讶得摔碎了手里那个前朝官窑烧的华德镇刘氏枫霞纹碗,为此师父鬓角多了数根白丝。
因此,楼敬对酒有些忌惮,可听说拒绝前辈的酒是一件相当不符礼节的事情,自己对酒又好奇得紧,实在忍不住,接了过来。他先战战兢兢地抿了一小口,发现味道不错,便一口闷完。
放下酒壶,才看见三师兄表情诡异,好似家传的宝贝掉进悬崖,苦不堪言,又忍俊不禁。
“三哥,这酒很贵?”他擦擦嘴,问道。
“算不上贵,只是买不着。”屈则申苦笑出来,道,“这是大师兄从木康城捎来的,我还没尝呢,本来想让你喝一口,剩下全给我的……”
楼敬一时不知如何安慰,憋出一句:“好像坏了,酸酸的。”
屈则申吧唧一下嘴,道:“这酒就得酸酸的,酸到盖过甜味才算是上品。”
“还有这说法?”
“没有,我瞎说的。”
二人相视一笑,坐到屋脊上。屈则申从腰间摸出一个包袱,可惜地说:“哎,可惜你睡得太早了,本来想带着酒和这玩意和你一块吃,吃完了你就睡个好觉,明天一同赴宴的。再有一会天就亮了,你喝了归云酿,明天醒不过来误了时辰可怎么办呐?”
“明天?明天怎么了吗?”楼敬盯着那包袱,直觉告诉他,是美食,而且是肉。
“明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啊!”屈则申一副很惊讶的样子,仿佛楼敬忘了什么理所应当的事情。
“什——什么大喜日子?”他一哆嗦,猛地想起那白鹿歌在傍晚好像也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视线赶紧跳到屈则申的脸上。
“你呀——”屈则申故意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一脸坏笑地拖长音,吊得楼敬喉结一动。
他摸了摸怀里的穗,有些忐忑:“我我我我我怎么——”
长音拖罢,屈则申哈哈一笑:“大家伙庆祝你出师啊,傻小子!”说着解开包袱,里面一层油纸裹出一个眼熟的形状。
“烤鸡!”楼敬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看着油渍斑斑的包装,想起自己晚饭还没吃,顿时对眼前被层层剥开的纸壳饥渴难忍。虽然已经凉掉了,诱人的肉味也消失了,但金黄色的外表依然带着从视觉到胃口的冲击力,撕开之后的雪白色在入口之后仍保持着欲罢还休的弹性,不断撩拨着舌尖和臼齿,在口中翩翩起舞,让楼敬欲仙欲死。
两人很快将蒲扇大小的烤鸡消灭殆尽,末了屈则申拿着酒壶倒出仅剩的一滴归云酿,意犹未尽。道:“怎么,来不来和我一起来刑部打坏人?哪里有事我们就往哪里跑,天南地北,还可以到处吃东西。”
楼敬不慌不忙地啃完最后一丝肉,问道:“干什么的?和捕快一样抓人吗?”
“我们抓坏人。”屈则申大声道,“下到响马海贼,上到贪官污吏,只要敢害黎民百姓,我们一个都不会放过,让他们牢底坐穿!”他勾着楼敬的肩膀,道,“咱们习武,可不就是为了铲奸除恶么?”
楼敬点点头,拇指在食指的侧面缓缓摩挲,他的视线在远远的山影游走,漫无目的。
他沉默片刻,第一次张口却没说出话,他又闭上了嘴,组织了一下语言,再度开口:“昨天我听个说书的讲眸水雷家被官府封了,他们也是祸害百姓、大奸大恶?”
“当然是啊。仗着行侠仗义的名义,私养军队”屈则申的神情没有一丝变化,像是在说什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向楼底下栏杆处一只橘色的猫吹了一声口哨,继续说,“文书上面把他们的军械库和一些与北国人往来贸易的事情都标注出来了,为此我上个月还去了一趟坦奴林,好家伙,整个地下陵墓全都是名匠锻造的神兵利器,每口棺木里边都有好几个法术卷轴,虽然不都是仙术,但那规模也忒吓人了。”
“雷家也算是大家,陵墓有些贵重品陪葬,不是寻常事情?”
“不不不。真要有贵重品,下葬第二个月就得让盗墓的给挖走;那群人没一点仁义道德,连尸骸都会被拣去做假舍利,哪能留给死人啊?”
楼敬笑了笑,答:“在理。”
他站了起来,手里拿着长杖,面无表情。视线还是随处游走,不知道自己应该专注哪里。
屈则申抬头看他,问:“六弟?”
楼敬换上一脸笑容:“漫漫长夜,百无聊赖,师兄何不与我切磋消遣?”
屈则申一愣,仰天大笑,活动了一下肩膀:“你小子是喝高了啊,也行,让师兄看看你闭关成果如何!”
楼敬回头看着屈则申,长杖甩到背后,身姿一伏,腾出一只手,竖起食指:“谁先跌出这个屋顶,明天的早餐就谁出钱。”
屈则申站起身,笑着挽起袖子:“韩春楼的早点可是出了名的贵,你身上带几个子啊?够我喝茶么?”
“下山之前师弟可给了我一捆银票,一顿早茶我还真不放眼里。”
“好哇,那我就要点最贵的了!”
话音刚落,二人身影便撞到一起。屈则申一脸狂气,楼敬笑容越来越浅。
月华如水,逐渐溶解深邃的夜色。东边的山顶被溶解成一片浅蓝,像极了劣质的蓝色布匹被水冲掉了颜色,露出滑稽的模样,在周围的衬托下显得粗糙。
在浅蓝托起朝阳之前,山林依然是一片寂静。人们都知道明天一定会来临,日子一定会过下去。
人们都知道,都清楚。
楼敬架住屈则申几招腿击,连连后退,最后一个后跃,踩在客栈前的木灯柱子上。
“你输了!哈哈哈。”屈则申双手叉腰,爽朗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