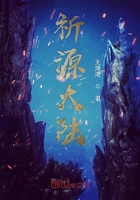第二天辰时二娘如常到承礼社训练,人人见了她神色好像与平日不同。她问了才知道四丫把她对阵安夫子的事传得人尽皆知。午饭后刘义也特意过来寻她,原来他也听人说了,就详细问了当时情况。
二娘听了扶额道:“义父,不是什么值得提的大事,不就是安夫子考我我答上来了而已。”
刘义看她不骄不躁,很是满意:“丫头,你之前说自己读过书,我也没在意,是我疏忽了。承礼社刚开办那时候也有让人识字学礼的目的,可惜后来的当家兼顾不到,才慢慢变成只教习舞乐。”
二娘第一次听刘义说起承礼社的事情,她很是感兴趣,便问道:“这识字和舞乐有关系吗?我还听说承礼社的第一任当家是个了不起的乐师?义父能给我讲讲吗?”
刘义沉思了一会,开口道:“其实很多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老当家原本在太常寺掌管礼乐,出宫后四处游历走到了咱们西河村,见此处民风淳朴又喜乐舞,便决定住了下来。我们整个汤阴一带祭祀曲乐都是他教习的,就连你昨日所观仲秋踏歌也是由他所编,这才让西河村在汤阴有一席之地。至于识字和乐舞有何关系,我只记得师父曾经说过,媚人之舞为下等,激人之舞为中等,自然之舞才是上等。可我师父也不明白自然之舞是何意,我活了这么多年也没明白,后来我遇到一贵人,他听了这话告诉我万事皆在书中。”
二娘很是新奇:“这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那踏歌为何舞?我昨日见了脑子里全是她,想得都无法入睡,这是媚人之舞嘛?”
刘义哈哈大笑:“我也不知,我觉得它可能是激人之舞吧,等你长大经历多了你就会慢慢明白了。”
二娘噘着嘴不满道:“您就知道拿等我长大之后的话敷衍我!”
刘义无奈:“不是敷衍你,舞乐对我而言更多是为了生计,我整日疲于奔命只为了大伙能多口饭吃,许多事情并不精通。我所生活和接触到的就仅限于此了,而念书像是人在平底处登山一般,可以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
二娘歪着头故意问道:“义父今日难道不是来听趣事嘛?”
刘义点了二娘的头,笑道:“现在才知道你原来也是个狭促鬼!”
刘义带着二娘来到二楼转角的一个上了锁的小屋子。二娘听过许多这个屋子的传闻,它常年上锁没人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东西。所以关于这个屋子的传闻有很多版本,四丫最相信这个屋子里关着一个疯女人,还说得绘声绘色跟亲眼见过一般,让二娘每次从这里走过都有些发怵。
一打开门二娘就闻到一股霉味,呛得她直咳嗽,二娘紧紧跟在刘义身后打量这间屋子。屋子陈旧古朴,阳光照进来满屋子尘埃在光晕中飞舞,中间摆着一把古琴,旁边两排是架子,架上叠着一摞摞的书卷。
二娘看了很是惊喜:“义父,原来我们这也有这么多书呢!”
刘义看到满屋子灰尘,有些懊恼道:“唉,这都是老当家留下的书,听说可宝贵着呢,当年我接手这里时一尘不染,这些年只顾着在外头,连师父临终让我好好保管它们都给忘了,弄得它如今变成这样子。”
二娘很有兴趣地翻看了一番,也觉得十分惋惜,这些书不止积灰还有虫蛀。她便自告奋勇:“义父,你没有时间就让我帮你打理这个书阁吧。”
刘义摸了摸胡子,故作深沉道:“这些书在我们手里只是一堆废纸,于你可是明灯,这里以后只许你单独进来,你可要好好保管它们。”
二娘兴奋道:“义父放心,这里以后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地方。我一定会把这里变成他原来最好的样子。”说完她就开始着手整理书籍,刘义见她沉浸其中,也不打扰她,就悄悄离开了。
二娘先是把架子旁书卷目录浏览了一遍,发现这里藏书所涉甚广,有经史类、礼乐类、地理游记、诗赋等等,她先是把它们整理分类,再分批拿到院子里晒,每天练完基本功就开始钻进书阁打理,整整半个月也不见人。
终于有天四丫才逮着她,急急问道:“二娘,你最近去哪里了,我们找你好几次都找不到,问大伯他也不回答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们可是好姐妹,你可不能只顾着自己一个人玩。”
二娘看着自己的伙伴满脸歉意,“最近从义父那里得了几卷书,我看入迷了每日都在书阁里念书呢,一时就忘了跟你们打招呼了。”
四丫不可置信道:“读书有那么有趣?我听别人说可没意思了,还能让你都忘记玩耍了,你没听过莫负少年时吗,现在真是玩耍的好时候!”
二娘挽着四丫胳膊憋笑道:“这道理你哪里听来的?书中有意思的东西多了去了,我最近看了些志怪故事,我是一时有些新鲜,就忘记时间了。那些故事你听都没听过,要不我下午说与你听?”
四丫一听还有故事听马上笑逐颜开,就提议今天在榕树下听故事。于是二娘就临时当起了说书先生给拾月她们讲起了搜神记。二娘讲起故事自然不如那些说书人,可细声细语得讲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一个故事说完她们还意犹未尽,催着二娘多读些书才能给她们讲故事。
从此二娘就过上了晨起练功,午后读书偶尔当回说书先生这种充实而快乐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