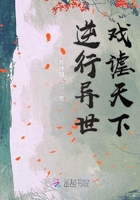一封白应昇亲笔的书信递到了长亘城的驿站,本来还要再辗转些时日的,可黄默丘偏偏在那儿瞧着了这封信。他这一回“偏偏”,换来了叶延一个怒目而视。
“这信上没有经手驿站的签章,是特别派送来的。”
“是的,黄掌管,我看得出来。”
“我惦记着这封信一定极为重要,所以带来给你。”
叶延毫不客气地讲道:“所以我才谢你。”
“哦,哦。”黄默丘笑笑,识相地走开。
无需拆开信,看这字迹便知道是谁写的了。信封上只有他两个字的名字,写得细长。
他在长亘这件事,会是谁说出去的?不会是黄默丘,他既然能递这个消息,白应昇也不会费这个周折,找专人送这么一封信,直接叫黄默丘转达就是了。
唉,把昀千那家伙给忘了。当日事情完了,他们分散时,昀千定是听见了他与马夫的对话。不过,昀千却不知道他身在玉楼。他不应该知道的。
回到屋内,拆了信,叶延更是什么话都说不出,只剩叹气。
开篇先是三个“速回!”,颇为慌乱。读到结尾,竟是白应昇要娶成茵姑娘,被族中长辈挟住了,两相对抗之下,白应昇希望叶延回去帮忙。信中甚至还拿叶延敕风首领的官职威胁,叫他收到信后不论人在哪里,立刻启程,回日曦城“援助”。
信上虽然如此写,实际上,叶延在白家人中完全说不上话。他能出的主意也不过是逃跑私奔那一些,对白应昇来说完全是废话。不过,白应昇都做了皇帝,要娶哪一个女子居然还闹得这样狼狈,等叶延回去了定然要笑话他一番。
叶延出玉楼去定马,这时已过申时,天已傍黑。良持用完了晚饭,伏在塌上睡着了。
可惜走了许多处租赁马匹的棚屋,叶延都没找到足够精神,能长夜奔袭的马匹。叶延不由得想起了在日曦城城郊马厩里看见的那匹不太顺从的马——那匹马比长亘这些精神百倍。他随之想起了白应旻——虽然这种联想有些奇怪,即使是这种情况,白应旻也定然能找到一匹好马。
叶延来到最后一家,仍是不满意。马匹不好不仅赶路耗时,如果半路马匹累倒了,那可是大麻烦。
“老板,往日里那些精神头儿足的马匹呢?”
“公子这是往哪儿走?”
“日曦城。我紧赶着走呢。”叶延笑道,“到晚了,饭碗不保。”
这老板是个头发稀少的矮胖男人,脸上带着长期酒醉的红色。听了叶延的话,他皱起眉头。
“公子,不是我这店骗人,实在是今天的好马都被借走了。说是朔仓部的一个将军,谁知道是个什么角色?简直是硬抢!抢到烨国地盘上了!”
“全城的好马都‘借’走了?你不是唬我吧?这一路上货摊子都摆的好好的,怎么可能有马队穿城而过?”
“不不不,他们没走。他们明日才走呢。”
“为何?”
那老板似乎就在等着叶延这句话,立刻凑上来,恨不得将自己知道的全显摆出去。他撇撇嘴,又换上一副傲慢的神情,说话时眼睛都发着光。
“朔仓人想在长亘停留一晚。你不知道为什么?”
叶延退后半步,与老板确认了眼神,立即掉头返回。
是玉楼。朔仓的将军留出这一晚来,是为了良持。
“哦,是说广让浮道吧?当初在我父亲手下,因为总爱逞威风、占便宜,可受了不少罪。就这还没改呢!”良持边打哈欠边说。叶延慌张地冲进来时,良持刚刚睡醒。在他语无伦次地讲了这许多之后,良持却似毫不在意。
“这么说,跟你还算有过节了?”
良持拉着叶延在几案旁坐下,仍是哈欠连天。她擦擦眼里挤出来的泪水,说道:“那算什么过节?他自己总管不住自己,只好叫别人替他管了。他那些丢脸事我可都记着呢。他若是敢来找我,我定要……”
“——你定要将从前那些事扔了,不要激怒他。”叶延抢过她的话。
良持不置可否。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圈,开口却是:“你刚才不是出去找马了吗?”
“你先答应我。”
“这样,你有要紧事,不要在这里耽搁,你去找黄默丘,让他帮你弄一匹好马。”
叶延偏着头,等着良持自己回到刚才的话题。
“你这表情是什么意思?不要这样看我。”
“你之前……”
“我可以,你不行。你这样我怪紧张的。”
叶延仍旧盯着她,直到她丧气地道出:“好吧,答应你。”
他刚踏出蝶屿阁,黄默丘身边的一个小厮便将他堵在门口。白应昇竟来信催他。信上又是一番气愤到无可奈何的抱怨。
“玉楼中可留有快马?”叶延问这送信小厮。
小厮一拱手道:“公子,黄掌管已经备下了。”
这黄默丘恐怕是受够了叶延的态度,干脆叫一小厮来做这些事了。
叶延随意问起这小厮的名字,他叫吉安。
日曦城皇宫紫微殿里,白应昇将下一步行动完全交付在了叶延身上。可是叶延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的确什么忙都帮不上。白应昇叫他回皇宫不是图他能有什么计策,不过是希望和族人起冲突时,能有一人站在自己这一边。
那帮老顽固说成茵出身低,那便给她姓吴,是烨国大姓。本来如此也就解决了,偏偏白章濂又有别话,竟说要替吴家女子出头,谈什么门第的纯粹!真要论纯粹,他也不想想自己名号为什么叫“惠”,还不是父亲要他平和冲淡,今天还在这儿装什么好人?
越想越气愤。
昀千呆立在门外,看着屋檐上的飞龙出了神。
“哎!昀大人!”边上一个侍从喊了几声,昀千没有反应。直到肩膀被人戳了,昀千才发觉到有人叫他。
“昀大人!陛下叫你呢。”
昀千用了几个来回才意识到原来“昀大人”是叫他。“昀”当然不是他的姓。这称呼只能叫他想起几个月前那个城门护卫“云大人”。
昀千进去的时候,眼瞧见皇帝已经全不似平时那样冷静了。地上砸了两套杯碟,上面盖着揉成一团的纸。昀千回忆着叶延那套平静的态度,努力把记忆中的全部线索复刻到自己身上。这事儿本来就该是叶延倒霉,怎么就叫他赶上了?叶延自己跑到长亘去了。等他回来,定要讹他一笔。
白应昇从一摞子拜贺新年的奏章中抬起头来,那神情把昀千吓得倒退了半步。
可是他躲不掉的。
白应昇向他招了招手,昀千只得走上前。这还不够,白应昇叫他把耳朵伸过来。
“把白章濂给我绑了。”白应昇的耳语好像蛇的嘶嘶吐信。
“陛下,这……不大好吧。现在绑走惠王,未免太明显了,谁人都猜得到是我们做的啊……”
“我就是要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决心如此,不容任何人置喙。”
昀千僵硬地后退一些,瞧见白应昇脸上的笑容。昀千苦着一张脸,犹豫地点了点头。
叶延,你最好马上回来。昀千在心里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