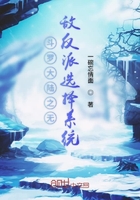田元照发现秘藏乐普不翼而飞,忧愤不已,疑心老和尚委派护卫随德,在宫廷冷眼观瞧久了,他不敢信任任何人。然而他深知绝不能叫修德察觉出来。老和尚深不可测,谁知晓是甚来头呢。夜间,修德护着他从宫中到府邸,走到内宅,小太监早掌起灯来,修德陪着走进去,到门口,修德冲照旧冲他一拱手:中使请,在下告退。田元照冲他修德一笑:今夜无事,你且来陪我吃几杯。修德道:主持不教饮酒。
田元照笑道:主持若问起,我自向他解释。修德不好推辞,只得跟他进去,转过屏风,堂中几案上摆着一架古琴,极未古朴,修德好奇,不免多看了几眼。
田元照冲他一笑:你亦通音律否。
修德把大脑袋摇了摇:未曾。
田元照:何不一试,别看它只有七弦,音不过宫、商、角、徵、羽,变化无穷。
修德走过去,迟疑着,右手伸出两个粗壮的手指笨拙拨弄了一下,发出沉闷之声。田元照便知他所言非虚,便伸出一手,略略拨弄了几下,琴声悠悠。修德张目道:好听好听!
田元照:众皆不知,咱净身入宫之前却是乐师,也曾地方闻名,因此颇通音律。我为你弹奏一曲如何。
修德连忙拱手:岂敢岂敢。
田元照指了指墙边一塌:你且坐听。修德依言坐了。田元照微闭双目,开始抚琴,琴声空灵,似从极远处飘来,修德不觉被其摄住,脸色渐舒缓,沉沉欲睡。田元照缓缓张开二目,望着他笑道:想你练武之人,必定辛苦,又被清规约束,如何得快活。日后我若得势,为你建一庙宇做主持和尚却好。
修德似睡非睡,摇头道:我在山寺孤苦,如何肯再回寺院,中使若提携,愿为官为将,财货美色受之不尽。
田元照不敢深问,便戛然而止。过了半晌,修德才恍然若醒,慌忙站起来:赎罪,却才听得心里畅快,不觉睡着。
田元照心里十分得意,当即吩咐奴仆摆酒。
次日,田元照来到宫中,皇帝跟几个小太监掷石子较远近。见他走来,连头也不抬。自选秀女之意教王策时驳回,杨炼怏怏不乐,喜怒不恒,常拿身边太监出气,虽田元照亦不免。
杨炼跟小太监比了一回,自觉无趣,一脚踢开小太监,打着哈欠,这才回身看着田元照:今日有何新戏。小太监爬起来,一溜烟跑开。
田元照看左右无人,便低声道:陛下不知,王中尉府中美妓如云。
杨炼笑道:他去势之人如何快活
田元照道:歌舞声乐方知美色之趣。
杨炼怒道:你故以此诱朕,却不能为朕分忧,实为可恨。
田元照道:奴才精音律,可于后宫调教宫女,为陛下助兴。
杨炼道:如何不早说。
田元照:陛下,奴才恐王中尉不允,故谨慎。
杨炼:朕自娱自乐,又不碍他事。
田元照:昔日太祖宫中有梨园弟子,皆精通歌舞。群臣莫不仰视。
杨炼道:如何她们何在?
田元照道:先帝继位,遣散至各地教坊司做司业去了。宫内亦有遗留之乐普,技法多半失传,奴才精研之,必能复其风流。王中尉甚好音律,若成,必允陛下选美女进宫。
杨炼大喜:你去办吧,勿使朕失望。
田元照心里暗喜,自觉处心积虑之设计略有所成,便于宫中暗先宫女。
这日修德护着他来到东市乐器行。一溜商铺皆是各色乐器。中正一家三间门脸,甚为宏阔,门上一匾额,上书:四维琴行。显目出摆放着四样乐器:琴、琵琶、笛、萧。写着一行字。萧将军临刑所奏乐器。墙上挂满各色弹奏乐器,两个掌柜在此静静地守候。田元照进来扫了一眼,并无出色乐器。传身欲出,一书生从院内匆忙出来,差一点将他撞上,修德略一推,推出几步之外,抬起头来,却是张景略。田元照未免狐疑:看着他问,你不伺候钧王,来此作甚。
张景略慌忙冲他拱手:田中使容禀,钧王欲得食肉,府内又无余钱,小人舅舅在此管账目,因此来打秋风,被他一顿嘲讽,气煞人也
田元照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一锭银来,丢给他道:难得你一片赤诚,伺候人主当如是。他这话是说与修德听得。
张景略回到钧王府,太监们照例凑在一起喝酒闲扯,见他来头也不抬。他微微一笑:好香的酒肉。无人吱声。他亦不觉尴尬,径自往里去,花园内有个小池塘,养着十几尾金鱼,钧王正背手观鱼。听见张景略的脚步,转过身来。
钧王:洗澡果然全身清爽。
张景略:难为殿下这几年,假痴不癫
钧王:我无害于人,能不免乎?
张景略:殿下既为皇子,焉能脱身事外,其势不得不为者。
钧王指了指金鱼:我不如池中鱼也。
张景略:天寒,若无人照料,池鱼将死。
钧王:你主欲何为。
张景略:殿下,天下名器,若鲁王意外,则太监必拥殿下。
钧王:杨炼一番害我不成,定有其二其三。我恐难逃毒手。
张景略:殿下安心,以臣之见鲁王不过心血来潮,非筹划已久,过后必忘。
钧王:我孤苦一人,任你等摆布。
张景略:臣岂敢,臣与殿下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钧王:你入府便知我做戏否
张景略点头:王妃不受宠,殿下门庭冷落,无人瞩目,先帝沉湎丹药,太子与唐王暗斗,诸太监及群臣亦察鲁王及殿下。
钧王:我若不做戏,只怕早被人害。我夜来不敢灭灯,亦不敢见生人,虽为王子,不若商贾之子。
张景略:殿下且忍耐,潜龙勿用。
钧王叹息道:纵做了鲁王又如何,不过教中尉玩弄鼓掌之中。往日李光庭在日,或能与之争衡。如今朝中文武皆仰其颜色,还有何望?
张景略:老太监必内斗,正可隔岸观火。
钧王走到凉亭中坐下,树叶落于水面,便道:人生若一叶飘零...
张景略:世事难料...不如饮酒...
杨府密室,灯烛莹煌,一个须发皆白老者坐在一个绣墩上,诚惶诚恐地望着一张旧药方,仔仔细细看了几篇,将药房小心翼翼呈送给坐于塌上杨玄机。
杨玄机脸色有些憔悴,显然睡眠不佳。
杨玄机:孔御医,你在前朝便入宫为医官,见识广博,可曾见闻此方。
孔御医拱手道:中尉赎罪,学生才疏学浅未曾听闻。学生观中尉面相气血两虚,恐夜来睡眠不足,饮食不调。此方多生发之物,服之则甚是凶险。
杨玄机笑道:如此,烦劳你下去开一方。站在一侧心腹太监马庆早上来,杨保走后,他便贴身当差,他朝孔御医道:孔先生,请。
孔御医慌忙站起来向杨玄机拱手:中尉保重,学生告退。跟着马进出去。杨玄机抓起几案上的茶杯摔得粉碎。
不多时,马进又回
杨玄机吩咐道:遣人暗中监视孔御医,若胡乱议论,即将其刺杀。
马进领命而去,杨玄机渐平复下来,站起来观看贴在中堂巨大山河图。
杨玄机看罢多时,转过身来,马进早在一旁伺。杨玄机淡淡道:此画乃京城名手所作,当日太祖赐予萧候,魏、赵二国柱伏诛,萧候诚惶诚恐,深恐被族,得画日便请辞大将军及一切职务,闲废在家,不交宾客。你看这千里江山何等壮阔,不用多久只怕要残破不堪了,天下纷纭,英雄四起,谁能收拾这旧山河呢。
马进知道是主人的牢骚之言,在一边静听。
杨玄机叹了口气:自古无去势之英雄。
马进道:以主公之能,足凌驾朝中文武。
杨玄机不由地摸了摸颌下:你不知也。
马进:王中尉犹能令文武畏惧,何况主公。
杨玄机摇摇头:迫于势尔,非真心敬服。走吧。
两个来到膳房,七八个庖厨正在忙碌,几案上摆好了数十道菜肴,杨玄机扫了一眼,皱皱眉:过于荤腥,都赏给护卫吧。
马进笑道:主公所食过于清淡,进府内医官皆教调补。指了指正在煨着的一罐汤,此南召进宫之柴鸡,加以高丽进贡之野参,慢火炖煮一日一夜。正是时候。见杨玄机并不说话。便过去打开盖,用汤勺舀出一点到一个银碗,一口喝了。等了片刻。换了一个汤勺,另一个银碗盛满了送到杨玄机跟前。
杨玄机看了一回,一勺一勺慢慢喝了,脸上冒了层细汗。喝完冲马进道:去花萼楼。马进明白要装扮。出了膳房,来到书房,临窗一梳妆台,杨玄机在台前坐下,对着铜镜端详自己,马进从梳妆盒中拿出几道浓黑的假须,十分熟练把一队八字须贴到他上唇,下颌贴一道浓黑的髭须。瞬时镜中人气度俨然,颇有王者之气。
杨玄机双目熠熠生辉,站起来来回踱步,望着马进道:如何。
马进笑道:主公龙行虎步,王霸气概。
杨玄机:昔日太祖晚年,张承恩和我几个在跟前伺候,每日清晨起来必掉打把须发,竟至于秃,因此常迁怒身边人,动辄处死,我跟承恩出主意,找了毛发秀丽的宫女头发剪下,做成假发假须给太祖戴上,太祖大悦。自此对我格外垂恩。
马进笑道:敢情皇帝也怕无须发。
杨玄机:皇帝所惧怕的比咱更多,你亦戴上吧
这是个巨大赏赐,,马进赶紧给自己粘上。看去果然像一个富人的管家。主仆两个皆笑。
花萼楼并不在府内,在离此不远的请愿庆历坊。往常皆是杨保跟随,主仆两个由八个护卫护着出府走在大街上。四处寂静如死,杨玄机抬头往外两侧黑魆魆屋顶,道:复仁掌管京城,夜间刺客不敢轻动了。
马进道:奴才听闻王中尉每夜数易其屋。
杨玄机:田元照近来做何时
马进:在宫内做梨园,教授宫女音律。
杨玄机颇为诧异:当详留意。
马进:闻听王建功率禁军出征之日,王中尉率左军主将送行,教诸将据牢津要之地。近来王中尉将心腹皆安插在各处膏腴之地。未把主公及右军放在眼里。
杨玄机淡淡道:贪多无益。说着便来到一处府邸,府门并不起眼,两扇窄窄木门,护卫啪啪叩打门环,门吱呀一声打开,里面小太监探出头来,看了杨玄机慌乱开门:温爷您来了。
杨玄机点头,迈步往里去。小太监一面往里引,一面朝里面喊道:温爷来了。
转过照璧,庭院深深,廊下摆放着兰竹盆景。院内宫灯照亮,院落屋舍清雅,两个婢女早迎出来,插烛似的拜下去:恭迎温爷。
杨玄机摆摆手,起来吧,吩咐护卫:你等在此等候。护卫便在外面戒备。他与马进两个跟着两个婢女往里去。
杨玄机:二位小姐在做什么?
婢女掩口而笑:闻听恩公来:匆忙打扮呢。
杨玄机不觉露出笑容:一向倥偬,久未进京。
婢女道:两位小姐日夜思念恩主,恨不能伺候左右。
杨玄机点点头。不觉便到了内庭。两位丽人风摆荷叶般迎出来,笑魇如花,大者不过二十,小者不过二八,盈盈便拜:玉清、玉洁恭迎恩主。
杨玄机双目闪光,急走几步便将她们一一搀扶起来,两女便一左一右将杨玄机往里面搀。马进识趣。便在门口伺候。
玉清嗔道:如何许久才来,定是将我两个遗忘。
玉洁笑道:我跟姐姐说,恩主不日将至。姐姐还不信。
杨玄机笑道:偏你能掐会算。
玉洁道:十年间恩主或一月一至,或两月一至,掐指一算便知。
杨玄机也笑:想我将你两个从教坊司赎出时,不过总角,今婷婷玉立,我亦老矣,星星白发,现于鬓垂。
玉清笑道:如今我两个都长大成人,正可报答恩主。
当下来到内堂,两女扶杨玄机坐下,婢女摆上酒食。
两女为其把盏,嘤嘤软语,杨玄机不觉端起酒来。
玉清:恩主,我两个不计名分,便是外宅亦可,以报救养之恩。
杨玄机道:我救养你两个非为此也,只因你祖父魏候与我有旧,故冒险将你两个重金赎出。想你两个亦是公侯子孙,岂能受此委屈。
玉洁道:妾身闻听萧候亦被族灭,谁人可保,若无恩主,只怕我与姐姐活不到今日。
杨玄机:日后旦有老夫在,你两个定然无忧。
玉清便冲玉洁道:妹妹,我两个来敬恩主一盏。
两个端起酒杯俩,玉清道:愿恩主万岁。杨玄机大喜,连忙一饮而尽。
玉清道:恩主,我两个身子皆洁净如玉,今夜便伺候恩主,教知我们心意。说罢她便宽衣,雪肤花貌,她扶了玄机的手摸上去,温润如玉。玉洁亦宽衣。玉体冰肌。杨玄机颇为惶惑,玉清上来便要替他宽衣,酒顿化作冷汗醒了,慌乱站起来:今日不行矣,我当戒斋。
二女一愣,玉清破觉委屈:恩主嫌弃我两个。
杨玄机慌忙摆手道:非也非也,只是明日要进报国寺上香。我过几日再来吧,逃也似的往外便走。
儿女穿衣不及,在后怅然喊道:恩主
杨玄机回府之后,在卧房徘徊久之。
战龙在野
山野萧瑟,黄叶堆积,山间小径上,吴南柯拉着阿呆踟蹰而行,夜幕垂下。吴南柯停下来,扶着膝盖道:走了许多道路,不见人烟。天色将黑,若在山里过夜,野狗出没,如何熬得过去。
阿呆呆呆望着前方山峦:阿霁....阿霁..
吴南柯笑道:老妖婆必受重伤,且凶暴,你何必念之。倒是姓雷的汉子,甚是和善,我两个随他一路也未阻拦,教老太监不敢紧随。我意径随他去,谁知你执意这条岔路走。若老太监追来,看你如何抵挡?
阿呆双目一闪:雷家,雷家,须避之为上
吴南柯:雷焕倒是痴汉,黄老汉害了他家,他倒去送其尸首。说着,从锦囊中掏出一粒黑色的药丸来把玩着,连我精心炼制勇士丹瞧也不瞧
阿呆伸手便来夺。吴南柯赶忙藏起来:此药不给你吃。乃是我在杨太监府内偷偷炼制。名曰:勇士丸。怯弱之人服下勇气自溢,即刻刚强。两军临阵,若教士卒吃下,勇不可当,不避刀剑。诸镇将帅若知,必千金求购。说罢摇头笑了笑,自言自语道:谋富家翁甚易。非我所欲,自年少窥我三叔药书便迷恋药术,百计实验以观其效,所以冒死入宫,因可广搜天下药材,亦不用蓄养药奴,遭人告发,为官吏敲剥。
说罢他哈哈大笑:谁人能料你不觉做了我之药奴。遍尝天下剧毒,已百毒不侵。昔日我叔父炼药不能成,诸多不便,今我无此烦恼。
说毕,将勇士丸随身藏好。又掏出一个锦囊,拿出一味指头大小红丸递给阿呆:吃吧。阿呆接了一口吞下。目光渐渐沉滞。
吴南柯笑道:老妖婆以为音律将你唤醒,却不知你两日未曾服药,若不能及时到岭南加制,药尽,途中你醒转,如何肯随我摆布。说着将锦囊藏好,拉起阿呆便走。
沿着山路又走了几里,夜幕垂下,下起蒙蒙细雨,路侧草木丛中,七八只野狗正在啃食什么,为抢食相互咆哮撕咬。两人靠近,野狗都停下来,目光眈眈地盯着他们。吴南柯看去,地上片片衣襟,中间一带血迹、一架森森白骨,不免惊骇,拉了阿呆便跑。野狗见人胆怯,便追上来。吴南柯地上捡起一根树胡乱挥舞。野狗群捻指间将他们围住,呲牙咆哮。阿呆颇为惧怕,径往吴南柯怀里躲闪。吴南柯灵机一动,怀中掏出锦囊,取出一粒勇士丸塞到阿呆嘴里,骨碌吞下,顷刻,见他须发皆张,额头青筋毕露,目光凶狠,跳上前一脚将一只野狗踢飞,复一拳打在另一只野狗的脑袋上,教它回嘴一口咬住,便往嘴里吸血。阿呆吃痛,另一手猛击野狗脑袋,没两下,这只野狗呜呜两声,松口跌落在地上,气绝身亡。阿呆愤怒,一脚将其踢飞。其它野狗见了,一哄而散,跑进草木丛中,眨眼不见。阿呆伤口咕咕流血,吴南柯随身带着刀创药,倒出来敷在阿呆伤后处。
吴南柯指了指草丛里的野狗尸体,笑道:它万想不到吸了你的血却被毒死。你如今亦是一大毒物也。雨已将两个打湿,冷风又起,吴南柯顿觉寒冷刺耳。而阿呆浑然不觉,犹自对着野狗去的方向发狠。吴南柯拉了他一把:走吧,若前方再无人家,夜间你熬得过,我如何熬得过?四面皆黑魆魆一片,两个高一脚浅一脚又走了一阵,翻过一岗,见前方隐隐射出亮光来。吴南柯大喜:天无绝人之路。摸着草木走去,听见有水流之声。借着微光,一片波光。灯光却是从一只渔船透出来的
吴南柯高声喊道:船家,船家,救我两个。连叫数声。船舱里钻出一老渔夫,提着灯笼朝他们影了影。见两个穿着不俗,问道:你两个是何人,如何走到荒山去了,往日这一带也有百十户人家,孙秀作乱,朝廷兵马路过,鸡犬不留。
吴南柯道:我两进山游玩,迷失道路,见有灯火,故来求救。
老渔夫:也罢,你两个且来避避雨吧。当即让两个上了船,进了舱。船上只有老汉一个。吴南柯已冻得瑟瑟发抖,问老汉:我两个一日不得食,还请老丈赏口吃的。
老渔夫叹道:船上已无米粮,我每日来此河捕食,摇橹半日到扬州城外去换几个钱买米度日,因怕被税吏发现,夜间常在荒野过夜。吴南柯将外衣脱下来,又道:有火将身体烤烤亦好。
老渔夫看是寂寞已久,见人甚喜:舱内自有炉子可生火。当即生起火来。吴南柯、阿呆两个火边做了烤着衣服手脚。
吴南柯:老丈,明日你将我两送到扬州城外,自有报答。
老渔夫点头,踌躇半晌,又道:此河鱼甚多,不难捕获。近处百姓皆虽饥不食。
吴南柯:何故如此
老渔夫道:昔日官军杀人皆弃于此河,鱼鳖皆食死尸,往年杀鱼肚内往往有人指甲。我只捕小鱼,不捕大鱼也。你两个若饥,舱内尚有一鱼,肥大。
吴南柯舔了舔嘴唇,摇摇头。
阿呆似乎药效已过,扑通到下鼾声如雷。次日微明,雨停风止,天空阴沉。
吴南柯看时,几丈宽的河面,水甚浑浊,不知深浅如何,两岸草木蓁蓁,出仓看时,可见游鱼黑魆魆的脊背。渔夫将船摇离岸边,到水中之时,岸边有人尖声喝道:渔夫停船,速速回岸。吴南柯看时,却是杨保,浑身湿漉漉,手中提着宝剑,脸带愤怒。他从霁月精舍出来,一路尾随两个,知道雷焕厉害,不敢紧随。不想两个中途换道,他一直跟到黄云谷,不见踪影,又不敢去问雷焕,踅回又寻,一路追踪到此。心头怒火早按捺不住,恨不得抓住吴南柯一拳打死。
吴南柯冲他挥挥手:你不用追了,回去告诉杨中尉,待我炼得好药,自去寻他。
杨保道:一路艰难,你两个又无盘缠,万一有闪失我吃罪不起,你且教船家停下,我护送你前往。
吴南柯笑道:我不惯受人管束。不欲你同往。
杨保大怒,用剑指着老渔夫道:船家,速回,不然一剑杀了你。
老渔夫见了恐慌,望着吴南柯。
吴南柯催促道:快摇快摇
杨保焦躁,奋力跃入水中,朝渔船游来,眼见便追上。
吴南柯怀中掏出勇士丸,取出一粒碾碎了洒向杨保方向,鱼群争食,亢奋,跳跃不止,见一大物游至,便群起攻之,一时将杨保围住乱撞。杨保大惊,往岸边便逃。
两个搭老渔夫的渔船至扬州城郊,时值中午,两个饥肠号腹,但见百姓亦多菜色。吴南柯便拉着阿呆进了城,逢人便打听最大的当铺,到了便将阿呆随身玉佩摘了拍在柜台上:掌柜,当钱。
掌柜见了两个衣着华丽,神情狼狈,心里狐疑,拿起玉佩托在手上观看,隐隐可见一条飞龙,暗暗吃惊。便问:当多少。
吴南柯嘿嘿冷笑:价值连城,若不是急用钱,谁肯拿出来,也罢,先拿五百两银子来用。
掌柜也不压价,开了当票,兑付银两交与吴南柯。他把钱包往手里一托,问掌柜:此地最好的酒楼在何处。
掌柜:不远,出门往南穿过两条街,便可见庆云楼的幌子,扬州城最为有名。
吴南柯笑道:我两个且先去饱食一顿,再做计较。扯着阿呆便往外走,阿呆沉滞的脸上也泛出亮光来。
掌柜冲门口的一个伙计一努嘴,伙计便悄悄跟了上去。掌柜仔细将玉佩揣在怀里,匆匆出门,专捡偏僻的胡同走,七拐八拐,来到一处僻静街巷,沿着着院墙走到两扇窄窄木门前,左右望望并无一人,便拍拍一扣门,门吱呀一声露出一条缝隙,里面看是熟人将门打开,等掌柜闪身进去,复关上门。
掌柜道:我有急事见主公。速领我去。
里面人便带他穿过花园,来到一处院落,一扣门,吴瀚章出来了,冲掌柜一招手,随我来。掌柜便跟他进去。吴瀚章重新将门关上,带着他走到内堂。
周行密坐在塌上,望着掌柜道:何事急着见我
掌柜将玉佩掏出来,呈上去:主公,方才两个客人急当此物,我见来路尴尬,不敢耽误,即刻报与主公知道。
周行密接过来在手上端详,面色渐凝重:此物非同小可。抬头看着掌柜:他们是何模样,如何装扮
掌柜回禀:衣着华贵,然颇为狼狈,须发皆蓬乱,料年纪颇不小。当得钱便往往庆云楼去了,似是饿急,我已遣人跟踪。
周行密抬头看着吴瀚章:苏竞开、徐璐密遣人到各处搜寻两人,莫非...
吴瀚章:苏候在京虽失势,耳目毕竟灵便...此两个来历定非等闲。
周行密将玉佩仔细揣在怀里:且看看去。
三人当即从后门出来,周行密打发掌柜先去。不一时,周、吴两个来到庆云楼门口,掌柜早安排妥当,引着他们到二楼的一间雅座。因不是吃喝时间,店内客人并不多。两个上楼时,见一楼大堂正中一副座头摆满酒食,两人相对而坐。大快朵颐。一人面向楼梯这边,周行密一眼看去,觉得有几分眼熟,一时又想不起谁来。
到雅间坐下,将帘子掀开,居高临下正好看着两个。见另一人侧脸,面相威严。
周行密往吴南柯脸上仔细端详,目光一闪,轻声道:是他
吴瀚章:主公相识
周行密:此岭南神医之子。先父在时,府内老少有病疾,皆遣人去请神医。甚信任之。神医被诬下狱时,先父多方营救不得。此人逃至扬州,先父将其藏匿在府内,我常陪伴,癫狂不拘,不耐约束,一月余,夜半越墙走,自此渺无音信。
吴瀚章指了指阿呆道:此人又是谁?谣言李代桃僵,莫非...?
周行密沉吟道:太过离奇..
吴瀚章:莫若迎入府中细细讯问
周行密摇摇头:不妥,苏竞开耳目众多,岂能瞒过。此两人如此奇异,料他们必得消息。不久自至。
吴瀚章:如传言非虚,对我有利有害?
周行密:尚不知晓,只得静观其变。
吴瀚章:自杨复恭山南督军以来,荆襄战船常至下游,淮南震怖,唐王麾下诸将不知所为。传言唐王常欲泛海而走。若严冬水面结冰,杨复恭严督诸道并进,挥军马便渡江,扬州如何防御。
周行密摇摇头:老太监不知兵机,未敢如此。李仙芝、黄棠乱未平,料不至兵进扬州,不过欲威吓唐王,令其不敢轻动,不使得漕运有失。若李、黄乱平,则必致力扬州。
吴瀚章:李、黄已横扫沂州,兵锋已至青州,宋威只按兵不动,料想非朝昔可扑灭。
周行密:宋威老奸巨猾,必玩寇自重,驱之他道,趁势扩张。若教他将乱贼赶至扬州..生灵涂炭。
吴瀚章:主公不得兵柄...
周行密摆了摆手,示意不要说话,但听得楼下一阵喧哗。苏竞开由丁兵簇拥者走进来。掌柜和伙计惶惶不安,跑到跟前伺候:苏爷,不知您大驾光临...
苏竞开一摆手,随从大喝一声:闪开。皆慌忙避让。
周行密拉着帘子,两个不说话,听着外面动静。
苏竞开走到吴南柯、阿呆跟前,仔细打量一番。吴南柯已经吃饱,正拿着牙杖剔牙,阿呆吃得颇为精细,用箸在十几个盘碟里拨弄来拨弄去,似乎无甚可吃。对苏竞开等众不置一顾。
苏竞开盯着吴南柯道:你两个是从京城来的。
吴南柯翻眼皮上下看着他们:你又是何人,敢对我如此无礼。
苏竞开见他如此气势,随即笑道:并无恶意,只是想请二位移步敝宅一叙
吴南柯把牙杖一丢:我不得闲,不去不去
苏竞开看着阿呆,见他并无反应,扭头又看着吴南柯:他是何人,我主人欲见一见。
吴南柯嘿嘿一笑:此我之奴,千金不卖,休要相缠,我与此间刺史有旧。
苏竞开:何人?
吴南柯:周厚安也。
周厚安便是周行密之父。
苏竞开大笑:周厚安久居地下,你稍后可见之。冲左右喝道:拿下。
丁兵一拥而上,将二人拿住,往外便推。
苏府,苏竞开和徐璐两个引着唐王来到后花园,院墙边一溜低矮屋舍。苏竞开走到当中一间,门上着锁,一推露出一条缝来,屋里不大,空无一物。吴南柯和阿呆靠墙坐着,听见动静,吴南柯站起来,抢到门口:奸贼,速将我药丸还来。
苏竞开不理他,将唐王引到门口:大王,你且看一看竟是不是‘那人’。
唐王凑近看了一眼,脸色大变,慌忙闪到一边。苏、许两个赶忙凑过去。
唐王看着苏竞开:讯问他们不曾
苏竞开道:入府便搜他们之身,除了几代药丸并无它物。讯问时,唯有门边人作答,皆狂乱语,墙边人面目呆滞,若木偶。
唐王沉吟良久:正是‘那人’,料想服用丹药损伤头脑。门边人应是巫医。突然厉声道:你两个若泄露半个字,杀无赦。
两个慌忙点头
徐璐道:大王,如今何以处之
苏竞开:既于事无补,不如纵之
唐王:落到他人手里,竟来挟持孤,孤将如何?荆襄水兵常逼,孤若不上表,此冬难过。
苏竞开突然想到一事:巫医言其与周厚安有旧,周行密应知此人,可唤来讯问之。
唐王摆手:此事机密,若传扬出去,谣言四起,于孤不利。孤熟思之。说着,不顾而去。
吴南柯见外面人又里去,任他如何喊叫也无人答应,只得靠墙挨着阿呆坐了。夜色渐浓,寒风从门缝往里灌入,冷如冰窖。吴南柯冲门外喊了多时,嗓子喊哑,无人答应。阿呆也冻得在屋内乱转。倦意袭来,两个靠着打了个盹。长夜难熬,好不容易到天明,外面又下起雨来,晓风嗖嗖,饥寒煎迫,两个浑身颤抖,吴南柯看着阿呆道:我两个竟要死于此地,早知今日,何不教老太监一路保护。
阿呆忽然盯着吴南柯,目光闪烁,又看了看四周,站起来似在思想什么。
吴南柯暗道不好,朝阿呆道:你休要到门口去,外面有人暗算。
阿呆目光凌厉地盯着吴南柯:吴太医,此是何地。何人大胆竟然将朕锁困。莫非王策时、杨玄机两个奴才兵变不成。
吴南柯不觉跪下叩头道:陛下容禀,正是左右中尉两个带禁军入宫,陛下服用丹药昏厥,太监便扶鲁王登基了。奴才趁乱带着陛下逃出禁宫,一路逃到扬州,却叫唐王派人拿住,锁将起来。
杨睢大怒:大胆奴才,竟敢欺朕,宫城防守严密,你一人如何带朕逃出;况两奴既已作乱,如何能容你走脱?
吴南柯笑道:陛下息怒,此乃李代桃僵之计也。杨玄机欲臣为其炼生根之药,臣将计就计,言非陛下试药不能成,杨玄机便杀太监扮作官家,将我与官家藏身他府,我乘间带陛下逃脱。
杨睢阴森森道:你给朕服用何药令朕头脑昏沉,令朕做药奴,最为可恨。
吴南柯:非如此,焉能令陛下脱逃。
杨睢转身望着门外不说话。
吴南柯道:陛下爱子欲饿杀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