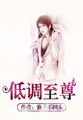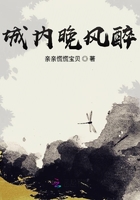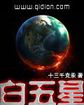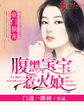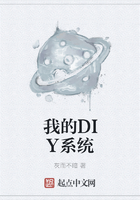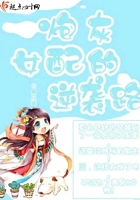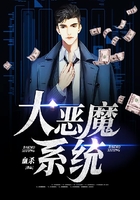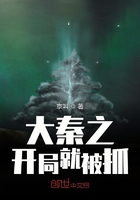4月24日晚上,贾植芳先生走完了他九十二岁的人生旅程,离我们而去。
复旦校园的林荫道上悬挂起千纸鹤。半个多世纪前,贾先生曾在这里被屈辱地带走,以后又在这里被屈辱地管制劳动。今天,当他以一个中文系退休教师的身份,一个清贫的无权无势的老知识分子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给予他的,是最真挚的敬仰和怀念。
和贾先生相识30年,许多往事好像发生在昨天。20年前我申报评“副编审”职称,是贾先生为我写的推荐材料。18年前,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的时候,贾先生为我作序,先生在序里说,我在“主持《现代家庭》、《为了孩子》这两个社会性杂志的编务”。贾先生一直把总编辑的工作称为“编务”,突出了具体和服务的感觉,对我是有鞭策的。
贾先生家里,进门那个房间布置成了灵堂,花圈簇拥着贾先生的遗像,花白的头发,抿着嘴,手指上夹着烟卷,想着什么的样子,好像还坐在书房。师母病重瘫痪的最后几年就睡在这里,那时床边上堆着很多厚垫子和布,侄女桂芙总在整理。
记得贾师母去世不久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办公室忙,门卫跟我说,有一个老头被人扶着来找我,是外地的。我跑出去一看,是佩带着黑纱的贾先生和桂芙!从复旦到南京西路有不近的路,桂芙说贾先生想出来散心。那天我们一起吃饭,还照了相,席间,贾先生谈笑如常。告别时,贾先生以他惯常的幽默说,谢谢你赏饭给我。
当时,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书房里,满屋的书,书桌上的稿纸,还是原样。氧气瓶拿走了,藤椅上的圆垫蒙着很干净的毛巾,在它上面坐了几十年的主人也走了。我在空空的藤椅上坐下,抬头看到墙上一幅笔力遒劲的书法——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三朝逆子 四度牢狱 半百出笼 花甲解放 七十带徒 八旬著书 九经考验 十分可敬。
我将永不能再听到贾先生那浓浓的山西口音:小琪,你来了。
29日下午,贾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宝兴路殡仪馆五楼的玉兰厅举行,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先生送行的人挤满了大厅。为贾先生印制的一页是先生的简历和主要著译目录,背面是贾先生晚年的语录:“不用说来世的事,就是今生今世,我也没有做过当官和发财的梦想。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吊唁厅里最醒目的,是贾先生胞兄贾芝的用999朵白玫瑰做成的大花圈,如一个巨大的洁白的圆。挽联上写着:堂堂正正的来,清清白白的走。
我站在靠近灵床的近处。一年前我们还能饶有兴味地交谈,如今已是永诀!贾先生的品格和人生态度,留给我们太多太多。
25年前,当上海市妇联执意要调我去任职的时候,因为留恋校园,留恋学问,我很犹豫,甚至觉得痛苦。我曾就这件事征求过几位师长的意见。
一位研究鲁迅的老师以他惯常的风格揶揄说:“学问?什么叫学问?我们国家的事啊,水涨船高,你有多高的位置,就有多高的学问,水平是跟着位子来的。你要能一级一级爬上去,有了权,水平不是问题,学问更不在话下。”那个年代,这样的话还是很让人骇异的。
而贾先生给我的忠告只是:不要忘了写作。之前,先生曾说过,在大学里向来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教书者不应多写,会把精力心思分散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搞文科的应该坚持动笔,一来多了解写作者的甘苦,免得眼高手低,二来能落到纸上的,往往已经过思考和提炼,本身是一种学习和提高,写作是一种劳动。而他是非常赞同后者的。
25年过去了。25年来,我从没有在“水涨船高”的路上追逐,也没有忘了写作。只是因为杂务太多,我的写作常常零碎短小,怕耽误先生的时间精力,自那本散文集出版后,我没有把以后写的那些文章给先生看过。一直想等有空了,把那些文字整理成书,再向先生报告,他一定会高兴的。现在,面对先生的遗像,我后悔没有及时去做该做的事。贾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与文字相伴,想象着先生摘了眼镜或是拿着放大镜阅读的样子,我伤感,那一幕永不会再现。
贾先生去了。那样挚着的教诲,今后还会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