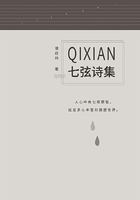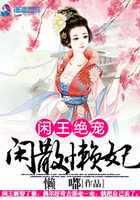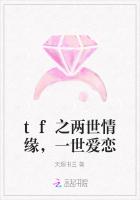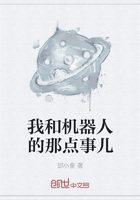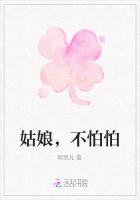清明,踏着浓浓的春色,大家都张罗着给另一个世界的亲人祭扫、上供。城里的糕点铺里,正适时地供应着青团,吃着这甜甜的、美味的食物,似乎也有了清明节的某种纪念意义。
其实,死去的人早已灰飞烟灭,稍有点唯物主义精神的人都会知道,他们是早已什么也不知道的了。活着的人忙乎的种种,其实都是为了自己,为了那种或痛楚、或歉疚、或悔恨、或疑惑、或哀伤的心境,做点什么,自己便能有几分解脱。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圣人百姓概难免俗,清明节便总是兴旺。
我从未能超乎其外。
每到梧桐飞花、春意弥漫的时候,我的心会沉浸在那样一种深深的、温暖的忧伤中。那逝去的,永不再生的人们,一个个那样生动,那样真切地走近来,对我说、对我笑,对我展示他们默默凝神的侧影。回忆便因永不能复活的他们而变得分外亲切、分外珍贵。
唯有你是例外,秋华。你的逝去本身便是例外。倘你也为那不可抗拒的生老病死,也为那莫测的车祸之类而去,你远去的孤魂不会也这样久久地缠绕着我。无论是我还是别的曾经与你同行的人们,都无法超然地、淡然地面对你的姓名、你的命运。
我无法释然。秋华,你的故事似乎已遥远得让今天的人们困惑不解,而无法被理解的牺牲,又是牺牲者何等刻骨的大恸!
只是,清明的祭奠总有一份是为你的,秋华,这能使你感到宽慰吗?
如果不是那惊世骇俗的结局,关于她,我能记住的只是几个片段。
二十年前,那列率先载着知青们驶离上海的火车靠站了。正下着大雪,浩浩荡荡的队伍把道上的积雪踩结实了,滑得像涂上了油。我们小心翼翼地走。
只听一个女孩子尖尖的嗓门:“哎呀,真好玩,溜冰场一样。”接着,咕咚一下,大概是跌倒了,一阵嘻嘻哈哈的大笑。稍停,又是咕咚一下,乱作一团了。
不远处,那个穿得棉花包似的女同学坐在地上,正脱鞋,两根短辫直楞楞地支在脑后。
“我就不信,就我会摔跤?”
她吃吃笑着站起来,穿着鲜红的绒线袜站在雪地上,脱下来的那双鞋,被她一抬手撩远了。有人制止她,小姑娘傲气地说:“那有啥,一双破球鞋,不值一毛钱。”她站起来,从挎包里掏出两个熟鸡蛋,自己吃一个,给那位好心人一个,“给你,犒劳犒劳。熟鸡蛋,妈妈给我的,让我滚蛋。哈……”
她大声快活地笑着,跑了。
有人在议论,说她叫陈秋华,是独生女,家里经济条件好,能养着她,不让她下乡,她说宁愿断绝关系,母亲只好屈服了。
后来,在县革会召开的欢迎大会上,知青们热血沸腾,有人带头呼起了口号,又跑上台把一个很大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石膏像赠送给县革会。从那尖尖的嗓门,急匆匆几乎有点蹦跳的脚步,还有那对直楞着的小辫,我认出似乎就是下火车时扔鞋的那位。
这就是你,秋华,一个满身孩子气的翘辫子,一个任性的小姑娘。
以后,虽说同在一个县内,却因为各个分散在不同的公社、不同的大队、不同的生产队,交通又实在不方便,大家都混同于一个普通农人,好几年里,彼此几乎没有见面。
由于招工、招生、提干等,第一批同来的知青所剩不多了。
且因为种种缘故,人心浮动。青年们不再埋头劳作,常常到县城走走,互通情报。大多数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情况的,那时,对于知青的管理就像对当地稀疏的农作物的管理一样,粗放得很。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年轻人们便在一起互相交谈,议论些什么,多少也排遣一点内心的寂寞。
那是一个春耕即将开始前的晴好的黄昏,我们沿着护城河漫步。县里正召开“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誓师大会,一些已当了社、队干部的知青属于出席范围,会议期间自然要在城里住几天,好歹有个落脚点,一些不属于开会范围的知青们,因为要办各种各样的事,或者只为了会会老朋友,也借机进城来,形成一个大聚会。
太阳在迅速地下沉,西天上红得像是起了大火,热烈而又壮观。我们走着,忍不住一遍遍地去看那正下沉的火球。迎面而来的人,都被那金辉裹得恍恍惚惚,只见轮廓,不见面目。
她迎面而来,一跳一跳的,脚步很轻快。走近了,我们中有人与她熟识,叫住了她。我们大家都停下来,那个曾经引起我注意的名字,使我禁不住细细地打量她——
一件碎花布的旧棉袄罩衫,旧而随便,却未能掩住那好看的身段。胸脯很丰满,腰细细的,一条屁股上打了补丁的褪了色的蓝卡其布裤直盖脚面,肥肥大大,反显得两腿挺拔修长。这样近地打量她,看见她嘴唇很薄,眼睛很大,乌黑,亮亮的,圆圆的脸庞黑红黑红,覆着风雨留下的粗糙。仍是扎着两个羊角辫,头发黄而枯燥,像干草。
她精神很好,眼睛不回避什么地看人。她好像在说他们正忙玉米杂交的事,时不时地笑,声音仍像我曾经听到过的无所顾忌的大声。她们说了一会儿话,就分手了。陈秋华一个人往回走,脚步匆匆,好像要赶着去做很多事。
继续散步,她的熟人告诉大家,陈秋华总是不一般,在谈恋爱了,而且是她主动提出的。那位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也是和我们同一列火车开到这里来的知青,高大的身架,几代产业工人的出身,是我们中不多的响当当的“红五类”,加上自小在贫困中的磨炼,他沉着、憨厚、积极肯干,当时已官至公社党委书记,知青中没有不知道他的。
陈秋华在一个什么场合跟他聊过几句,回去当晚就给他写了封信,信中直截了当地提出:“给我们的生活放把火吧!可以做你的妻子吗?”然后说:“如果你不愿意,下次看到你,我大概要脸红了。”
那时的我们,无论按自然规律还是按婚姻法,都正该是谈情说爱的阶段。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因为一种扭曲的意识,也因为当时总觉得生活还不甚有着落,恋爱还是个陌生的项目。陈秋华像处理其他事一样,简洁明了地闯到前面。
她得到了呼应。据说他接到信后惊异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最终也是直截了当地写了封回信——
假如你已充分了解我的生活和志向,并且愿意跟我共命运的话,我答应你。
从此,他们之间就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秋华甚至没有过一点腼腆和羞怯,他们谈恋爱,往往只是她一个人在“谈”,滔滔不绝地讲这讲那,他呢,沉静地听,津津有味。他们有缘得很,如今是越来越好了,注定是要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去。
大约是在我离开那个地方回城上大学的那一年,他们结婚了。
当时,不知是因为陈秋华的热情泼辣、能说会道,还是因为她的永远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志向比别人更突出,县里招她进城到派出所当民警。穿着制服的秋华,那个大眼睛的、身背挺直的姑娘,真是神气极了。派出所给了她一间宿舍,以后就成了他们的新房。
婚事原是打算回父母身边办的,结果未能如愿。秋华家不同意女儿这门不当户不对的选择,坚决反对她,还气急败坏地斥责她。
于是她便在暴怒中冲出家门,空着两手找到他说:“我们回去,我不要这个家了。”第二天他们就踏上了返程的火车,秋华绝不愿在这件事上让自己或他受委屈,一再强调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他是爱她的,曾不无自得地跟人说,秋华像一团火,总是通红透亮地燃烧着,一遇杂质,即刻便会爆出异样的火星来。还说,人不能只为自己或爱人活着,但他却愿以他的生命护佑她的幸福和欢乐。
半年以后,我便听到秋华自杀的消息。
冬天,很多人回城探亲,大家聚会的时候,他也来了。
他显然变了,眼神木呆呆的,哀伤像一层大气,簇拥着他。
他说,秋华当上户籍警后,分配给她的工作是清查户口。当时因为在知青中招工、提干,有很多“农转非”的名额,在各个关卡都有人做手脚,将这些极其宝贵的,非同一般的名额给了自己的亲属或特殊关系。上面发现这些问题后,希望找个与本地人事没有瓜葛的知青来做清查工作,查出来是要退回大田里的,这项工作就非同一般。秋华太单纯,也太认真,她很快就触到了那张多少年缔结起来的、无所不在的网,又不顾三七二十一地统统撕破,四面树敌,得罪了很多人,而且都是有权的。最终上面做了决议,要她离开派出所,仍回生产队去。
他说,那天他们一起吃的晚饭,秋华还嘻嘻哈哈的。当时流言很多,有攻击秋华是“狗崽子”(指出身不好)的,也有说她是火箭式上升的干部的。他当然明白这是秋华的工作引起的。为了不再加重秋华的思想重负,他常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话题。那天他是觉得秋华有些反常的,但绝没想到会有那样的结果出现。
他说,那天他是注意到了秋华嘴角时时浮起的讥诮的神色的,却没有特别在意。晚饭以后,他觉得气闷,便想出去走走,当时,秋华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弹,只是抬起头来,看了他一下。他说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她是用怎样的神情望着他的。他无法形容那双亮亮的眼睛里究竟蕴含着什么,但他能感觉到,那双眼睛里包涵着那样多的内容,多得几乎要满溢出来。他为什么不改变主意不再出去呢?他好后悔啊!
他出去总共不过十五分钟,回来的时候,一推开门便是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扑面而来,他便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几乎记不清当时是怎样呼救请人帮忙把秋华送到医院的,他只清楚地记得秋华穿着整洁的民警服,头发梳得很整齐。他抱着她,别人扶着他,面前的房屋,高大的树木,昏黄的路灯,都在摇晃、倾斜……秋华咽气的时候,神色很安详,像是累了。眼睛闭着,脸是苍白的,大理石一样的,两根短辫依然从脑后直楞出来。
他说,秋华已有三个月的身孕,她死后,孩子掉了出来,已经成形了,是个男孩,是他们的孩子,和妈妈一起火化了。那个火葬场是新造的,设备不齐全,没有人管他们,几个知青陪着他一起去收骨灰,没烧透,还有几根骨头,两个发夹。……他说,秋华是有准备的,她写了遗书,藏在枕头里。他给我们念那封遗书的最后段落,那些话已经刻在他心里了——……
生活是美好的,二十五岁的青春年华是美好的,我留恋这一切,我不愿意死,但我不怕死。对于我来说,只有死,才是捍卫正义的最高形式。戊戌政变,谭嗣同在赴死时曾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请自嗣同始。”今天,我就做20世纪的谭嗣同吧。那些专谋私利的人是多么爱惜自己,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活得更好些啊!一个年轻生命的泯灭,会使他们震惊、害怕。我的血不会白流,这也就是我的生命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了。
……
永别了!我和未出世的孩子跟你永别了!忘记我,寻找新的生活吧。以你对生活和事业的忠诚,你是应该有美好的将来的。地球在转,大自然是永恒的。我祝福你今后幸福的心愿,将像这不灭的宇宙一样永存!
……
他用手遮住了双眼,肩膀也因抽泣而微微抖动起来。
我总也忘不了秋华,她的永久的离去把她的身影牢牢地写在许多同龄人的心中。我无意评说她的逝去当或不当,我只是为那样年轻的生命的断裂而心痛欲摧。当我看见冬天的大雪覆盖了一切的时候,我会想起当年那双踩在雪白的冰雪上、穿着鲜红的毛线袜子的脚;当我看见夕阳西下,西边天上大片大片的金红色在翻滚、聚拢、渐渐消退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扎着两根小辫、走路一跳一跳的身影正裹着金辉向我走近;大街上飘着忧伤而舒缓的歌,把我的思绪引向那紧紧闭上了的、大理石般的眼睛和嘴巴——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