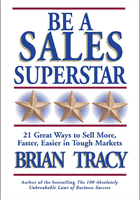秦墨微微一愣,一种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不协调感觉,涌上心头。
“重新都查过一遍了么?”
秦墨慵懒地捏了捏眉心,似是犯困,有些心不在焉。但他深沉的目光始终落在那个蹲在尸体边,仔细查验的某人身上。
他努力压下心底那种不协调的感觉后,这才低声问道。
一旦投入工作,邵小春的全部心思一点都不会分给外界的干扰。听到有人询问,她头都没抬张口便答道:“快了快了,催毛线催?这是尸体!又不是白菜,随便切一切就行了吗?这还剩下最后的两个。如果不出意外,这两个跟其他大部分的人都一样,八成是被毒杀的。”
毛线?是什么线?暗器的名字么?流月碰了碰流年的胳膊,用眼神询问。
流年:这个毛线是重点吗?重点不应该是这厮嚣张的态度吗?流月你个白痴!
流月:大人都没当回事,你还计较个屁啊......你真不知道毛线是个什么暗器?
流年:“......”
那样不恭敬的态度,却奇迹般的没有让秦墨感觉不适。这样鲜活的邵小春,倒是让秦墨莫名的有一种新鲜感。
毒杀。
这倒在秦墨的意料之中。
只有类似于银针的暗器能在短时间内,悄无声息地要了这么多人的命。只是一般把银针当做暗器的,大多都是江湖中的帮派——难道是买凶杀人?
最后一个尸体勘验完成后,邵小春揉了揉早就僵硬的腰,一瘸三拐的朝着秦墨走来。身后那件对于她而言过于宽大的大氅,此时正被风吹的猎猎作响。
望着他的腿,秦墨这才想起一件事。十天前,暗卫曾来禀告,这人朝着凤凰山的方向而去。三天前回京时似乎身上带伤。他当时并没怎么在意——邵小春的忠心完全经得起任何的考验和推敲。
明显僵硬的左肩和不敢使力的右腿,让他的肢体看上去非常的不协调。苍白到几近透明的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显然是短时间内失血过多造成的。即便是有双忽闪忽闪的明亮眼睛加持,却怎么都难掩他瘦弱到不堪一击的事实。
——他在凤凰山似乎伤的不轻。
他抬头抚了抚额头,突然间想知道他去凤凰山干什么去了?怎么会伤成这样?
“你这腿——”
“报告头儿,四十七具尸体里只有一具是被火烧死的。在其他四十六具尸体里,每一具里都有一根这样的小玩意儿。”她小心翼翼地用帕子捏着一根长约三寸,通体柔软的银针。
仔细看来,那银针上还闪着诡异的绿光。
邵小春早在秦墨盯着自己的腿时,心底就悄悄地打起了小鼓。身上这伤太严重了,严重到她根本没办法掩饰。可问题是这伤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事造成的,她根本不清楚。如果冒然出口说谎或者鬼扯,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大的坑还在等着自己。如果是那样,她宁愿像现在这样插科打诨地先混过去。
至于要混到什么时候?她想至少要等自己把“邵小春”的秘密知道个七七八八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当邵小春突然岔开了话题,拒绝谈论自己伤势的时候,秦墨立刻就明白了一件事。
在凤凰山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能让自己知道的事情。
如此看来......秦墨微微眯了眯眼。
再次望向邵小春的视线里,夹杂着几许意味深长。
他接过帕子看了一眼手上银针。
这银针除了被淬了巨毒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和符号。他想了想,将银针递给身后的流风。不知道低声吩咐了什么,流年领命,几个起落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望着流风消失的方向,邵小春一脸的兴奋:这难道就是传说中不科学的轻功么?古人真是诚不欺我啊,这TM居然是真的!
“哪一具是被火烧死的?”
秦墨一开口,尽管声线很低,却立刻就让她回到了现实。
这个boss不好对付,要全力以赴才不会露馅。她稳了稳心神,这才开口道:““呃......这是这一排最后的那一具,”她说话间,已经一瘸一拐的朝着那尸体的方向而去。
“您看,就是这具。”她走过去撩起裹尸布,指了指尸体身上的衣服,有些不解的问道:“这应该是个新娘子吧,看这一身的嫁衣,莫非这文国公府是在昨夜失火前是在办婚礼么?”
大火过后的文国公府,虽然处处都是残垣断壁,却也不难看出这满地的狼藉下,很多未完全烧尽的红绸或者红灯笼里,还夹杂着前院里还没有来得及撤下的残羹冷炙。
棋子正在逼宫,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他身后的主家还有心情办喜宴?
这不合常理。
秦墨心下的疑惑更甚。
“根据这尸体的特征来看,只有这姑娘是被活活烧死的。”
邵小春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了下来——这么小的女孩,人生还未开始,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在大火里断送了一生。她的心里不免为这个姑娘鞠了几把同情泪。
心思转了转,她突然转身问向流年:“亲,你们是从哪里把这新娘子抬出来的?”
亲?指的是我么?这又是什么意思?他挠了挠头,有些尴尬和诧异。想想刚才邵小春对大人的称呼和态度,想来这可能是同僚的意思后很快调整了情绪,将负责抬尸的衙役招了过来。
那衙役想了想,这才低声答道:“回掌镜史大人的话,这个新娘子是从西厢房里抬出来的。西厢房倒在地上的大门上有挂锁,也许是这姑娘被锁死在这西厢房了,所以......”
“是么。”邵小春收回视线,若有所思得摸了摸自己尖尖的下巴,慵懒漆黑的眸子依然盯在那具女尸上……
显然,她对答案仍存有疑问。
“带我去那个西厢房看看,可以不?”心怀疑问的掌镜史大人笑呵呵的问向一边的衙役。
“是,大人。”这衙役哪敢说不行?刚才那京兆府尹的徐大人就是在这邵大人跟前,被三言两语的就弄丢了官职,何况是他这只不够看的小虾米?
二人也没有请示秦墨的意思,一前一后的朝着西厢房的方向而去。
他身后的流年这会有些目瞪口呆。
这?这就走了?
他似乎不太敢看自家大人的脸色,这是赤果果的无视啊!
只是他家大人脚下一抬,竟也朝着那个方向而去。
流年: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直到看到已经倒在地上,壮烈牺牲的那扇应该是属于西厢房的门板时,邵小春才不得不承认小衙役的确是没有骗她。
那巨大的铁锁还大喇喇的杵在门环上呢。
只是......这文国公府为什么要把新娘子琐在这里?为什么只有这个小姑娘没有被毒杀?而是被活生生的烧死在这个院子里?
脑中白光一闪,她迅速问向站在一边的衙役:“除了这个新娘子之外,其他人的尸体是在哪里发现的?室内还是在院子里?”
秦墨下意识的瞥向那衙役,也许从他一进这文国公府的那一刻起,一个一直困扰着他的疑惑,可能就在接下来的回答中得到解答。
被枢密使大人这么一瞥,在这寒冷的天气里,那小衙役竟“奇迹”般的起了一起冷汗,麻利地迅速回答道:“除了这个新娘之外,其他人全都是在院子里被发现的。”
答案似乎就快呼之欲出了。
邵小春有些吃力的抬头与秦墨对视了一眼。她自己目测这个身体至少1米七,要与秦墨对视,还是让她觉得有些费劲。
这人到底是有多高?
那一眼让彼此的猜测似乎都有了印证。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悖论了。”不知道沉默了多久,邵小春这才缓慢开口道。
“悖论?什么悖论?小春,小春你快说啊!”一边已经快被冻僵的流月,实在是没什么耐心继续看这二人在这里打哑谜。
邵小春没有理会快要跳脚的流月,而是走进了那间把新娘子活活烧死的喜房里。
她需要一件东西,或者是一个痕迹,来证明自己的猜测。
喜房的房梁因为受到了高温的洗礼,这会已经整个都坍塌了下来。满地的残渣和碎片,几乎没留下什么完整的物件。
她非常谨慎地在这些碎片里穿行。仔细的查探过四周后,视线锁定在喜房外室里,端端正正摆放着的几个大箱子上。
箱子的主要架构是由玄铁组成,尽管被大火烧过,这会还是能保持着箱子的原有形状。虽然外表焚毁严重,但是却没有垮塌。
这里是喜房外室,又是这样特制的箱子,除了是新娘子的陪嫁之外,还能是什么?
邵小春微滞,挑了下秀丽的眉梢。视线细细的扫了过去,终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