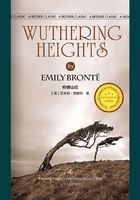我吓了一跳,以为是感染者推开门攻进来了,赶紧跟三毛两人跑出去。跑到刚才大家聚集的那个房间,却发现所有人都趴在窗口往外看,嘴里还不时发出阵阵惊呼。
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那爬上旗杆上的哥们,终于支撑不住往下滑了。
他底下的活尸群似乎看到他滑下去了,纷纷鼓噪起来,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号叫声越来越响。他的手掌跟光滑的旗杆发出吱吱的摩擦声,每滑下一段,他便咬着牙又往上攀爬几步,但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他面向我们这边,我看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神就跟被捕兽夹夹住的小兽一样,恐惧而绝望。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从三层楼高滑落到跟我们齐平的位置,他的脚后离感染者群伸出的密密麻麻的手已经只剩下不到一米,老任家的那个女孩吓得尖叫连连,捂上眼睛不敢再看,看起来他无可避免地要落入感染者之口。
正在我们为他扼腕叹息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地面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起先只是脚底板感觉到一阵轻微的酥麻,到后来,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强烈的震感,连房间里的各种办公用品都跟着抖动起来,发出咯咯嗒嗒的声响。
紧接着,我看到一辆巨大的推土机从我们撤退的路上突然拐出来,它的铲斗高高扬起,发动机隆隆作响,原本就残破不堪的水泥路面在钢制的履带下面不断碎裂。
广场上的感染者有一部分被推土机的巨响吸引,咆哮着向推土机迎过去,但它们的勇猛无惧在同样冰冷没有感情的钢铁机器前面败下阵来,推土机连丝毫顿挫都没有,毫不费力地把感染者碾压在地,在推土机后面形成一条斑斓血路……
接着推土机砰的一声撞在旗杆上,旗杆晃了几下,便颤颤巍巍地向我们这边倒了下来,旗杆上那人连忙手脚并用爬过来,我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了进来。
“快下来!”楼下传来一阵大喊,我看到推土机驾驶室里军士长正在朝我们激烈的招手,而推土机的铲斗已经架在我们窗户下面了。但推土机旁边马上便被感染者围得水泄不通,一些手脚相对灵活的感染者爬上履带,挤在驾驶室周围,把玻璃拍的乒乓作响,里面的军士长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叶孤舟,马上就会被巨浪淹没。
我和三毛对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同时说道:“你先下去接应!”
我愣了一愣,三毛马上猛地一扯抓住我的手臂,把我用力往窗户上推,我也不再推让,顺势把腿架出窗外,双手扶着窗户沿,双脚稍往下一探便踩住了推土机巨大铲斗的锯齿状的外沿,我双手一松,稳稳地跳进铲斗里。
紧接着,冯伯的脚率先探了出来,我慢慢地托着他,把他安全地接了下来。然后是老任家的那个女的,再接着是杨宇凡、老吕、三毛……这时候铲斗里已经站不下人了,我朝三毛做了个手势,俩人爬出铲斗,手脚并用地爬上连着铲斗的液压式机械臂,车头上的几个感染者听到声响,齐齐地转过头来,嗷嗷叫着向我们扑过来,我把抓着机械臂的手微微一松,借着向下的冲力,一脚蹬在那感染者的胸部,然后抽出军刺慢慢地刺入最靠近我的那个感染者眼窝里。
我心里感到一阵强烈的快感,对!没有以往的恐惧,只有畅快淋漓的复仇的快感。
我借着位置优势连杀三个感染者,和三毛一起肃清了车头,这时老任家的另两个人和刚才爬在旗杆上的男子也从楼上下来,进了铲斗。
“走走走!”三毛用力地拍打驾驶室的玻璃。
车子猛地一震,我身边的烟囱突的一声冒出一股黑烟,推土机顿了一顿,紧接着原地打了一个转,履带底下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乱响。
“耶!”所有人都是一片欢呼,我听到一阵疯狂的咒骂声,声音很陌生,不知道是老任家那几个还是旗杆上那汉子发出的。
推土机原地转了180度,把所有攀上车身的感染者都甩了下去,军士长把铲斗降了下来,铲斗里的人也都越过机械臂爬了过来。我和三毛也不客气地拉开驾驶室的门,挤了进去。
军士长也没什么反应,只是翘首四顾,看见大家都找到了地方并且抓住了固定物,便一踩油门,推土机像一头垂死的巨兽一样号叫了一声,向挤满感染者的大门缓缓动了起来。
500匹马力的发动机疯狂地嘶吼着,这辆将近16吨重的钢铁巨兽终于在撞击伸缩门之前加速到10公里每小时。我紧紧地抓住门上的一个把手,整个心脏都勒了起来,生怕一下子无法撞倒伸缩门,那样我们就再没有脱险的可能了。
但推土机显然非常不屑于我的担心,它像是中世纪重装骑士一样向前挺近,平放着的铲斗像是骑枪,凹凸的锯齿形铲刀首先插入伸缩门的缝隙,伸缩门猛地向外凸出,外面挤着的感染者群一下子被弹出一圈空隙,紧接着,一阵让人牙酸的金属扭曲声响起,推土机没有丝毫停顿,继续往前,铲刀把伸缩门连根拔断,一下子铲到了空中!
军士长扳了几下操纵杆,整个驾驶舱带着机械臂向左转了90度,然后铲斗往下一倾,伸缩门便被抛在了地上。推土机继续往前,我们前面只剩下密密麻麻的感染者,驾驶舱又转回原位,慢慢地压了上去。
我这才松了口气,其他的伙伴们也都欢呼起来,连刚刚抱团痛哭的老任一家人,现在也破涕为笑,那旗杆上的汉子,此刻更是手舞足蹈。
只有老吕,还是神情木然,痴痴地看着一个方向。我顺着他的视线转头看去,只见车后面张牙舞爪追上来的感染者中,有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女性,身材高挑,如果忽略掉她被咬掉一半的腮帮子,长相还是很好看。
我朝三毛使了个眼色,三毛也转头去看,然后回过来叹了一口气,片刻之后他对军士长说:“带枪了吗?”
军士长抬头看了他一眼,迟疑了一下,然后朝自己座椅下面努了努嘴,三毛探身下去,从里面摸出一支95式突击枪来。
三毛褪下弹匣看了看子弹,然后拉开枪栓,打开车窗探出了上半身,举枪瞄准。
砰的一声枪响,女尸应声倒下。
我看到老吕打了个激灵,无声地张了张嘴,然后向我们看过来,我朝他微微点头,他也朝我点了点头。
推土机发出隆隆的声响,缓慢而不可阻挡地往前推进,我们站在推土机的高处望去,大概有半条街,两三百米都是密密麻麻挤满了感染者,至少有几千只。推土机像是行驶在灰暗斑斓海上的孤舟,白色手臂、黑色头颅组成的感染者巨浪连绵不绝地拍打在前伸的铲斗上,拍打在滚滚向前的履带上,撞得支离破碎。那些撞击、碾压的感染者浑然不觉,没有发出一丝惨叫,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喉咙口挤出那让人头皮发麻的呻吟号叫。
我们不得不把那些爬上车身的感染者清理出去,这些感染者往往都被推土机压的只剩半个身子,只靠两只手攀上车身,脸上身上都被推土机狰狞的钢铁外壳撞击的遍体鳞伤。
我们丢了粪叉子,只能等感染者靠近了用刀砍,用军刺刺,或者直接用脚把它们踹下去。
突然,从车头方向传来一阵尖叫,我抬眼一看,只见一大堆感染者从铲斗上翻滚下来,原来铲斗里已经装满了感染者,而且越堆越多,终于整片都翻了下来。这堆感染者大部分都撞到机械臂上,摔下两边,但少数几个抓住了机械臂,仍然挣扎着爬了过来。
老任家那女的吓得连声尖叫,不由地向后一跳,一下撞在那年龄偏小的男孩身上,那孩子原本正用脚去踹一个攀着推土机空气滤清器的感染者,这一撞竟偏离了方向,从那感染者的头颅旁边擦过,感染者一口咬在了他的小腿肚上,接着抓住了男孩的小腿,那男孩被这么一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便一头栽下了车。
“小益!”那女的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回身伸出手想去把自己的亲人拉回来,却连自己也差点摔下去,幸好被另一个男的一把抱住,但她还是在他怀里挣扎着想要跳下去救人,那男的只好一只手紧紧地抱住她,另一只手牢牢地抓住车头上的烟囱。
“小心!”在他们旁边的老吕一声大吼,一个跨步过来,把那个已经快爬过机械臂的感染者刺死。
“你他妈的已经害死一个了,还想再害死一个?”老吕疯狂地对着那女的大吼,“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要好好活下去,这样才对得起死去的人,要不然,就自己一个人去死!”
那女的听到老吕的厉声大骂,明显愣了一愣,随即便收起了嘶喊,神色一片黯然,又过了几秒钟,她轻轻挣脱男人的怀抱,扬起手里的砍刀,向旁边的感染者砍去。
这时,我们的推土机已经向前冲出了一百多米,活尸群的边缘地带已经近在咫尺,这方圆几公里的感染者已经全部集中在这里,只要冲破这片区域,就可以摆脱他们了。虽然推土机只有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但以感染者蹒跚的速度,肯定是追不上的。
眼看着就要逃出生天,所有人都兴奋起来,奋起余力砍杀感染者。终于,好像一挂鞭炮燃烧到了尽头,我们前面忽然一亮,推土机冲出了感染者群,驶入了空旷地带。
“哈哈!”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但还没等我们高兴多久,刚把感染者群甩下五六十米,突然推土机猛地一震,差点把我们都甩下去,然后便一动不动了,无论军士长怎么调进退档、怎么踩油门,车子仅仅是颤抖几下。
“快跑吧!履带断了!”军士长在另一边大声喊。
我们碰到了城市保卫战中所有军队遇到过的一样的难题,那时在电视直播中,那些坦克、装甲车组成的洪流看起来坚不可摧,只是血肉之躯的感染者好像根本没有胜算,但实际上,这些钢铁怪兽总是会被源源不断的尸海困住,最终不是损坏,就是在团团包围中耗尽油料。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甩开感染者群很远的距离,对于这群速度极慢的感染者来说,五六十米已经足够我们逃脱了,在一阵疾奔之后,我们终于和感染者群拉开了足足两百多米,然后在一幢写字楼后面隐藏了下来。
“它们追不上来了。”军士长极小心地伸出头看了看,然后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也伸出小半个脑袋观察了一下,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么小心,众所周知,感染者的视力极差,在这个距离,即使你对着它挥手都不大可能被发现。我看到那群感染者还是挤满了半条街,但此刻已经不再统一行动,而是自顾自地,漫无目的地四处溜达起来,感染者之间频频相撞,就像是初中物理中学过的布朗运动。我收回脑袋,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他妈的你们为什么自己跑了?”一声刻意压低嗓音,但极度愤怒的声音突然响起。我转头一看,只见老任家剩下的那唯一的男的,正抓着军士长的衣领质问,“啊?为什么把我们扔在那里?我们一家……呜呜呜……”男人说着说着哭了起来,但还是竭力压低自己的嗓音,可那种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呜咽声,却听起来格外的悲戚。
“呜呜呜……我们一家……全死了……呜呜呜……你们他妈还是人吗?”男人一边哭诉,一边揪着军士长的衣领用力摇晃。
我看到军士长紧绷着脸,但眼神中闪过一丝愧色。
“是啊,张队长……你们也太不仗义了,凭什么把我们扔下自己跑了?”那旗杆男也阴阳怪气地插嘴。
“这是预先设定的战术,如果感染者太多无法力敌,可以让一部分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军士长像背书一样苍白地解释。
“我们就是那一部分人?你们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老任家的男人一下激动起来,他身后的女人连忙过来安抚,轻轻地拍着他的背,让他安静下来。
“先告诉我们?”旗杆男嗤笑一声说,“先告诉我们我们还会来吗?明摆着就是想让我们当炮灰,送死……”
“先别说这个……”冯伯突然站起来挥着手,他对着军士长的脸,沉声说道,“按你这么说,后来你们是拿到粮食了?”
军士长微微点了点头:“我们从后门绕了进去……”
我们几个一下子都站了起来。
“有多少?”三毛急切地问。
军士长环顾着看了我们一眼,缓缓地说:“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