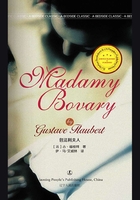这时身后又不断有人赶到,所有人都推搡着往前挪动,然后在看到门口的景象之后被吓得哇哇大叫,有几个甚至直接瘫倒在地。第二组的那对父子,那个十五六岁的儿子把头埋在自己父亲的胸前,抽泣着不敢看外面,他的父亲搂着他的肩膀,双眼迷离而又麻木,另一只拽着粪叉的手指节发白,微微颤抖。
我着急地四处张望,但是这个广场上空空荡荡的,仅有开裂的混凝土地面,从缝隙中生长的杂草,几个被遗弃的笨重机器。三根生锈斑驳的旗杆子孤零零地戳在地上,似乎是在嘲笑我们这群无路可去的人。伸缩门在大约五十米外,后面是挤成一堆根本看不清数量的感染者,它们在看到我们之后更大声地呻吟号叫,它们的肢体,透过伸缩门之间的缝隙,像水蛭一样密密麻麻地蠕动,那道单薄的伸缩门被不断地推挤,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咯声响,似乎随时都要倾覆倒下。
“它们追来了!”后面有人大喊。
我扭头一看,只见刚才那群感染者已经享用完它们的“美食”,继续向我们逼过来。那几个被咬的人大多还活着,但感染者们似乎已经对他们没了兴趣,任由他们在地上翻滚惨叫。这是索拉姆病毒惯用的伎俩。道长曾经说过感染者们其实不需要血肉来提供营养,它们要的只是传播,它们存活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地通过撕咬传播控制它们的病毒!
“快抄家伙!跟它们拼了!”正在众人都愣神时,冯伯突然大吼一声。
我如梦方醒,几个团队的领导者这时候也反应过来,呼喊着让自己的团队拿好武器准备迎敌。
这时我们已经身处办公楼和伸缩门之间的小广场上,空旷的空间让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像刚才一样组成一条阻挡感染者的阵线,而且此时也没了军士长那样全局指挥的人物,我们所有人又成了一盘散沙,以各自的团队东一撮西一撮地分布在各自以为相对安全的角落里。
“结阵!”三毛朝我们大喊,杨宇凡、林浩和冯伯三人迅速站好位置,伸出手里的粪叉子,但是冯伯似乎已经耗尽体力,手里的粪叉子摇摇晃晃的东倒西歪。
“我来!”大力低吼一声,一步上前抢下冯伯手里的粪叉子,替上了冯伯的位置。
此时尸群已经近在眼前,前面几个满脸新染上血污、龇着牙大张着嘴,像是刚从地狱出来的猛鬼,更多的是那些一层一层像是山呼海啸般席卷而来的呻吟号叫声,让我头皮一阵阵的发麻,双腿不争气的大幅度颤抖起来。
“准备!”三毛大吼一声,三支粪叉子平平的伸出,我看到杨宇凡和林浩嘴唇煞白,眼里尽是惊恐,大力紧咬牙关,下颌肌肉一条条地绷出来。
“推!”粪叉子像蛇咬一样向前探出,当先的几个感染者被牢牢地卡在杆头伸出的枝丫上。
“上!”就像是本能反应,我举着军刺冲上去,用力把军刺刺入眼前那个活死人的眼窝,乱舞的手顿时不动了。
“撤!”三毛又喊,我迅速退了回来,前面的三个推挡手也是齐齐向后一步,同时把手里的杆子一甩,三具尸体被甩落在地。
空旷的广场让我们有了腾挪的空间,相比刚才的挤作一团,现在我们有了更大的杀伤力,凭借我们几人默契的配合,几轮下来,已经有十几个感染者倒在我们的军刺之下。
但也就仅此而已,相对于数以百计的感染者,这区区十几个实在是杯水车薪,而且别的团队对这套阵法并没有我们那么熟练,在短短几分钟之后已经险象环生。
首先是第一轮崩溃时遭受重创的第三组,他们仅剩的五六个人连手里的武器都丢了,他们空着手在广场上乱糟糟地四处逃窜,妄图通过灵活的跑位避过行动迟缓的感染者,但很快便体力耗尽,有几个撕心裂肺地惨叫着被感染者团团围住,还有几个聪明一点的,躲在了几个尚能维持阵型的团队后面。最奇葩的是一个可能自认为身手不错的,竟然徒手爬上了一根旗杆子,引得一群活死人挤成了一个球在旗杆底下引颈嗥叫。
紧接着是第二组的那对父子,这次换成了父亲做推挡手,但在他叉住一个感染者后,他的儿子却迟迟不敢上前杀死感染者。
“快!快上来砍死它!”父亲对着儿子嘶吼,但他儿子却躲在他身后,脸上眼泪横流。
“快点!”那父亲几乎是哀号起来,他的粪叉子上又增加了一具感染者,这让他脚步踉跄连连后退,但他儿子还是只顾自己哭泣,连看也不敢朝前看一眼。
在第三具感染者堆上他的粪叉子之后,他终于不堪重负,向后摔倒在地,那三具感染者重重地压在了他身上,这位父亲没有惨叫,只是梗起脖子挣扎着去看他的儿子,但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儿子直直地站着,抽泣着不做任何抵抗,然后被一个感染者咬中脖子。
不断有人倒下,我耳边充斥着恐怖的惨叫声,每一个团队,只要有一个推挡手倒下,阵型出现缺口,便会迅速的崩溃,然后四散而逃,最终体力耗尽被感染者包围。仅仅五六分钟后,广场上还保持完整阵型的,就只有我们和老任一家了。
“老吕,快去开门!”三毛从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女感染者脑门上拔出军刺,摸着脸上溅上的血污扭头对老吕大喊。
我回头一看,这一阵且战且退,我们已经被逼到了办公楼附近,离楼底下那道紧锁的卷闸门只有十多米的距离。
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在感染者围攻之下,躲进某幢孤立的建筑,从来都是最差的选择,因为那会令你陷入绝境,到最后也只是换一种死法罢了——从被感染者咬死换成饿死冻死。死亡的过程也会拖得冗长无比,没吃没喝感染者环绕的情况足以让任何精神强韧的人都陷于崩溃,更别说不久前我们刚经历过一次被困在妓院天台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遭遇了。今天,Maggie Q还会不会从天而降来拯救我们,只有天知道了。
但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现在的情况哪怕拖一分钟、一秒钟也是好的。老吕应声而去,我们的压力马上增大了,冯伯已经虚脱,早就只剩下象征性的存在,事实上的突击手只剩下我和三毛两人,老吕一离开,顿时险象环生。
我和三毛一左一右,保护着推挡手们的侧翼。我旁边是林浩,这个在危机前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小职员,此刻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仿佛每吼一声他心头的恐惧就会降低一分。他的手臂已经无法用力抵住粪叉子,粪叉子的一头直接戳在他的胸膛上,那地方像是被子弹击中一样渗出一摊鲜血。
三毛已经不再发出指令,我们只剩下机械式地把手里的军刺刺进某个感染者的头颅,然后拔出来再刺,我现在甚至开始感激起把我们扔下的军士长来,如果不是他送给我们的军刺,还是拿着原先那条沉重的铁钎,只怕现在早就连手臂都抬不起来了。我们的脸上身上都溅满了感染者那种让人恶心的黑色黏稠的体液,像是被人泼了一桶黑色的油漆一样,浑身上下都是斑斑点点。
“啊……”我听到中间的杨宇凡一声惨叫,似乎是身后绊倒了什么东西,向后一歪,一屁股坐倒在地。幸亏他手里的粪叉子并没有歪斜,现在一头撑在地上,另一头还撑着一个食尸鬼,只是阵线上出现了一个破口,两个感染者从中间挤进来,眼看着就要扑向地上的杨宇凡。
“快起来!”大力嘶吼着把他手里的粪叉子猛力一摆,把杆头叉着的感染者向一边甩出去,接着他像是武侠片中的高手一样,使了招横扫千军,把手里的粪叉子像八卦棍一样向外挥舞,把那两个挤进来的感染者挥倒在地。我趁着这个机会,从林浩身边打了个旋,把军刺扎进杨宇凡粪叉子上叉着的感染者太阳穴里,然后把杨宇凡从地上拉起来补上了空缺。
“老吕!快点!”我扭头朝老吕大喊,但是一回头,却看见一个感染者正向蹲在地上开锁的老吕扑过去。
“小心!”我连忙示警。
但是没等老吕抬头,感染者已经猛地扑了上去,老吕猝不及防,被扑了个正着,和感染者来了个脸对脸,感染者大嘴一张便往老吕喉咙上咬去,老吕哇哇大叫,一把掐住感染者的脖子,一人一尸就这么僵持住了。
我正要上前帮忙,却不料从我这一侧又有一个活尸向林浩逼过来,林浩双手撑着粪叉子,吓得大叫,我只得转身先去对付眼前直接的威胁,本想叫冯伯去帮一下老吕,但左右四顾,却找不着他人了。等我了结完这只感染者,回头看时,只见老吕还是死死地撑着感染者的脖子,但是感染者的嘴已经越来越近,嘴里还不住地往下滴黑色的液体,老吕不得不紧闭着嘴,把脸侧到一边。
“啊!”突然一声大吼,冯伯从一旁冲过来,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手臂抡圆了,砰的一声重重地砸在感染者的头上,感染者顿时白了白眼不动了,老吕连忙把感染者从身上甩脱,从地上爬起来重新开始开锁。
我心下稍安,继续转身对付正面的感染者,但现在三个推挡手组成的阵线已经显出了破绽,大力没有问题,手里的粪叉子还能维持用力地推、甩等动作,而林浩已经只能把粪叉子的一头顶住自己的胸膛,然后机械地防御,根本没有余力做其余的动作。
最危险的还是杨宇凡,原本因为压力相对小才把他安排在中间,但现在缺了一个人后,中间没有突击手去清理感染者,他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至于三支粪叉子从中间位置已经凹下去一大块。
我见势不妙,连忙移动到杨宇凡身后,想从后面顶住他,把他推上去补住缺口,但我还没来得及使劲,从缺口处就挤进来两个感染者,一旁的林浩下意识地想学大力把粪叉子打横去拨,却不料自己已经油尽灯枯,根本没有余力,粪叉子向前一卸力,身体失去了倚靠,反而向前打了个趔趄,一下子被前面的感染者扯住了领口。
林浩惊恐地大喊着把粪叉子撑住那感染者,身子往后缩,他的T恤发出吱吱咯咯的撕裂声,整个前襟都被撕了下来,眼见着就要脱离感染者的爪子,却不料杨宇凡留下的缺口这边,一个感染者终于完全钻了进来,一把抓住林浩的手朝着他的胳膊就是一口!
林浩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把手中的粪叉子一丢,从腰间拔出砍刀,一刀剁在那感染者的脖子上,黑血向上飚出老高,但感染者浑然不觉,还是死死地咬住林浩的胳膊。还没等林浩把它扯下来,他的另一只手又被感染者咬住,紧接着涌上来的感染者越来越多,他整个人在一息之间便被感染者淹没了。
林浩一死,我们的阵型瞬间崩溃,大力也索性扔了粪叉子,抽出他的军刺砍杀起来,杨宇凡已经力竭,喘着粗气跌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没有了一米五长的粪叉子的保护,感染者那张恶心的脸近在咫尺,我甚至能看见它们臭气熏天的嘴里漆黑的小舌头。我护在杨宇凡身前,看到感染者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涌过来,一股透顶的绝望从心中升起来,觉得这下是真完蛋了。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哗的一声,那道该死的卷闸门终于被老吕打开了!
“快走!快走!”老吕在我们身后连声催促,我把杨宇凡从地上拉起来,跟着三毛连滚带爬向后跑,大力在后面掩护了我们一下,刺死了两个突前的感染者,接着也转身就跑。
卷闸门只向上开启了差不多半米的高度,我在跑上三级台阶之后便一个滑步,贴着地面从门下面翻滚进去,接着三毛杨宇凡和大力也滚着进来了。
“别关门!”老吕正想拉下卷闸门,就听见门外有人大吼,接着一只手伸进来托住了卷闸门,几个人像我们刚才一样滚了进来。我一看,原来是老任他们一家人。我连忙过去从门底下把人拖进来,但只拖进来三个人,然后我们便听见纷纷涌来的感染者撞到卷闸门上的声音,卷闸门剧烈地摇晃起来,那只托着门的手也缩了回去,透过门下面的缝隙,我们看到老任已经被推倒在地,一个感染者正从他脖子上扯下一块肉来。
“关门!”老任朝我们无声地张嘴。
老吕用力一按卷闸门,哗的一声,我们顿时陷入了黑暗之中。
卷闸门继续发出砰砰砰的撞击声,而且声音马上变成汹涌的推搡,卷闸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哗哗声,向里面凸出来。
“快,拿什么东西挡住门!”三毛朝我们大喊。
这时我的眼睛已经慢慢适应里面昏暗的环境,左右四顾,发现我们正身处一个大厅,左右两边都是长长的走廊,一架螺旋形的楼梯在我们背后蜿蜒而上,一边的墙上贴着几个亚克力切割字——钱潮市伊佳乐食品有限公司,在它前面则是长长的前台。
“把那个拖过来!”我指着前台大吼。
我们五人加上新进来的三人连忙冲过去开始搬这个巨大的前台,幸好这个台子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是大理石制作的,而是外面贴了一层仿大理石饰面板,只在面上嵌了一层人造石台面,所以它的重量比我们想象中要轻很多。
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后,这个质量不太好的木头前台终于被我们推到了卷闸门前,我们又去旁边的一个会议室里搬了一张会议桌还有许多椅子,把它们层层叠叠的堆在了门前,看起来就像是《悲惨世界》中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居民用家具建造的街垒,那道薄弱的卷闸门终于不再岌岌可危了。
危险暂去,我们都瘫软在地上大口地喘气。这时我才闻到一股呛人的霉味,这间大厅里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就像是很多年没人进来过,大厅没有窗户,只有螺旋形楼梯上方射下一束微光,激起的灰尘在光束里上下飞舞。
“我们上楼!”三毛说道。
我点了点头,几个人同时向楼梯上走去,但我走到半路才发现老吕还在门前,愣愣地看着轰隆作响的卷闸门发呆。
“老吕……”我叫了他一声,但他还是没有任何反应。“老吕!”我加重语气又喊了一声,他这才如梦方醒,朝我看了过来。我吓了一跳,老吕脸色死灰,像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眼神里尽是恐惧。
“怎么了老吕?快走啊,说不定楼上还得你开门呢!”我也没太当回事,因为当时我们的脸色都好不到哪里去。
“啊?哦哦……”老吕匆忙应着,拔腿跟了上来。
楼上并没有什么锁需要开,每个房间都敞开着,也都是平淡的布局设计,中间一道走廊,两边是玻璃隔断的办公室。但我们一上楼梯,透过南面的玻璃窗,就看到了让我们惊奇万分的一幕。
只见刚才那个爬上旗杆的哥们,现在还像只猴子一样孤零零地挂在上面!
我们走进一间办公室,打开朝广场的窗户向外面看,那人似乎是个攀爬高手,此刻爬在旗杆的最顶端,比我们所在的二楼还要高很多。他用一根皮带绕过自己的臀部,和旗杆系在一起,跟紧抓着旗杆的双手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支撑点,让他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抓住旗杆,但是现在他已经明显乏力,抓着旗杆的手臂在微微颤抖。而他的身下,则是层层叠叠挤成一个圆圈的感染者。
那哥们大概是听到了声音,转过头来看我们,他满头大汗,眼神里尽是恐惧和绝望,但他并没有喊救命,大概是知道喊了也没用,我们根本不可能隔着二十多米的距离冲过重重活死人,把他救下来。
我摇摇头,不忍再看,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来。这时一股沉重的疲惫感向我袭来,我忍不住呻吟了一声,感觉到四肢百骸全都酸痛得难受,尤其是手臂的二头肌、三头肌还有小腿的腓肠肌,简直就像变成了坚硬的石头,不住地痉挛。
我抽着冷气,龇牙咧嘴不住地搓揉这几块肌肉,然后看到老任家的三人在一边哭哭啼啼的,他们两男一女,年纪大点的看起来三十多岁,长着跟老任一模一样的高大凸出的额头,活像是年画中的老寿星,这应该是老任的儿子。女的跟他年纪相仿,脸上故意涂抹的黑乎乎的,看不出相貌年龄,另一个男的个子很高,但面相很嫩,最多只有十七八岁的年纪。
“嘿……”我正琢磨着呢,一边的三毛突然用肩膀碰了我一下,朝我使了个眼色,然后起身走了出去,我连忙跟上。
“你有没有觉得老吕有点不对劲?”刚走出办公室,三毛就急着说。
“什么?……咦?”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老吕整个人瘫软在一张大班椅上,两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
“是很奇怪啊……”我嘀咕道,老吕大概是本着“贼不走空”的职业精神,每到一个新地方,做的第一件事必然是翻箱倒柜,我从没见过他像今天这样六神无主地坐着。
“你说他是不是被咬了?”三毛嘟哝道。
我浑身打了个激灵,再一看老吕,可不就是一副死了娘似的衰样。我们跟老吕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一个多月的患难与共可比几十年的泛泛之交要认识深刻的多。他这人虽然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关键时刻除了大力就数他最靠得住,也许是多年在江湖上行走带来的经验,危险时刻他往往比任何人都要沉得住气,但像今天这样的失态我还从来没见过。
“可能是刚才开门的时候被咬了?”我想到刚才他被感染者扑倒,掐着感染者的脖子和感染者相持的样子,“现在怎么办?”我摸着头问道。
三毛沉吟了一会儿,咂着嘴说:“先把他叫出来吧,咱俩先问问,这儿还有其他人,搞不好会引起恐慌。”
我往里面一看,只见老任家那三人还是抱在一块痛哭,大力、冯伯和杨宇凡也是垂头丧气地坐着,一片愁云惨雾。我暗忖如果冒冒失失进去说我们之中有人被咬了,还真不知道这些人会做出什么反应。
于是我朝三毛点点头说:“那我把他叫出来,你找个房间。”
三毛左右看了看,指着走廊一端唯一的一扇不透明木门说:“就那儿了。”
我随意编了个借口叫老吕出来,他丝毫没有怀疑,事实上他现在失魂落魄,似乎根本没听清楚我在说什么,只看到我向他招手便跟着我出来了。
我打开木门,招呼老吕进去,三毛就站在门边上,我刚把门关上,三毛便一把抓住老吕的领口把他顶到墙上。
“你他妈被咬了是不是?”三毛沉声低吼。
“啊?什么?”老吕似乎完全不知道三毛在问什么,惊恐而诧异地问。
我心里暗叹了一口气,这样的场面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已经见得多了,几乎所有被咬的人,一开始都是试图掩盖,接着便是矢口否认、假装被冤枉的愤怒,然后在暴露确凿证据——身上的咬痕——之后是苦苦的哀求……每个人都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即使被咬也不会尸变,但我们从来没看到例外。
“少他妈装蒜了!”三毛撕扯着老吕的衣服,“我们都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老吕对三毛伸过来的手左推右挡,嗓门一下大了起来,“你们别他妈冤枉人!我什么时候被咬了?”
三毛朝我看了一眼,似乎是在说戏码又上演了,我叹了口气,走过去抓住老吕的一条胳膊,柔声说道:“行了老吕,咬了就咬了,反正谁都有这么一天,兄弟们先送你上路,免得你变成那样的孤魂野鬼……”
老吕听了我的话,一下子暴跳如雷,猛地一下把我的手甩脱,大声吼叫着说:“老子脱给你看!”说着他几下把身上的T恤脱下来,重重地掷在地上,然后解开皮带,褪下裤子,一只脚狠命一踢,把裤子踢得远远的,然后张开双臂。
“来啊!来看啊!哦对,还有这,感染者咬我屁股蛋了!”说着又把内裤脱下来丢在身后的沙发上。
我和三毛都尴尬起来,但还是仔仔细细地观察起老吕的身体。老吕大概一米七出头,在中国南方,算是不高不矮的身材。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这几个月来都没刮过胡子,稀疏卷曲的胡须乱糟糟地覆盖在他的下颌直到脖子,脖子下面,以圆领体恤的领口为界,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上白下黑,那是长时间只洗脸不洗澡积累的泥垢。他的胸膛因为气愤而激烈地上下起伏,肋骨像是某种怪兽,一根根暴露在外,只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皮肤。从肋骨上下来,他的腹部以一个令人恐怖的角度向内紧缩,看起来羸弱不堪,他的阳具不知道是出于愤怒还是恐惧,缩成了一团,挂在骨瘦如柴的双腿之间,看起来像是一个悲惨的笑话。整具躯体散发着难闻的臭味,让人憎恶和恶心,但仅此而已,没有咬痕!我们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确实没有!
“看清楚了吗?”老吕像是达.芬奇的名画《维特鲁威人》那样大张着手臂,愤怒地对我们叫喊,“有吗?有被咬吗?”
“行了行了!”三毛讪讪地笑着说,“我们这不是以防万一嘛!谁让你今天这么奇怪的。”
我从地上捡起老吕的衣服递给他:“对啊,你今天不对劲啊,怎么好像死了老娘一样?”
没想到老吕一听我这话,竟然像个孩子似的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也不接我的衣服,就这么赤身裸体的,捂着脸蹲下号啕大哭起来。
我从来没看见一个男人哭得如此伤心,我和三毛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做什么,只得呆呆地看着他。
还好,老吕哭了一会儿后,自己站起来,抹着眼泪说:“外面……我老婆在外面……”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
要说危机爆发以来最残酷的事情,莫不过目睹自己的亲人、爱人被病毒感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而是我还活着,你却成了活死人。曾经不止一次,我暗自庆幸自己的父母走的早,让我可以避免这种残忍的境遇。
“我和她都是贵州山里来的……”老吕套上自己的内裤,哽咽着说,“我们初中就好了,那时候家里穷,两家都穷,但是她家里嫌弃我,说我给不起彩礼,他爸要把她嫁到山外面去,我们就逃了,出来打工,一开始在东莞,做鞋,老板说我们没有身份证,抓到就是童工,只给一点点工钱,可是我们很开心,终于有地方住,能吃饱饭了……”
老吕说到这又忍不住一阵抽泣,三毛在他背上拍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继续说:“后来我们有身份证了,我们换了很多工作,可两个人总是在一起,后来工钱也慢慢高起来,她爸爸也同意了,我们在老家办了婚事,日子总算眼看着要好起来,可是,我开始赌博……
“一开始只是跟老乡小搞搞,到后来越输越多,一个月的工钱还不够还赌债,她就跟我吵,我嫌她烦,就打她,有一次打的厉害,出血了,去医院才知道她怀孕了……孩子没保住……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收手,花钱也大手大脚。到后来,我们两个人的工钱加起来也根本不够我几天花的,老板把我们赶了出去,老乡们也都知道我这副样子,没一个厂子肯要我们,到最后,我竟然跟她说,你长得漂亮,东莞这么多夜总会,你去卖啊!”
老吕说到这里,情绪又失控,号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她这个人很傻,真的听我的出去卖……她不像别的小姐,有点钱就给自己买手机,买包包,她手里有一分钱都存起来,而我……呜呜呜……我不仅花她的钱,还打她,说她脏……呜呜……她这个傻女人,真的以为自己脏,自己有错,就任由我打骂,从来没想过要离开我……”
“直到有一天,我因为小偷小摸被抓住了,被人打了个半死,回到住的地方,她抱着我哭,我也哭,我说为什么一样是人,我们就要生来被人打,要做妓女,被人这么轻贱糟蹋?她说我们不做了,她攒了钱,有十几万,我们回家去,一起开个小店……我说好……”
“可是第二天,我就偷了她的银行卡,把她存的钱全部取光,还拿了她的手机,她的首饰……后来知道都是假的,不值钱,我全扔了……我一个人跑了,不到半年,我就把十几万全花光了,我也没脸回去,又开始东摸西骗,终于被公安局抓住,判了六年!”
“后来她来监狱里看我,我没见她,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自己不会好了,她跟着我就是害她一辈子。我在监狱里提出了离婚,她马上就同意了。我在监狱里认识了一些人,学会了怎么做一个真正的贼,出狱以后我四处游荡,连老家也没回去过,没听到过她的一点消息,没想到……”
老吕又失声哭起来,深吸了几口气以后才说:“没想到再见到她竟然是在这里……”
老吕说完自己的经历,一直埋头痛哭,我也忍不住鼻子发酸,心里像被剜了一刀一样尖尖的疼,我看到三毛眼里也有泪光闪动,神色戚然。我知道老吕的一番话肯定也勾起了他的一些回忆,虽然我没正面问过他,但知道他的父母亲人一定也在灾难中罹难了。
我拍了拍三毛的肩膀以示安慰,他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我们二人沉默着,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劝慰一个痛哭的男人。忽然,我听到外面响起一阵惊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