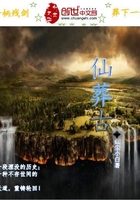许多北京人不拘小节。
这种不拘小节首先反映在穿着上的不太讲究。
北京大凡有份不好也不赖的工作的人,上班时的穿衣倾向是向领导潮流的白领阶层看齐,只是由于其他原因,或许是北方人疏懒,或许是表现一种品味,许多人爱着休闲装,据说,这类服装不容易显示富贪贵贱,符合北京人不喜招摇的个性。不过在不拘小节的人这里,就显得过分随便。他们穿着随便偶尔还不太干净的衣服,堂皇出入酒楼宾馆,乃至美术馆音乐厅。可能这倒现出这部份人之所以不太讲究的原因:要干的重要事多着呢,谁乐意穿衣戴帽的没事折腾。
有了这些不拘小节的人,京城凭空多了些景观:大庭广众下“丫丫”的嚷叫,体育馆里“傻×”的呼喊,墙根前旁若无人的撒尿,夏天里光着膀子的招摇。
据说,北京现在又增添了新的爷一族“膀爷”。光膀子人之谓也。还听说,北京市某大报买了一万件T恤衫,派出大量人员上街,见一“膀爷”发一件。
北京的膀爷恐怕不止一万名,这一万件大概不够用。
膀爷的形象一般是这样的:穿一双随便什么鞋,一条齐膝大裤衩子,满身肉,大肚子,圆脸上油光满面,眼不大而像没睡醒。仰靠在露天酒桌的沙摊椅上大口灌啤酒,边灌边侃大山。腰腹上的肥肉,随着侃出来的笑声颤动。喝多了肚子胀,趿着鞋找个黑影墙根“哗”地撒一泡再说。
膀爷就是不拘小节的人,不拘小节的人在夏天叫“膀爷”。
不拘小节的人的前辈是北京痞子。当年北京小痞子的标准“时装”:麻雀头(就是前脸像小平,后脸赛哪吒),白衬衫(的确良的),大兵裤(上肥下紧,裤脚还要向外挽一寸左右),白袜子掖在裤角外面、脚蹬一双大片儿鞋俗称“懒汉鞋”。如果穿25号的,建议您买26号半的,衬衫的领口敞着,起码要露两个扣子的位置,脖子上现出一条低廉的项链(红绳儿也无不可)。手没事儿的时候不要乱放,一直要揣在裤兜儿里。见到熟人打招呼怎么办?根本就不用挥手,只需要点点头。要注意,真正的痞子点头打招呼不是从上往下点,而是从下往上扬,这叫“扬首示意”,嘴里伴一句“哎”。走路呢,脚不是轻抬轻放,要“搓着地”走,两腿跟木棍似的在地下,把泥地出印来。
不拘小节的人多了,的确也让市政当局头痛。
前几年,北京为放不放养广场鸽,有过一场讨论。其中有人建议:不要搞形式主义,而要多做实事:如果把广场上的鸽子变成许多小痰盂,也许更实用。结果,这一建议遭到反对——广场上不是没有痰盂,对于不拘小节的人来说,你就是每人发个小痰盂挂在他脖子上,恐怕也没用。
坐公汽的时候,人们一拥而上,不去管什么公共秩序,更不管什么礼仪风范的小节。而北京的中巴真可以称为一大奇观,身处人潮熙攘的大街,无论你走到哪里总是有中巴的售票员在车上冲你热情地挥手。而且多半总是站在敞开的车门口,一只脚支撑着整个身躯,一只手拉着车门上方,整个身体像旗帜一般飘扬在外面,或者站在靠近车门的座位上,打开车窗整个上半身探出窗外,那比长臂猿还要敏捷的身段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喜欢停靠在人流量巨大的路口、地下过街通道口或者过街天桥的出口肆意“拉客”。而司机呢?往往凭借其高超的驾驶技艺玩些惊险的花样,靠着你的身边来个紧急刹车,或者出其不意地猛烈超车。对于同行的激烈竞争总是当仁不让,明目张胆地在大马路上进行“拉力赛”,不分出个胜负决不罢休,整个挣钱的过程中好像都在炫耀自己的技术,体验着强烈的表演感。然后,在遥遥领先之后神情非常得意,落后者当然无一例外地骂骂咧咧。
见惯了这些不拘小节的人,禁不住会想自己遵从的那些礼仪规范,是不是落后了,过时了?
北京的“的士”,也透着不拘小节的作风。北京“的哥”热情豪爽,外向健谈,既关心政治,又关注隐私,和客人几乎不需过渡,自来就熟。同时也有点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爱谁是谁。看气度和口气,不像政治局委员,起码也像候补的。
北京“的哥”似乎从来没有统一着装的习惯,穿着随随便便,往好了说,是生活态度潇洒随意,往坏了说,是过于邋遢,更谈不上企业形象。早些年“面的”风行的时候,甚至有“的哥”光着膀子开干。与之相对应的,是出租车里也不太卫生,坐垫儿和椅套儿大多黑不溜秋、脏了吧叽,有些客人外出参加重要活动,穿着比较正式和体面,落座时就不免有些踌躇。北京“的哥”健谈之中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优越感,特别是在外地客人感叹北京的壮观和美丽时,他们往往有点得意忘形。说出话来总是这样:“好看吧?没见过吧?下次还来吧?”
有了这些不拘小节的北京人,北京人的形象可是要大打折扣了。
大雅大俗,可算北京的城市特色。大俗,便是不拘小节人士给城市添的一道彩。
不拘小节人士的另一特征,是做事情丢三落四。
有的北京哥们经常丢东西不是钥匙就是钱包,再要么就是手机。
这类人虽然已不会像前面说的小痞子那样,走路腿像木棍似的在地下,但那姿式总让人觉着别扭,就在这种姿式的别扭中不觉什么东西就丢了。到要用的时候一摸,糟啦,我钱包怎么没了?我没上哪去呀。
大人丢三落四,也传染给了小孩。
办个夏令营,北京孩子也净不拘小节的,丢三落四,习以为常,几乎没有保管物品的习惯,也不觉得可惜。洗个澡,丢下一大堆手表、背心、毛巾等;郊游一次,扔下十多台照相机,甚至1万多元一台的摄像机也忘了拿。主管夏令营的王肃老师说:“我都快成收容队长了。”有的物品找不回来了,也没见几个心疼得抹眼泪的,倒大都一脸坦然:“没事儿,再让我爸我妈买。”那感觉,背后的爸爸妈妈真是一座用之不竭的宝山。
不拘小节人士的第三个特点,是不耐烦干小活,拙于学艺,连修个门锁都不会。
在这类人士家里,不论什么坏了,绝对是请人来修。自个几不会呀。不会你在旁边看,看一次心里不就有数了吗,可他不,他宁可出去侃大山。
有这么一位老兄,正跟人侃山的时候,有人跑来告诉“不行了,山子你们家着火了。”山子不着急,继续侃,旁人替他着急呀,催他:“还不快回去看看?!”他搓着脚丫子坦然:“不急,咱接着侃。”等再侃一段,这老兄方吸着鞋回家,一进胡同见一片残局就火了:“这他妈谁干的?小丫的我不整死他!”脾气发够了,旁人见他不动窝提醒道:“去火堆里收拾一下东西呀。”他不去,不干这活。扭头请俩收破烂的来干。
不怪人送给北京人一个北京大爷的称谓,这些不拘小节人士真的像大爷。
大爷们不干小事,也不屑于计较小节。随随便便,大大咧咧。他们管这叫“大气”。
这些大气的人们在公共场所高声谈笑,旁若无人地高声打手机:“什么?你大声点,啊,股市又涨啦,好,几万元之内你作主,我这会正忙着呢!”
如果上面这些事都不稀奇,全国什么地方都会有,下面这事就不拘小节得太出格了。
好端端的家被旁边楼上没有公德的人扔得满地是大便,这事儿听着不但让人恶心,更令人感到气愤。5月14日,这事儿又发生在许婶的家里。
许婶住在广渠门外垂杨柳北京建筑机械厂内的平房,旁边是该厂10多层高的宿舍楼。5月13日上午10时许,正在屋外歇晌的许婶眼瞅着一袋东西从旁边的高层楼上被抛了出来,在自家门口“炸”开了花。许婶仔细一看,跟几天前一样,又是一袋子大便!自己刚刚打扫完的地面顿时又弄得污秽不堪。
据许婶讲,这种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从住在这间小平房开始,近一年间老出现这种事。不但门外如此,就连自家院里也没能幸免于难。放在院里的生活用品没有一件是干净的,更可气的是,就连吃饭的家伙上也是这样。其他的东西可以不用,可是饭不能不吃呀,但是这饭又怎么能叫人吃得下去呢!尤其是现在天气也热了,引得到处都是蚊子、苍蝇。许婶说:“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不光是许婶一家有这样的遭遇,其他邻居家也是这种情形。楼下的自行车头天晚上还是干干净净的,第二天一早就没法再骑了。其他邻居们都说,从楼上扔下个纸团儿、菜叶什么的这都可以原谅,可是把大便从楼上扔下来,简直太缺德了。
明朝人谢肇在剖析当时的北京人时,说过这么一段话:“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看看扔大便炸弹的行为,不由人不信。这事发生在2002年。
2002年8月份,北京麦当劳店举行促销活动,结果抢起来了。“真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早餐!”早6点半,蔡先生路过楼下的麦当劳右安门外餐厅时,看到有200多人拥在餐厅门前,疯抢88份“免费早点”——1个普通汉堡包加1杯饮料。人群中上百位老头老太和十几个小学生在一起前拥后挤,把维持秩序的经理早早就撞到了一边。据经理讲,这样的“免费早点”在平时的这个时间段只售四五元钱。
早6点,离麦当劳开门还有半小时,就有许多老头老太太过来排队了:“反正平时也出来遛早。”不过,最早的一对老人家竟然三四点钟就来了,还是让人感到吃惊。队伍里开始还有说有笑,等到人数一超过80人,人们就有些绷不住劲儿了,等到队伍一甩尾,在台阶下排起长长的一溜,200多人就全炸了窝:推推搡搡全都往前80名的位置靠,还有不少新来的顾客正从六七名在队旁拦挡的麦当劳员工的缝隙中奋力插队。
其间,麦当劳员工给排队的顾客发了号,按10人一拨顺序进店堂领“免费早点”。据一目击者讲,餐厅的门刚刚开了一条缝,站在门前维持秩序的餐厅经理就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撞了出去。满头白发的“爷爷奶奶”、大块头的“叔叔伯伯”和背书包的小学生互相扒拉着拥进餐厅,不少小孩被挤得大叫起来。一名上班的中年妇女大声叫着:“谁挤了?不都为孩子吗!”
据餐厅的员工讲,袋装的汉堡包和饮料是早已准备好的,所以发送的速度很快,十九分钟就送完了。只是门口没排到前88位的顾客中,不少还在找经理:“都排半天队了,容易吗?”餐厅经理表示“没辙”。
有记者打电话给在北京同时发送“免费早点”的另6家麦当劳餐厅询问,得知哪家店的发送场面都是这样。旁观了这火爆场面的路人感慨说,没想到麦当劳餐厅十几天的轮流促销活动,着实对北京人形成了一次考验。
这件事发生的当天,还有这么一件事:
一大早,租住在朝阳区白家庄民航宿舍的许女士正准备出门,却发现家里的防盗门插销无法拉动,用力推门,门也纹丝不动。许女士明白了:门又被人封上了,这是她半个月以来第三次被人关在家中。有记者赶到许女士家门口,隔着防盗门的纱网,她愁眉苦脸地讲述了半个月来的遭遇。原来,两年前许女士和民航科研中心一职工合租了这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产权属民航总局所有。今年,不常在此居住的邻居想把他租的那一间转租出去,许女士觉得会影响她家的安全和正常生活,曾提出异议,两家为此发生过争执。
7月17日,这位邻居曾往这套单元房的防盗门锁孔里灌过强力胶水,但是效果不佳,许女士只是出得来进不去。8月4日,邻居打电话恐吓许女士,要把防盗门焊上。放下电话后不久,许女士便发现防盗门打不开了,她只好请朋友从外面砸开,结果发现门是被强力胶整个地粘在了铁门框上。昨天,恶作剧再次上演,可许女士的先生正在外地出差,上次帮忙的朋友又不在北京,许女士和女儿急坏了:她今天不但得上班,而且眼部不适急需看病;在东北上大学的女儿该返校了,原本打算去买火车票。
万般无奈的许女士拨打了110求救,可110说:除非有房子产权单位的同意,否则他们无权破门而入;许女士又赶紧打电话找租给她房子的民航科研中心,可有关负责人称他们管不了,让许女士自个儿跟110“协商”去。没辙,许女士只好把先生从外地火速召回,到昨晚7点多,才将防盗门从外边砸开。
现在,许女士家的防盗门已经彻底报废了。换一扇新门容易,然而换一种友善的人际关系却很难,许女士担心的是: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
许女士是北京人尚且如此,外地来京旅游的人则更难说了。咱们来听听一位“长城一日游”的导游的说法。
这位李姓导游介绍,把八达岭长城掉包成八达岭水关长城后,一些旅行社从团费中已经大赚一笔,再加上从购物点拿的回水单(回扣),平均每个游客要被额外赚走80元。
包括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和十三陵水库在内的“长城一日游”,团费开价120元以上。如果是坐游1路去自助旅行,车费要50元,八达岭长城的票价是45元,加上明十三陵的票价,也就是120元。而对旅行社来说,车费已经赚了不少,再加上旅游景点在票价上对团队的优惠,组一个团不存在赔钱的问题。
黑旅行社暂且不说,即使是一些正规的旅行社,也是处心积虑地想多挣点钱。按旅游局规定,各旅行社必须向游客出示旅游景点游览时间标准,并让游客签字认可。李导游提供的某旅行社景点游览时间标准中,八达岭长城被“浓缩”成长城两个字,不知其中奥妙的游客欣欣然大笔一挥,签上名字,然后就被带到了八达岭水关长城。水关长城的票价是12元,团队还能优惠到10元。这一掉包,旅行社从每个游客身上多挣了35元。
李导游所在旅行社只接待广东团和福建团,这两个地方的游客购买力强,旅行社可以按人头拿回扣。如果接待的是购买力较弱地区的游客,就不能按人头拿回扣,而是按实际购买数提成。提成最高的是“太医苑”的药品,“太医后代”与旅行社五五分成。
前几天,李导游接了一个33人的福建团。福建团的游客被带到了水关长城,购物点是玉器店和什刹海附近的另一个“太医苑”。从这两个购物点给旅行社所签回水单上可以看出,无论购物与否,玉器店给旅行社的回扣是每个游客30元,“太医苑”的回扣是每人15元。33人的团队,旅行社从购物点拿到了1480元的回扣。
“让游客开开心心从腰包里掏钱,才是你们导游真正的本事。”李导游所在旅行社的经理常开导她们编故事蒙人。比如带游客去所谓的“太医苑”时,就说《大宅门》是在那儿拍的。去奥体北门一家足底按摩中心时,就说是旅行社送给大家的免费项目。实际上等泡脚后按摩完毕,按摩中心会拿出一袋袋的“泡足粉”让游客购买,一袋“泡足粉”价值不过1元钱,游客要掏280元,每次有几个游客购买,按摩中心和旅行社就实现了“双赢”。
这种事已经让人无法接受了,比这更骇人听闻的还有。
2002年4月2日,万泉新新家园的业主召开了依法维权的新闻发布会。向新闻界透露了他们半年来的调查结果,从而揭开开发商“做鬼”实测面积的惊人黑幕。
业主们指出,开发商在将5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违规销售后,还出租给业主“二次挣钱”。根据海淀区房地局测绘队提供的《商品房销售面积明细表》和《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在测绘队的实测结论中,至少有5837.93平方米的地下室被列入了销售建筑面积,并分摊给每位业主。
而根据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京房地权字(1998)第1285号文件的规定,作为仓库的储藏室和机动车车库所占用的建筑面积不应该计入销售建筑面积分摊给每位业主。开发商在将这部分面积以分摊的方式销售给业主的同时,还把这部分面积单独出租或出售给业主。也就是说,同一块地方,既分摊又出租,赚了两次钱。律师指出,这种行为是典型的欺诈行为,而测绘队的实测结论则是这种欺诈行为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今年3月,业主们从北京市建筑档案馆查阅到万泉新新家园一期竣工图纸。请有关专家精心计算后,发现总建筑面积为54285.90平方米,而实测面积为71512.97平方米,二者相差约1.7万平方米。对这种情况,业主张先生分析,“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开发商在报送政府审批机关的图纸上篡改数据,骗取政府批文;另外是测绘队的实测错误,将面积虚增1.7万平方米”。
业主们委托的律师给算了一笔账,358套商品房,按照当时平均销售单价每平方米7000元人民币计算,平均每位业主在购买万泉一期商品房时,多支付的购房款就达人民币11万多元。如果再加上业主因多增加的分摊面积而额外已经支付和将来要支付的物业管理费和供暖费,业主的实际损失简直难以想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4月3日,业主代表及律师已经向海淀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出申请,要求重新核定分摊范围,依据政府文件重新确定分摊原则;指令测绘队重新测绘和计算每套商品房的销售建筑面积。
既然证据确凿,为何不向法院起诉呢?有关业内人士指出,某些开发商的势力已强大到令不少律师不愿或不敢给中小业主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地步。这位业内人士指出,从普遍发生的面积欺诈事件来看,开发商主要是在公摊面积上做手脚。主要有三种手段:一是增加公共建筑的内容,将原本没有或不该列入的建筑列为公摊范围;二是在不增加公共建筑数量的前提下,将测量面积人为加大;第三是调高公摊系数,在不改变实测公摊面积的前提下,增加每户的公摊面积。事实上,这三种方法都被交叉使用,而这一切,都必须得到土地、房管或测绘部门的认可或配合。
对于业主依法维权,这位业内人士并没有表示出很大兴趣。他说,根据他的统计,目前北京有影响的业主维权状告开发商的诉讼,还没一个胜诉的。从王府公寓到温泉花园,从紫玉山庄到庄胜广场,从嘉德公寓到阳光广场,可以说业主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输了官司。
对于个中原因,他以嘉德公寓为便作了分析。开始业主有证据发现面积不对,便找开发商理论,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房地局测的,和我们无关。业主不信邪,将开发商告上了法院。法庭上,开发商拿出了一大本有房地局测绘部门盖章的报告。业主于是败诉,原因是实测数据是政府部门出具的,开发商不承担责任。于是业主转身去告测绘部门,结果法院审理发现,测绘部门只是受开发商委托,提供技术服务,业主们告测绘部门于法无据,结果仍是驳回。
上边的这些事便,已经不是用不拘小节可以概括的,用一个什么词,这里不便讨论,还是各人去见仁见智吧。这里还是用明人的那句话收尾:盖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京师尽有之。
34.做不了大事的北京人
北京有着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传统给北京人以骄傲,也来得了北京人的步子。
北京人爱说“知足常乐”。这知足常乐使得北京人容易满足。而多少代做为天子脚下臣民的身份,又使他们这种知足,本身包含着自得的意味。
因自得而知足,因知足而自得其乐,这一乐使北京人缺少了闯荡气势,不闯荡自然也就做不了什么大事。
北京人性格中显示较多的顺适。历史上的政治风云与时代的变化,都使人生显得沉重。北京人从中悟出了顺应生活的哲理。“人大不过天去”,“命有八尺别攀一丈”,老辈人代代传下来的教诲,让皇城根下的北京人渐失远祖的锐气。
北京人爱说,俗称“京片子”,说这种行为曾是包括王公贵族和里巷小民在内的北京人的重要消闲方式,以致聊天的北京人和架鸟笼的北京人成为人们审美上的典型北京人姿态,在中国,关于说的盛况,可能只有四川的人聊天(又叫摆龙门阵)堪与北京人的聊天(俗称侃大山)相比,但四川的龙门阵却更多地遭到人们的批评,认为是“盆地意识”的狭隘文化表现,北京人的聊,却很少有人指责。说,表明了北京文化的精致,也表现出它的消闲性质,北京人的雅趣和文化消费心理,与元、明、清和贵族文化的民间化不无关系。因而,人们历来认为北京人是“光说不练”。这种“光说不练”的习气来自满族贵族生活趣味,北京人对其说的文化那份自豪,那份文化优越感,如同法国人对法国话的自豪和优越,“京腔京韵自多情”。但贵族式的生活却使北京人很少有不安分的举动。
他们悠闲、优雅,生意人做的是和气买卖,采取的是古意盎然的经营方式,买主卖主之间一团和气。文化人到古老的琉璃厂去买书,会买的老主顾不是挨着架地搜检、查看,而是“问”,坐在供顾客休息的木椅子上,和卖书的营业人员亲切地聊,有什么书,有没有你要的书,一问便知,假如你急用,而这里没有,营业员还会帮你打电话四处打听,别的书店有没有。要不,就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来了书告诉您。比起外地城市里书店工作人员连书名都叫不出的窘态这里则要更舒适一些,到邃雅斋、海王村、中华、古旧……去买书,简直是一种享受,卖书、卖古籍、卖古董的如此,卖绸布、卖茶和酒的、卖药的,尤其是那些老字号、店铺,都弥漫着宁静悠闲的古旧商业情调。
林语堂说过,在北京的男女老幼说话的声调上,都显而易见的平静与安闲,这证明了北京人文化和生活的舒适与愉快,因为说话的腔调儿,就是全民精神的声音。这是极富国粹派气味的论断,充满着本人的文化优越感。
就是这种平静和安闲,舒适与愉快,使北京人走不出去。或即便走出来了,心里为这平静安闲记挂,也就丧失了做大事的冲力。小有成就了还得回来,知足常乐。
于是,北京人落了这种批评:现在北京城里做大事办大公司的,没一个北京人。
其实这话也不确切,写《北京人在纽约》的曹桂林,曾是中国第一地产品牌的万科的老总王石,全是北京人。他们之所以不在北京占地儿,可能是出于其他的考虑。
但其他的北京人,大部份确实缺乏做大事业的雄心和手面。同中国其他城市人比较,可能只有南京人与其相似。
北京人容易满足,挣个几百万便不干了。不想再把事业做大。
所以,许多以前北京的款爷,如今只够中产水平。
而北京的市民,不能在遍布京城的大公司里,做到老总、付总的职位。只能小打溜的干干。他们没那份儿能力。
用一句话来总结,叫没有进取心。
结果,北京就出现如此现象,最高级的工作和最低级的工作都由外地人来做,太高级的本地人干不了,太低的本地人不惜得做,宁肯待业。
为什么会这样子,这实在是个谜。
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人是沉寂了,落后了。但一当北京人看准了,敢出手的时候,不乏为天下先的勇气,一时千夫所指的“官倒”,北京人处领先地位,出国热,北京人又表现活跃。应该说北京人不乏敢做敢为的勇气,但是,真到要做大事业的时候,找不到北京人的影子了,他们又知足者乐了。
安于享乐,容易知足,这可能是北京人做不大,做不了大事的原因。
几百年来,北京人享受看天子脚下臣民的待遇,新中国建立后,又享受着计划经济的优先供给权,游手好闲惯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渐渐退化了。享受生活质量,不做事业的奴隶,大概成了他们的一种普遍心态。
几年前,许多进京打拼的外地人便普遍认为,北京人爱说不爱做,怕吃苦,爱享乐。这话恐怕一语中的。
怕吃苦,爱享乐,许多北京人只好去当“虫儿”。什么“饭虫儿”“题虫儿”“鸟虫儿”“房虫儿”,不一而足,反心全是人中的“虫儿”,一边玩着一边钻缝子,乐子找了,小钱也挣了,可就是没胆子做大事,还有道理,叫不做金钱的奴隶。北京作家刘一达对这类人有极灵动的描述。
几年前,北京从天桥到永定门大街西侧,是无数毗邻相接的服装商亭,以天坛西门为界划分为北区和南区。北区的商贩大多是北京人,南区的商贩清一色是南方人。
竞争就从这里开始。北京人进的货,常常是二三手的价格。把价码一标,高高一挂,几个摊主凑在一处打牌。他们不怕不好卖,反正家就住在附近,来往方便。说不定哪天捉住一个大头,一件就能卖出几件的价钱。南区的外乡人不敢这样潇洒,他们吃住都要花钱,房租一点儿不便宜。所以见利就走,价格低得多。他们自产自销,城外的村里既是住地又是生产基地,一个小工一夜可以做40条西裤。
北京人发现,不论他们以什么低价出手,南区的外乡人总是比他们便宜。北京人还发现,不管他们从哪个渠道进来俏货,上市只要一两天,外乡人的仿制品必定接踵而至。北京人终于自叹不如人,索性把营业执照出租给外乡人,自己闹个旱涝收完事。于是,外乡人如虎添翼,生意越做越火,人也越来越多。
北京人的许多地盘,就是这样让出去的。
北京人干不了这个,北京人就只能当二地主,收租子。
北京人要干就干个大的,小打溜的没劲。但大的总也不来,等真来了也干不了,因为怕吃苦,没有从小事干起的精神,因而也就缺乏经验的积累。
《北京人在纽约》里边的王启明,恐怕最了解北京人的这种特性,所以,当朋友来投奔时,他将其甩下不管,让对方先多吃点苦再说,而他自己,也因吃了好高鹜远的亏,什么全不懂便去干房地产,结果一败涂地。还是干不了大事。
北京有最好的教育设施,但北京学生考分普遍不高,为什么?还是因为怕吃苦。
现在不吃苦,将来还是做不了最好的工作。
眼高手低,小事不做,因而也没有大事可做。
广州的天河新城和环市高层建筑群有“香港中环”的美誉,实质则是都市“白领粉领灰领和金领”们打拼竞斗的“城市森林”。从一个公司最底薪做起,积累数月的经验马上跳槽到另一公司涨高了薪酬;尔后再积累数月经验又跳至一家薪酬更高的公司……层层递进,永无休止——这是所有城市白领青年人在广州的奋斗轨迹缩影。在广州工作,老板可以不看你的来路、地位、年龄、性别甚至学历,他只看你能否为公司带来效益,这才是你所体现的价值。于是,在广州打拼的所有事业中人或谋生中人,都不必着意于拼外表、拼穿戴、拼气质、拼谈吐、拼心计、拼人际关系、拼三亲六戚……你只需拼出自己的实力、特长,拼出你智慧的“市场”或商业实绩,就等于打拼出了站稳广州做“人上人”的梦想将来。离生活近,有“舒适感”。
北京人不会这么做。他会说:不值。或说:我去干那事?于是,他们会待在家里,等熟人给介绍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干烦了,回家,再等下一份。
有了钱的,玩鸟、玩狗、玩车,就是不想把事玩大。不愿意担那风险。
这类人多了。这类人一多,连带正在做事业的北京人也跟着背了黑锅。
因为这类做事业的北京人,占城市人口比例太小了。
除了这小部份人,还有一个奇怪现象:许多能干大事的人,都不在本地发展。
这个现象不光北京有,其他城市也不少见。
这个现象值得一些“家”们好的研究。
能干大事的大部份跑了,小部份在默默打拼,剩下的让城市落个干不了大事的名声。
这个名声除了广州人,什么上海人、南京人,武汉人、全有。他们那儿能干大事的大部份也跑别处去发展去了,小部分默默打拼的也不出名,可能是不愿出名。
余秋雨所写的《上海人》里,这样讲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
而在上世纪前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结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
余秋雨所说的上海人的情况,比之北京如何?恐怕,北京人在大企业的职位,还比不上上海人。
八十年代末,北京的一位某小姐,从几千名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为深圳麦当劳快餐店的见习经理,月薪1500元,但不久之后,她炒了老板,重返京城。她说“那儿工作太苦太累,人变成了赚钱的机器,不适合我的性格。”
如果说上海人做不成大事是因为没有气概,那么北京人干不了大事是因为缺乏吃苦精神,只想知“足”而乐。
一个是想做要做做不成,另一个则是老说不练,嘴足而心乐。
所以,北京人的市场,前几年全是外地人在练。一步慢就步步慢,等人家都练成了大鳄,北京人反倒落个干不了大事的名声。
看看下面这一段,北京人在一个外地人眼中的形象:
北京人说起来也可怜,上班通勤时间一两个小时是正常的,每天有四五个小时花费在路上,为的仅仅是住在北京,遭的是哪份罪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北京拿高工资的往往还不是北京人!不信随便在哪个高技术企业打听一下,有多少北京本地人在里面,就是在里面也十有八九是打工的。瞧瞧报纸上的房地产广告,我敢说北京的青年人除非从地底下刨出两个北京人头盖骨,否则今生不要指望买上自己的楼房了,更别说买车了。能够赖在父母家已经很不错了!天天上楼下楼乘电梯,物业公司的各种催费通知单让人触目惊心,这个费那个费,我庆幸自己不是北京人!也庆幸不是北京的永久居民!
北京人在这位外地朋友眼中,成了这付模样,惨到家了。
知足常乐的北京大爷,该醒醒了。
北京人爱充大,什么都要大,结果干不了大事。
真正出能人的地方,出了一拨又一拨,北京好赖出过一拨,再不见出了,是不是该找找原因了?
原因可能也确实复杂。
一是挣钱的机会没抓着,那会儿还小,等长大了再想抓,机会已没了,市场已从无序变成有序,再没有大把挣钱的时候了。
再是,该读书的时候没好好读。没想到社会发展这么快,后悔已来不及了。
还有啃老啃惯了,反正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不如在父母家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再就是,手里倒是有俩钱,但干大事远远不够,也不想再冒风险,就在股市上挣俩投机钱拉倒吧。
不知这几条说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