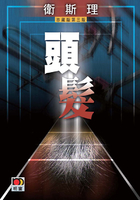有些事情就是那样凑巧。第一次跟李逢春来会馆时见到的"人体宴",那样的宴席,当时只觉得如此的荒诞而令人震憾。这一次,就发生在眼前。
活生生的女子,就在我眼前裸着身,面无表情地躺在榻榻米上。看到这一场面,我的心几乎沸腾。但我已不再是那个没有见过世面、遇事惊慌的女子。我尽量让自己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但心里稍稍流露出来的不安,还是不能逃脱费的眼睛。他低头对我说,"凌落,这只不过一道菜。"
是的,那只不过一道菜。对于身边的男人来说,早就见怪不怪了。
"为什么要如此隆重?"我忍不住问。
"为了钱塘江畔那块地,应该隆重。"
金局长来了。他一走进包厢,仿佛也被眼前的阵势惊吓了一下,他惊愕地说出:"费总你?!"
费立起身,微微一笑,向对面座位一伸手,请金局长入座。
他说:"都是哥们,出来吃饭无非图个尽兴尽意。"
这个包厢不大。我坐在费的身边,对面金局长的身边空出一个位子,费好像早就设计好的。上菜时,他俯在服务生耳边交待了几句。立即有一个女子被带进来,五官清秀,身材单薄,看上去很年轻。她有些羞怯地扫视大家一眼,垂着手站着等人发话。
费让他坐在金局长身边去。她坐过去,身体有点拘谨。我被她那点拘谨和羞怯搅得心里一阵乱,脸莫名地烧。
这于我,多么像嘲弄。多么相似的一段时光,戴着假面回来了!那一刻,我已进入一个非我所控制的莫名其妙的情绪里。我听见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一年前,那个女子就是我,我就是那个女子。还有那个裸着身被当作盛菜工具的女子,我也可能是她,被当成一道菜,一个工具。我的心开始隐隐作痛,开始在自己想象的细节中受刑,在虚构的场景里痛苦得脸奇怪地扭动。
两个男人在谈笑风生。他们谈女人,谈股市,谈怎么玩,怎么痛快,却独独不谈那块地的事。
金局长看上去有点兴奋,他忽然递过酒杯来,要敬我一杯。我勉强站起身来,金局长恭维了一句:"何小姐还是那么漂亮!"
费立即玩笑着说:"凌落今天穿的旗袍可是我送的,千万不可被酒水弄脏了。"
金局长哈哈大笑,"哪敢哪敢!那天酒多了,实在不好意思!"
费又趁机说,"凌落现在已经是费氏的副总经理,希望金局长以后多多关照!"
金局长再次露出吃惊的样子,他将身子挺远一些,一副刮目相看的表情。他拉着身边的女子一起敬我,说了一大堆恭喜我的话。
费心照不宣地温柔地看我一眼,我的心被轻轻撩动了一下,他的温柔缓解了我内心紧绷的神经。仿佛从一个世界掉进了另一个世界。
我回过神来,身边的这个男人让我明白,我已拥有一个被人敬重的身份--费氏的副总。我已在"人上"。我不会再像眼前的女子那样,在"人下",被当作盛菜的工具。
然而,我依然沉静着脸,没有太多的笑意。我笑不出来。我不知道金局长为什么突然一改常态,拼命地恭维我,并不时拥抱他身边的女子,仿佛在见证他那一刻与我们无关的快乐。
事后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费设的局。在这个饭局之前,费告诉金局长,我已认了高副市长做干爹。后来,我听费说,他在请高市长吃饭时,偶尔提起我,并巧妙地说起我飘落于这个城市的身世,又委婉地问高副市长是否愿意认下我这个干女儿。没想到高副市长被费的一席话,激起了男人的怜惜之意,趁着酒兴,当场点头,给了费一个天大的面子。而费为我做的这一切,我却蒙在鼓里,全然不知。费动用他一个男人的计谋,轻而易举地替我铺设好了一条光明大道。
也许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人会正面跟费去争抢一个女人。虽然,费并没有向任何人宣布我是他的女人,他只是慷慨地给了我一个响当当的名衔,然而这样的举动,对这样一个男人来说,已足够心意澄明。
钱塘江边的那块地正式批了下来。费氏收到批文的那天,也正是我进费氏上班的第一天。
那样的一天,如今回忆起来,依然充满血气和热量。在我生命里是一个特殊的场面。费在那天宴请了费氏上下所有的管理人员,同时也请了高副市长和金局长。
费在餐桌上夸我是"小福星"。我一来,福就到。高副市长在口头上当众认下了我这个干女儿。我承认,那一刻我的虚荣犹如涨起的潮水,涌满整个心房。有一种迷醉在我体内激荡。原来,站在"人上",沐着众人投射过来的充满羡慕的目光,就像一服催眠药,让我晕眩。我的双眼灌满色彩。那是一个色彩纷呈的世界,是我从未曾涉足过的。
我狠狠地掐一下自己。这多像一个梦。那段时间,我总是做梦,总是从这个梦又到另一个梦,我已弄不明白,我是不是在梦中?
一阵剧烈的掐痛唤醒我,我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身边的男人,在看着我爽朗豪放地笑。
有记者采访,"能不能请费董事长透露一下,那块地什么时候开始招标?"
费回答说,"会立即请人设计图纸,等图纸一出来便进行招标。"
"这个楼盘将以什么命名?"
"梦江南。"
"请问那块地到底会被打造成什么样的楼盘?"
费把目光投向我,凝视着我身上的旗袍。那件旗袍是他亲手挑选的,深绿绸缎的面料,有暗红的梅花图案,镶着闪亮的金丝线。他微笑着反问记者:
"你觉得何小姐身上的旗袍怎样?"
记者怔住,不知费的用意何在?这完全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驴嘴。我也不明所以,脸微微热,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也都在屏声凝气地静候着答案。
"费氏会把它精心打造成精致、优雅、风姿绰约,令人望一眼就难以舍弃的高档次公寓楼。就如穿在何小姐身上的旗袍一样,我要让购买'梦江南'公寓楼的人,都能像何小姐身上的旗袍一样优雅地生活。"
那是怎样撩动人心的一刻!我在一片掌声里差点落泪。空气里荡着透骨的香味。我知道我正被一个男人重视。因为他的重视,我已成了众人瞩目的对象。
第二天的城市早报上,头版头条刊出了这样一篇文章:《费氏将着力打造"梦江南",让居民像旗袍一样优雅地生活》。
我身穿旗袍的照片,赫然出现在标题下面最醒目的位置上。文章被添油加醋大大渲染了一番。
我居然成了这个城市的焦点人物!这令我大为吃惊。当我拿着这份报纸走进费的办公室时,他也正在看。
见到我,他高兴地说,"我说你是小福星吧,你一来,凡事皆顺!这样的软广告,比花上一大笔钱去做的广告效果要好出无数倍。"
我心里明白,他的恭维讨好就像一个大人对一个孩子。其实我根本没有对费氏作出过一丝一毫之力,所有的事,皆操纵在他自己手里。他就像拥有一只神来之手,总能借助一些看似无形的力量,运他自己的功,达成愿望。
我开始上班。我并没有房地产方面的专业知识。不知从何做起。费鼓励我,说没有人天生就懂。他让我学会去管理,去管好人就行了。至于专业方面,自然有技术人员会负责去做。
我拥有单独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有现成的电脑。窗口朝南。早上九点后,会有一抹阳光温暖地照进来,办公桌边的那株绿萝,叶子会变得光滑透亮,有细微的尘埃在阳光里整齐地舞蹈。
这样的时光太令人欢快,轻松,然而,我的心情却与这样的时光极不吻合,我总是会陷入恍惚的境地,不知自己身在何地。不过,这没关系。我有足够的耐心坐下去,从上午到中午,又从中午到下午,我不想计算时间,这段时间与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区别。我甚至不去想,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只想静静坐着,享受那一抹阳光的温暖,享受从未享受过的这份待遇。
公司上班的人,一律身着职业装,唯有我,依然一身旗袍,配各种风格不同的披肩。那是费专门给我的待遇。
他说,"你是个生来就适合穿旗袍的女子,你可以不用穿职业装上班,而且,我也喜欢看你穿旗袍的样子。"言语间毫不掩饰他对我的那份纵容和专宠。
开始的时候,我也尝试过穿职业装,但总觉得不习惯。有一次黄晓晓曾对我开过一句玩笑,她说,"何小姐你就别再鱼目混珠了!你天生就是个穿旗袍的料,还是穿回你的旗袍吧。"
那句玩笑话,我到后来才知道,她是别有用意。黄晓晓是费的秘书,那天费接过她手中的电话,知道是我约了他,一句话便让她去通知下面的人把会议推迟,这件事她记忆犹新。她说费总从不曾这样过。
每天早上,她会送一杯泡好的龙井茶走进费的办公室,然后顺路走进我的办公室里来问我一声,"何小姐要咖啡还是茶?"
我总是对她说,我自己来。不知为什么,每次与她对话,总有些说不上来的轻微的压迫感,但又说不清原因。她的声音极细极柔,但没有温度。虽然她说话时脸带微笑,声音也是凉的。
她在费氏呆了两年多,时间不算长,但却知道很多事。一来她是费总身边的人,二来跟她爱说话有关。
那天她来我办公室,手里端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每次当她端着咖啡杯过来坐,我就知道她又揣着一肚子话过来。她坐在我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脸带微笑。她笑的时候眼睛更细长,稍稍有点媚,有点讨好人的意思。我心底里不太愿意多跟她说话,但我不愿得罪人,想着多了解些情况对我总有好处。
晓晓问我,"喜不喜欢这间办公室?"
我说,"喜欢。"
她环顾一下四周,说,"这间办公室空了好久了。据说以前也住过一个漂亮的女人,模特出身,是公司招进来专搞外交的。你知道,我们暗地里怎么称呼那个女的吗?"
我摇头,"我怎么会知道?"
晓晓诡秘地靠近我,轻而狠地吐出"肉弹"两个字。
我莫名地脸红心跳,不知她什么意思。
晓晓两片薄薄的嘴唇像刀片,她说,"公司好比武器,在必要的时候,钱和女人就是子弹,没有子弹,武器再亮也只是空壳,强大不起来。"
室内的空气有些闷,压迫着人的心脏。我那天穿的旗袍太紧身,背上渗出些汗意,我挺了挺身子,让自己坐正一些。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出来自己的声音比晓晓的声音更冷,我怪自己的直觉来得太慢。
晓晓眉头一挑,啜一口咖啡,她把嗓音压下去一些,装出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来,"你的话为什么问得这么硬邦邦?"
"我硬邦邦吗?"我淡淡地说。
"其实你不必这样,你跟她们不一样。"晓晓跟我解释。
"你是被费总重用的人。"她把重音落在"重用"二字上。她说,"你现在又是高副市长的人,是他的干女儿!"
"那又怎样?!"我一下跳起来,"我跟高市长一清二白!"
"你跟高市长当然清白,那是因为费总塞过他一只信封,那只信封对一个男人的吸引力足以压过你的美貌。董事长没把你当'肉弹'打出去,留你在费氏,难道你不知道?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自己想'用'你!"
我倒抽一口冷气,奇怪于她说话竟然如此放肆!这个女人她到底还知道多少?但我不想再听。我大声命令她出去!
我几乎不这样对待别人,尤其进费氏以来,我曾对自己规定了几条原则:不粗暴,不生气,不愤怒,不无礼,包括要轻言细语,温文尔雅,绝对淑女样。而对这个黄晓晓,我的原则一下子都跑得无影无踪。我愤然赶走她。
黄晓晓喝得分明是咖啡,却像喝进太多烈酒那样,醉着人,扰乱了她的心智。不知哪根筋搭错,她把剩下的咖啡忽然便摔向我。
我站着没有动,任咖啡的暖香伤了我一身。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办公室门外有人闻声而来,他们惊讶地目睹了这个场面,有人试着进来劝问。晓晓尖细的声音在空中飘荡:"狐狸精!"
在人群中,我反而镇静下来,内心有一种奇异的空荡。自始至终,我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直至费百强分开人群,从门外径直闯进来。
我无声地望向他,心里忽地聚集起一种委屈。他朝人群看了看,人们立即识趣地退出门外,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他关上办公室的门,看了我一眼,转头问晓晓:"怎么回事?"
晓晓头一仰,眼睛里充满血,"你开除我好了!"
"你以为我不敢吗?"
晓晓不气馁,仍硬声硬气地说:"反正我也这样了!"
"你怎样了?"
"你忘记两年前那个晚上了吗?你要了我,你又不要我!"晓晓大着声说,她的身体轻微地颤抖,牙齿咬得咯咯响。
"可那天晚上你明明知道我喝醉了,身边是谁我都不知道,第二天你告诉我这件事,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对你做过什么!"
"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晓晓眼都红了。
"就算我相信,我已向你道过歉,你还要我怎样?"
"但是这两年多,我一直为你守着,你都看在眼里!"
"我们不可能......"费的声音低而沉,充满果断。
......
我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对话里,知道两年前,费在醉酒后曾对晓晓犯过错,但晓晓却一直等着费去爱她。一定是我的闯入,让晓晓陷入无望,意识到她的等待终成泡影。
晓晓说,"我就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开除我好了!"话虽这样说着,但语气似乎有些软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