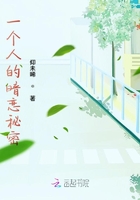过后将此事说于笺南听,他微微笑了笑,颊边展出了两个浅浅的酒窝。
“臣等大漠儿女不会这些,但来了上京那么些年,学会了汉人的对弈,对牌,其余的会慢慢学会陪公主玩。”
想了那么些功夫,笺南已捧着一碟子蟹粉酥而来,未穿袄子的他落了一身的白雪,但却一直用宽而大的掌罩着点心。
我赶忙撑着油纸花伞出去迎,气急败坏道:“管内务的狗奴不会看眼,竟连我身边的人都敢那么欺负不给袄子穿!”
笺南并未说什么,我掸了掸他肩头和纱帽上落的清雪,触及皆是一片冰凉,凉到了心里。
“这么着,你拿着父皇前几日新赏我的长毛黑兔袄穿,左右那件式样我也不甚喜爱,空闲着也是空闲。”
若是不作这些说辞,笺南恐怕会弓着腰板连道:“公主不可,公主不可。”
此刻他退了几步,拱了拱手,脸上带着笑意道:“臣多谢公主赏赐。”
我息了油纸花伞,笺南接过放到伞台上,我拢了拢衣袖,见他裸露的双手冻的发紫,道:“来金炉边烤烤火,赏你块酥饼吃。”
他应声而来,坐到我身旁的蒲团上,带着一身的凉气,我烘了那么久的火都发觉那么一吹颊边冷。
“现年冬日冷,往常这时候我已换了那件薄而靓丽的梅袄了,现下却要穿着那么一行头,活像只笨熊。”
确是这样,湖面的冰凝的未化,甚还有续凝的迹象,公主府里每日都会有侍人扫积雪,但似是扫不完样,落了一堆又一堆,梅枝也断了一根又一根。
笺南小口吃着酥饼,用袖子轻揩揩薄唇,道:“大漠的冬寒冷而又漫长,人群都穿戴着黑熊或是白狼毛皮,公主定是不喜爱那里的。”
“但臣却时常挂念着家乡,那里的朦胧钩月、葡萄成酿、筚篥脆鸣、五色琉璃……臣想给公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