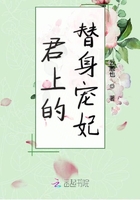十五年又十一个月的人生路,她未曾有一次想过自己会受到如此奇怪而莫须有的伤害,或许因为对方的无知或恶意揣度的习惯,或许因为她内心的不安和脆弱,此时面对母亲骤然的死、面对眼前瞬间翻天覆地的一切,还有那个看似她内心妥协于现实处境才接受下来的“交易”,她心底真正的想法确实有几分像他说的“讹诈”。
是啊,如果现在她还有另一个选择,或许此刻她早已打包行李远离有关母亲死亡的一切一切了,包括林刻、杜安妹还有……林子瀚,而不是像这样身不由己默认让自己留在被救者的世界里,像个假清高的乞丐自以为活得如从前一样有尊严和骄傲,可最最实际的仍然逃脱不了一个“钱”字,更何况她现在真的是因为母亲的死才有资格和被救者谈起“钱”,这不禁让她一时间倍感羞愧无地自容了。
毕竟如她想象的,要完完全全保持住母亲救人的纯粹与高尚之名,此刻她就应该早已从被救者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不像这样自欺欺人留下,可……
是啊,少年……少年的她又有什么力量,能够对抗突然失去母亲后那令自己无能为力的现实世界?或者,她就应该固执让迟早该崩溃的就此崩溃下去,在那样深重的苦难里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自己的路,可未来呢?未来她又该如何对母亲寄托在自己身上的那个名校梦有所交代?
想到这里,眼泪缓缓涌起,她仍固执没有流下,默然靠墙坐在床角抬头看向那空无一物的天花板,心底无限挣扎与哀痛无人可诉,渐渐感到全身僵硬且冰冷,忍不住低下头蜷缩起身体,暗自开始祈祷这煎熬难挨的时间能够尽快过去,再快一些。
“叮……叮……”桌上的手机仍在不时震动,另一边云珈继续发来小子的照片,等她好不容易缓过来伸手拿起,低头看见小子被云珈抱在怀里,此时的模样已然焕然一新,不禁微微怔住了。
小子,原来早已不是她曾以为的那副普通模样,一夜间变得那么干净而温和了,看上去像极了优雅礼貌衣着整洁又爱梳头的年轻绅士,竟然有模有样直立站在镜头前夹住前腿朝来人作揖,不知不觉让她心情渐渐放松了下来。
终于,她默然轻叹一口气,暂时放下心底那些解不出的偏执,低着头斟酌了许久,才拿起手机给云珈发去短信:云姨,你好。安管家跟我说,在他不在这段时间,我如果有事情可以直接找你商量。嗯……所以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可不可以让我先回一趟我家,因为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我想自己回去拿。
原来,她以为自己又要等上好久才能听到回音,就准备暂时将手机放回桌上,可还没等她来得及放下,手心已经感觉到手机的震动,不禁暗自惊讶低头看去,只见此时屏幕上清清楚楚写着:“好的,绪花同学。今晚云姨就让司机师傅带上钥匙送你回去。”
就这样,她不由如释重负地彻底松了一口气,缓缓将手机放下了,起身朝衣帽间走去。
直到夕阳西下夜幕缓缓降临,年轻司机如期出现在房门外,她二话不说转身拉着早已准备的旧行李箱走出门外,就一路沉默跟着司机坐车回到了那一片熟悉又喧闹的长街。
那一刻,她拉着行李箱默然站在川流不息的拥挤人潮里,手中真正握住了那一串新钥匙,竟突然莫名其妙对从前未曾那么看重的钱财猛然长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奢望来,甚至开始奇怪想象着如果她以后能够拥有足够的钱财,不用很久就在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她能够拥有足够可以打动房东的钱财,或许她就可以将自己和母亲那么多年漂泊异乡勉强寄身的这个小窝直接买下来,不为什么物质上的拥有,只为做她这一辈子的精神寄托。
是啊,母亲离开了,那样……离开了,按照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运行规则,最后或许连她都不得不忘记了母亲的存在,就仿佛她从未来过,生活依然平凡琐碎如同未曾惊起一丝波澜的水面,最终悄无声息将过去时间里那些沉痛的、撕裂的、哀敏的、横行的……从曾经施予的每一颗人心里一一收回了,只留下那些空洞而不断变换着的世间躯体和心壳在注定消逝的凋零与枯萎的尾音里迎接刹那的毁灭,那么到底她和母亲这一生里曾经发生过的痛彻心扉又挣扎不开的诀别、争执还有控诉和指责,还有痛苦、受伤……又能算得上这必将逝去的一切里的什么呢?
因为更在乎、更深爱、更偏执或更疯狂,直到相似又不同如她和母亲终有一天在时间尽头重逢了,又会不会对这样作茧自缚的天性感到无比后悔呢?毕竟对比这终将逝去的一切,那些所有的刺痛和分歧其实都显得矫揉造作又卑微不堪,但只要她能真正对母亲少一些在乎、关心或期待,是不是她和母亲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是不是就能少许多的伤痛,更多一些温情?
时间,依旧是……时间,最经不起反复推敲和假设,所以从来只给每个人一次机会去经历那一切,又毫不留情给所有人预留下注定死亡和毁灭的结局,说起来是那样的残忍而极致,像一面放大镜平摊在每个人或长或短的每一种经历上,总将绝望照得过分清楚、虚妄映得无比魔幻、贪婪裸露得那么真实……可人心尽管有他偏执且坚信到底的力量,依然会被自己深陷其中无力自拔的种种境遇欺骗到丢盔弃甲、举手投降,然后莫名其妙溺在被动放弃的自我申辩里假装挣扎不出,其实从头到尾只是想给自己的“不想努力”找到一个值得他人同情的理由,好让那一副套着人皮又脆弱不安的人心找到一件尚堪入目的假衣,自称为人的外衣?
可“人”到底又真正是什么呢?
许多人说他们多变如瞬息风向难以捉摸,许多人又说他们坚信像极从傻子变成疯子的逆臣贼子冥顽不灵,不论以何种面貌出现或度过这一生,答案真的就那么重要?或轻浮如尘,或凝重如山,谁又能轻易说别人好不容易走来的人生就不是人生?但或许差别只在于,到头来他们真的是做了陨灭于美好想象的一缕灰,还是做了放弃美好想象的一抹尘,毕竟世间并没有人能够推翻自己未曾坚信的另一种结局就真的不会实现。
就这样,她独自顺着原路走回到公寓门外,进了门、开了灯,转身看见屋子里被弄得乱七八糟的一切,募地感到一阵强烈的痛苦和难过,就强忍着泪立刻放下行李箱重新将屋子各处收拾好,然后找来一些容易搭配的秋冬衣装到箱子里,才终于有时间停下动作安静坐到那张旧沙发上稍事休息。
灯,依旧昏黄如雾。
屋,依旧静若坟墓。
那仿佛走过无数个日夜了的一切又一次安静展开在她眼前了,只是时间里母亲的身影依旧清晰而熟悉,却莫名得渐渐没了温度,任凭她如何回想都再想不起母亲曾经手掌间的温度了,仅仅只是一天一夜的时间过去,她竟突然变得那么的健忘了,不觉心底被什么东西狠狠穿出一个洞来,瞬间让她麻木也沉默了。
时间,是不是以后都会像这样,莫名其妙就从她手里悄然夺去了母亲留下的无数个瞬间和回忆了,她就会像此刻感到如此无可救药又无能为力了?
终于,她默然冷笑了,满眼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