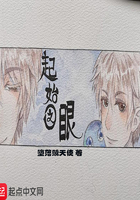萧灼穿越沙漠,渡过黄河,一路西行。兴庆府的城郭掩映在蓝天绿荫中,浮现在眼前,如梦如幻。她仰望清河门上方的楼台,扯下面巾,取出令牌挂在腰间,难以自禁的笑容涌上脸庞。
那匹乌骓马像是感应到主人急切的归心,载着萧灼穿过喧嚣的街坊,直奔内宫而去。
萧灼停在宫墙边的马厩,挑了捆鲜嫩的草料放入槽中,将坐骑周身上下仔细洗刷了一番。她见那匹马已不似前些日子那般神采飞扬,原本乌黑油亮的鬃毛也变得暗淡无光,想到自己这几日的艰难,不禁起了同病相怜之心。萧灼唤来管马的小吏,塞了锭银子在他手中,叮嘱他好生照料,便转身大步走进宫门。
一名叫做忆竹的宫女提着篮子,从斑驳的树影中走过。她见了萧灼,瞪大眼睛问道:“萧侍卫,你可算回来了,这是随军队打仗去了吗?”
萧灼心中一阵苦笑。这些天她日晒风吹,以尘洗面,想必模样已是不堪入目。若是皇后见了自己这副狼狈相,少不了又是一番责怪怜惜。她将手指凑近嘴唇,低声对忆竹道:“莫要声张,惊动了皇后殿下!我稍后便进殿禀报。”
萧灼弓腰溜进后院打了水,回到东侧耳房。她脱去黑袍,卸下软甲。肩头的箭伤倒是无甚大碍,只留了不深不浅的一处凹陷,血渍已凝固发黑。只是她连日骑马奔波,肌肤不知磨破了多少回。那条乌绢长裈密密地渗满血污,早粘在了腿上。萧灼只得咬紧牙关,忍痛将裈子撕做一条条揭下。
骄阳透过窗格,洒进片片耀眼的白光。清凉的水流滑过健壮的身躯,荡去污浊,将点点刺痛撒在伤口上。萧灼阖上眼,沉浸在来之不易的宁静中,无尽的思绪也悄然而至。
两年前,辽国选派兴平公主远嫁夏王李元昊。萧灼便做了公主的贴身侍卫,随她来到兴庆府。只是这位“公主”既非皇女,也非宗室。假冒公主的,正是颜翰任的姐姐颜予清。
送亲队伍刚到夏国时,李元昊亲自出城二十里迎接,场面甚是隆重,往后一段时日,两人也颇为恩爱。哪知不到一年,李元昊渐渐怀疑起她的身份,对她的宠爱一日日冷落下来。
萧灼听过昭君出塞的典故,本想两国和亲,不过是场光冕堂皇的交易,无人会深究公主出身。她见宫中光景逐渐萧瑟,心里焦急,几次三番要替皇后出头。颜予清本是个性情恬淡的人,对权宠并不放在心上,每次都挡了下来。这般日子虽是平淡,两人倒也落得悠哉。直到十几日前,一场变故让萧灼实在忍无可忍。
那夜李元昊醉醺醺冲进蓬莱殿,又将侍女都轰了出去。萧灼在耳房听得动静,隐隐觉得不对。他前脚离去,萧灼后脚便赶进殿内,只见皇后发髻散乱,凤眼含泪,斜歪在座榻上。
萧灼心里一惊,上前握住她双手,急切问道:“姐姐,这是怎么了?”颜予清双眉紧蹙,摇摇头道:“只是喝醉了,过来胡闹,休要去理他。”萧灼见她眼光闪烁,神情中透着痛楚,心中不免生疑。她忽地伸手,抓住颜予清衣襟,将那身真红罗衫拉下半尺。
白皙光洁的肩背上,凸起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他竟敢这般对你?”萧灼的声音不禁颤抖起来。
颜予清将萧灼搂在怀中,轻轻抚着她的头发,柔声道:“陛下这几日心情焦躁,忍一忍便过去了。毕竟是咱们失信在前,也不能全怨他。”
萧灼顿足道:“都怪我害苦了姐姐!可他究竟因何事拿你出气?”
“方才我见他狂躁,也设法套了些话出来:只因前几天从吐蕃来了支商队,进贡了不少财货。太子与那头领相交甚欢,便带他去高台寺拜谒。哪知商队离去后,供在塔中的国宝竟不翼而飞。陛下盛怒,下令将太子囚禁,又把当晚值夜的士卒都割去了鼻子。”
所谓国宝,是一枚佛指舍利。萧灼听闻李元昊笃信佛教,更是将那枚舍利当做庇佑大夏国运的无上圣物。她思索了片刻,便对皇后说:“他若派兵追赶,又恐那些吐蕃人听得动静,将舍利或毁或弃,因此左右为难,是不是?”
颜予清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萧灼的鼻尖,微微一笑:“灼儿到底是长大了,事情看得愈发周全。他投鼠忌器,正是有此顾虑。”
萧灼抬起头,瞪圆杏眼,一字一字道:“我立刻去求见陛下,请命夺回舍利。”
颜予清沉吟半晌,叹了口气,缓缓道:“也是个法子。”便教了萧灼一些应对的话。末了,她看向萧灼,眼中满是爱怜与不舍。
“切记,拿到出宫的腰牌后,勿去追赶那支商队,火速北上去辽国,再也不要回来。”
萧灼大惊失色:“我怎能自己逃走,将姐姐一人丢在这虎穴狼窝?”
“我名分上仍是辽国公主、夏国皇后,不会有性命之忧。”颜予清抓住她衣袖,“方才我所说的,你须得照做。”
萧灼的双眼模糊起来。她勉强点点头,转身走出大殿。
“朕酒后失言,与皇后发生了些许口角,改日便亲自去看望她。”李元昊的酒看来已是醒了。他端坐在紫宸殿内的髹金木椅上,语气中透着几分和蔼与懊悔。
“呸!口角?”萧灼俯首站立,眼睛直直盯着面前的金砖,心里早把他骂了百遍。“臣前来并非为了此事。”待他说完,萧灼抬头应答,“下官愿为陛下分忧,夺回那枚佛指舍利。”
“你?”李元昊显然吃了一惊。他细细打量眼前这名高大结实的女侍卫,“你要带多少人马?”
“孤身前往即可,以免打草惊蛇。事不宜迟,只要陛下恩准,下官即刻便动身。”
李元昊想不到这个居于深宫的女官竟有如此胆识,傲岸的目光中已闪出些许期待。他发问道:“那商队中都是吐蕃武士,悍勇善战,你有几成胜算?”
萧灼与他对视,昂然回话:“敌众我寡,首当智取。不能智取则力战,力战不得则舍命。又何必计较有几成胜算!”
铿锵的话音犹在房中萦绕,李元昊已抚须赞叹:“可惜啊,可惜!你若是个男子,定可成我麾下骁将,征讨四方。你舍身赴险,又有何所图?”
“只图日后陛下能善待皇后,别无他求!”
李元昊微微颔首,肃然道:“难得你一片忠心。事关国脉,只可成功,万不能失手。你若能取回国宝,我定会加倍恩宠皇后。”
萧灼领了腰牌手谕,跨上乌骓马,挑了兵器防具,又用骑兵黑袍将自己裹个严实。临行时,她特意绕至蓬莱殿前,深深望向舒缓宽阔的飞檐。她想要进殿辞别皇后,却终究没能鼓起勇气。
各军司都已接到御旨监视过往商旅。萧灼一路询问,不久便寻得商队踪迹。她远远跟随,一面耗其锐气,一面仔细观察:那头领一见自己逼近,便不自觉地轻摸前襟,想来舍利必定藏他身上。
余下的便是算准时辰,趁夜在树林前一击得手。
无意间掉落的那封信,头领似乎看得比舍利还重要,她便顺手收入囊中。自己不识汉字,一路不住好奇信上究竟写了些什么。或许是上天与自己开了个玩笑,竟让颜予清的弟弟独坐在沙漠中。
她想起自己一时疏忽,竟上了他的当,心中仍不免又好气又好笑。那个清秀的年轻人眼中射出飞蛾扑火般的光芒,与自己何其相似?与他同行,荒漠中孤苦伶仃的旅途也变得温暖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