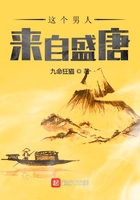逐云阁被血红的灯火模糊了轮廓,打这里望去,如一副刚摘下的内脏浸在漆黑的墨汁里。每到夜晚,这座宏伟的楼阁便成了夏国的中心,只因其中高坐着那位生杀予夺的雄主。
那楼好似有无边的魔力,勾着李宁令哥的目光。他死死盯了半晌才垂下眼帘,默默关严了窗扇,坐回桌前。没藏讹庞孤身侍立在旁,见他转身,忙上前斟了杯酒,低声劝道:“殿下再不决断,只怕要追悔莫及!”
这位中书侍郎今晚罩了件褐麻斗篷,乍看上去像个杂役。他白胖的脸上不见了平日里的和煦,神情凝重而恳切。李宁令哥将酒樽举到唇边微呡一口,抬头望向他双眸。没藏讹庞的眼神让他有些不自在:深邃的光芒从眼窝射出,仿佛在将自己的衣物一件件剥去。父亲的眼睛便是这般,那个叫做普布的吐蕃商人也并无二致。
普布是第一个找上自己的人。他明为商贾,暗地为吐蕃赞普效力,一面探听夏国虚实,一面与宋国暗通款曲。此人看似豪爽粗犷,实则心机深远。两年前,他便以共拓商路、寻求荫护为名,在东宫上下打点,与自己逐渐相熟起来。去年夏天,普布又带了金银、象牙、珍珠、藏红花、木香、牛黄、水獭皮等财货入宫觐见。二人叙话半日,时至傍晚,便在殿内设席共饮。待李宁令哥有了几分醉意,普布起身携了一名窈窕女子入内,施礼道:“这歌女是在下从贺兰山麓寻得,虽不比宫中佳丽,倒也有些姿色,特献与殿下解闷。”
李宁令哥懒懒望去,天灵盖上却似猛地挨了一棍:这女子身形容貌竟与没移氏有六七成相似,烛影之下,恍若爱妃重回身边,望着自己嫣然一笑。这笑容恰似一柄利刃,毫不留情地将未曾愈合的伤处割开。刹那间,思念与无奈、愤恨与不甘一齐喷溅而出。他摔下酒杯吼道:“我要这俗物做什么?”
普布立时面露惶恐,连忙挥手将歌女撵了出去,叩首道:“在下浅薄粗鲁,不知太子殿下不近女色,该罚,该罚!”李宁令哥向后仰去,阖眼长叹。自己虽贵为太子,却被禁锢得极严,身边一无党羽,二无挚友,自没移氏被掳走,便一个交心的人也没有。他沉默半晌,终究难忍,便借着酒力将李元昊如何强占了自己妃子一事,连同心中愤懑尽数吐露而出。
“我还想着殿下为何憔悴了许多。若换作我这莽夫摊上如此遭遇,怕是一日都忍不得。”普布听罢嗟叹不已,“你可曾尽力争取过?”
“他是大夏皇帝。苍生万物,哪一样不是他要拿便拿?我想见他一面尚且不易,又如何去争?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巴望他早日暴毙。”
“他毕竟是你父亲,这话怎可乱说?”
李宁令哥顿觉失望,自嘲道:“好,不说也罢。你们都是忠臣孝子,莫要被这些话浊了双耳。”
“殿下若决意为心上人不惜一切,在下倒情愿效劳。”普布沉吟片刻,望了过来。
“你难不成能替我杀了他?”
“在下一个小小商人,哪有这般本领?不过如借了外力,此事也并非不能办到。”普布凑上前来,一步步道出了联合两国攻杀李元昊的计划。李宁令哥怎会不知他是想要借助自己复兴吐蕃,但只要能再与她相聚,弑父也好,国破也罢,又有何妨?即便普布转身便向李元昊告密,慨然赴死也好过行尸走肉般活着。热血贲张之际,他一挥而就,在绸布上写下联宋伐夏的书信,盖了印递与普布,这矮瘦汉子却接过来在烛火上烧了。
“请恕草民无礼。”普布深鞠一躬,不慌不忙从怀中取出数张薄纸,几近透明,“一路东去汴梁,理应不会有什么差池,不过顾及太子殿下安危,总是谨慎些好。这纸张易燃易化,用作密信最为合适。”
待李宁令哥重写了信笺,普布又缓缓道:“殿下手迹,宋国朝堂无人熟识,最好再有信物交与在下,方能令人信服。”他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瞄在李宁令哥腰间。李宁令哥立时会意,他微微一笑,手指掠过玉带,轻按在佩刀上。这口刀,是自己被册立为太子那日父亲所赠,平日从不离身,单是抚摸着雕纹精美的包金刀鞘,便足以勾起无尽的喜怒悲欢。
“请随我来。”李宁令哥起身,领着普布快马奔至高台寺,取了舍利回宫。
“从我祖父时起,这物什便被视为国宝供奉。如今交与你带去,可够份量?”李宁令哥将舍利捏在两指间,得意一笑。普布却紧皱眉头:“我原本不知这舍利如此贵重,万一败露,殿下要如何自保?”
“你放心,越是贵重,越是无虞。这舍利一直藏在塔顶,即便每年开春祭拜天地时,也是隔着铁匣,极少示人。”
普布盯着面前的残羹思索片刻,抬头道:“还请借宝刀一用。”
“说到底,阁下还是嫌烫手。你若无胆量,随我将它再放回去便是!”李宁令哥紧盯普布,哈哈大笑起来。
“我绝非此意,殿下稍后便知!”普布在桌上取了根羊骨,接过自己佩刀剁下,拈起碎骨擦拭干净。比对舍利,这骨筒长短宽窄颇为相似,乍看之下,难以辨别。他从怀中取出一只小盒,将假舍利收好:“若事有不利,或许可凭它搏得一线生机。”
“那枚真的你要如何带走?”李宁令哥有些好奇起来。
“挑一匹骆驼,在驼峰上划下小口藏入,再以细线缝好,断无人能察觉。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晓,即便那帮随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也一个字不会得知。”
好个心如细丝的商人,早早便留了后手!就算商队被截,他只需毁了书信,那舍利便烂在骆驼身上,绝无对证。好在自己也不落下风。带普布同取舍利,一来让他亲眼见识国宝的排场;二来若被人发觉,他也脱不了干系,到时只作不知,将罪责尽数推在他身上,二人互有牵制,方能齐心协力。
时至今日,李宁令哥回想起来,仍是后怕,他早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有一点,当初激愤之时未曾想到:若兴庆府沦陷,宋国定要赶尽杀绝,怎能容自己偏安一隅?好在此事就此再无消息,自己性命得保,太子之位竟也未被剥夺。日渐暴虐的父亲是当真发了善心,还是想要将自己放在掌心里慢慢戏弄,实在难以琢磨。
自己究竟有没有胆量去直面他?李宁令哥不自禁地轻抚佩刀柄端的宝石。“我李宁令哥,夏国太子,今夜便要夺回本该属于我的一切。”他手指暗暗加力,强扼越来越快的心跳。
没藏讹庞依然静静伫立在对面,眼中的光芒却已渐渐黯淡下来。李宁令哥并不着急答复,此人比自己更期待这场风暴的来临。约莫过了一刻,没藏讹庞终于按耐不住,低声叹道:“我深知殿下顾及人伦,但大夏已陷危难之中。今早接到战报,我军已突破宋国防线,不日便有一番恶战。陛下现今一句真话也听不得,动辄便要将进言之人挖眼削鼻。他只顾调军征伐,哪知国内已是十户五空,若遭宋军反噬,又怎能自守?”
“这套说辞,我早已听得腻了。”李宁令哥哼了一声,“我想杀他,是为了心爱的女子;而你真心是为了黎民社稷,还是满足一己权欲?有人传言,你暗中派人下药毒死了皇后,只为扶你妹妹上位,可有此事?”
没藏讹庞挺直身板,大腹将斗篷顶得滚圆,慷慨道:“这些胡言,太子殿下也信?不错,我确实渴求权力地位,却也不会蠢到因贪图小利而害死皇后。若得罪辽国,引来战火将夏国覆灭,那时我还能得到什么?”
这番回答倒是诚恳,让李宁令哥颇为满意。没藏讹庞第一次找上门密谋之时,自己便极为欣赏他的沉稳老练。事实上,除了他还有谁值得信任?自己原本寄予厚望的东宫侍卫们如今看来不过是一帮草包罢了。
李宁令哥效仿孟尝君养士之法,一向善待这七十名侍卫,金银赏赐、大小宴席始终不绝,有人犯了过失,他也只是好言相劝,从不责罚。正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皇后刚死,那个名叫萧灼的瘟神便跑来威逼恐吓。情急之下,他只得忍气吞声,回宫匆匆集结侍卫,找头领借了一枚腰牌,吩咐他们尽数持枪挽弓,去城外东南林中设伏。
侍卫们一听要去搏杀,个个面露怯色,再听得只是个落单女子,又眉飞色舞起来。李宁令哥见状,心中大为不悦,再三强调这女子极为凶悍,叮嘱众人小心谨慎,悄然杀人掩尸,夺了随身物品便回。他满心希冀地在宫内等了半日,待到有人狼狈来报,方知侍卫们嘻嘻哈哈地抓阄去了半数,又只随身带了短兵器,弄得二死四伤,萧灼也突围而逃。
没有谁能指望,要做大事,非得亲力亲为不可。李宁令哥望着逐云阁的方位暗自入神。
“今夜当班的禁军已换成我的亲信,各宫门也都下令不得进出。”没藏讹庞似乎读出他心事,语调低沉柔和,“事成之后,我立即带人冲上楼去,拥立殿下登基。”
“那些宫女乐工你要如何处置?”
没藏讹庞踌躇道:“依我看来,一个也留不得,殿下若过于仁厚……”
李宁令哥不耐烦地摆摆手:“你看着办,与我并不相干。再过半个时辰,待他大醉我便动手,你且去筹备吧。”
“陛下!”没藏讹庞退后一步,朝李宁令哥伏地叩拜三次,起身拉上兜帽快步而出。这两个字将李宁令哥心弦拨得震颤不已,他这才发觉自己的双手也在难以扼制地抖动。
楼内灯火熠熠,珠帘璀璨,层层叠叠的红艳几乎要流淌下来。李宁令哥在楼阁刚落成时随父亲来过一回,当时深深震撼自己的,不仅是这里的壮丽精美,还有父亲的一句话。
“眼前的一切,将来都是你的。”
他低头走上曲折蜿蜒的楼梯,卫士们既未行礼,也不阻拦。自己纤瘦的影子被梯板间的缝隙段段切开,随高处传来的一曲《蝶恋花》不住跳动。楼级似乎比记忆中多了不少,待他登上亮如白昼的顶层,双胫已隐隐酸痛,紧握刀柄的手心也沁出汗水。
“你来这里作什么?”一声断喝扑面而来,余音缭绕,在耳内嗡嗡作响。那个被自己称作父亲的人正一手搂着一名歌女,烂泥般瘫坐在案几前。他抬起紫涨的脸庞,扯动鼻翼,瞪圆双眼盯着自己腰间的佩刀。李宁令哥原本以为迎接自己的会是一阵轻蔑的嘲笑,或是毫不留情的掌掴,这一吼打断了乐声,也将李元昊的惊怯展露无遗。
“他真的老了。他老得学会了惧怕;老得抛下了出征的士兵,躲在温柔乡里以酒消愁;老得只剩那双青筋暴凸的大手还能证明当年的勇武。”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涌上李宁令哥心头。他停下脚步,猛然抽刀出鞘。
人群惊呼着四散奔逃。雪亮的刀刃映出李宁令哥的笑容。
不,这哪里算是笑容?分明是一只饿极的豺狼冲着猎物咧开了嘴,露出两排利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