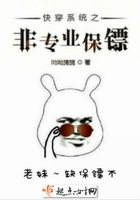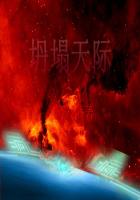运河水途经一郡,名为武城郡,郡守叫做甘子言,文帝仁寿年间入过科考。甘子言本是智计斐然,朝廷下了凿通期限,却教他束手无策。若照数强征民伕,自己不忍见百姓受苦,加之又有安顿难民诸多事宜,实在无暇顾及;若保全百姓,上面逼迫实在太紧,总归是横竖没有办法。
就在甘子言为难之际,下人来传,说是府衙来了一个督导运河的大官。甘子言立即赶回,却见当中的蒲团上箕坐一人,满脸怒气,粗声道:“你是武城甘郡守?”甘子言道:“我是甘子言,将军是?”那人喝道:“好个郡守,运河大事未完,你不在府衙号令,却在外面寻快活了?”甘子言拱手道:“将军误会,我是在城郊安置灾民,没有寻快活。”那人一拍桌子,起身骂道:“灾民灾民,太平日子哪里来的灾民?便是有灾民,这灾民要紧,还是运河要紧?”说罢,一时手里没有物什,随手抓起几案的毛笔朝甘子言扔来,甘子言侧身躲过,高声道:“以民为本,乃先帝立下的条训。将军这个也不晓得?”实则这话隋文帝并未说过,是甘子言气急之下将《孟子》张冠李戴,以先帝来压那武将一头。
果然那武将一听“先帝”,兀自了收气焰,道:“教你知道,且听仔细了,我乃是督十六郡漕运事翊卫骁勇护倭国朝天使大将军童春古是也。武城郡守督导运河不力,私藏灾民,意图不轨。御官已向陛下禀明,派我来查探此事。你且说说,圣旨下来半月有余,别郡别县都已经开凿二十余里,怎的就你武城郡半寸也没有,你们郡中百姓都做甚么去了?”甘子言听他乱七八糟一串,回想本朝并无此官职,只怕是新近加封的短工,难得这粗莽将军说的如此顺口,自觉好笑,便存心要挤兑他,说道:“下官此处郡小人鄙,属民都是粗人,我念了十遍告示,他们也记不得。若是都像将军记住自己官名一般,下官也能带人凿出二十里!”童春古听他挖苦,着实气恼,骂道:“那灾民你如何解释?御官说你这小小的武城郡收容了数万灾民,你莫不是要学那些匪首造反?”甘子言昂首高声道:“别郡郡守驱逐灾民,灾民无处吃粮,只好落草。本官在此尽心尽力发粮赈灾,流民安然过活,无不感激朝廷和圣上的大恩,将军竟说我要造反,天理何在!烦劳倭国将军代问圣上,这灾民饥荒之患,究竟是谁的过错?”
童春古给他一顿抢白,逼的浑身颤抖,想要骂几句,自己不通文事,一时张嘴无词,憋了半晌才怒声喝道:“大胆,尔不过一小小郡守,本将军随先帝南征北战之时,怕是你连字也不识得。而今本将军代天行事,你敢顶撞我?你不想活了?”说罢,一抬手,两旁侍卫便伸手来抓甘子言肩膀,想扣下他。
岂不料甘子言身躯一扭,擦开两人手臂,手中扇子抬将起来,在两侍卫胳臂上轻轻一点,那两人只觉一阵剧痛,胳臂吃重抬不起来,只是“哎呦哎呦”的叫唤。其他侍卫哪里见过这样场景,原先只欺负他一个书生,颇有些瞧不起,因而只有头先两人懒洋洋上来缉拿,谁料这姓甘的看似柔弱,手里可硬,当下不再怠慢,团团将甘子言围了起来。
甘子言毫无惧色,哈哈大笑,道:“切莫小看了读书人。就你们这几个,你甘爷爷还不放在眼里。一起来罢!”说罢,张手一扬,那扇子骤然打开,镔铁扇骨闪闪发光。几个侍卫数刀齐出,向甘子言兜头砍来。甘子言后退几步,趁那刀刃在鼻尖前砍下,手肘却猛然向后撞,后面几个侍卫刀伸的前了,收不回来,给甘子言撞倒在地。侧旁的侍卫抢出来,刀尖递向甘子言两腰肋,甘子言也不转身,左手将扇子一横,挡开左边刀刃,右手却递出,使一招“金雕擒兔”,霎时右手拇指、食指、中指之间便多了三把刀刃。
那三个侍卫骇然大惊,向后抽刀,甘子言就势一推,那几个侍卫便扑倒在地。其余侍卫不敢单打独斗,一齐进刀,甘子言左躲右闪,连扇子也不挥,眼见那刀光又多又险,就是砍不中。甘子言游走一阵,喝道:“倒下罢”,将扇子横在胸口,几步上前,任那刀刃砍在扇子上,却只是一片火星,正对着的两个侍卫,却给甘子言啪啪两掌拍在地上。剩下的侍卫惊疑未定,还不知怎的一回事。
童春古坐在当堂,看出门道来,暗道:“此人步法巧妙,能在刀刃之中躲闪自如,看来是有高深的轻功。那招徒手入白刃的功夫,虽是几个狗差使手头太软,给他一下拿去三把,看来他指上功夫也是十分强硬了。”想到这里,胜心陡起,道:“都给老子退下。”那些侍卫纷纷躲向两旁,再一个敢出手的也没有。甘子言瞧见他们狼狈,鼻头“哼”一声,冷笑道:“你们连个读书人都打不过,还有脸在这里撒野?”
童春古上前几步,道:“你这刁官,功夫倒不错。他们这些酒囊饭袋不是你的对手,我童春古自认神拳无双,且来和你过几招。”说罢,也不等甘子言回话,出手就是双拳齐上。自来拳法出招,都是一手出拳,一手保护腑脏,却没有两手同时伸出之理,甘子言心头一凛,见他出招怪异,不敢拆解,只是摆出防护,左足却早已暗暗使劲。
岂知他双手刚然接上童春古的两拳,立刻觉察有异,这两拳一刚一柔,劲力路数全不相干,教人无法化解。甘子言自幼习拳,以柔克刚,以刚克柔,却不能同时兼顾,也不知竟会有同时兼顾的拳法,情知无论是挡了哪边,另一边定要受重伤,好在自己早有准备,左足一点,身子轻飘飘向后飞了出去。
就这一拳,甘子言便知此人武功精妙,自己万不是敌手,当即收了招式,道:“姓甘的没那兴致。将军今日扰乱公堂,对本官无礼,有违国法。我乃是朝廷命官,要给本官加罪,还需大理寺说话。将军若是藐视国法,陛下和宇文大人面前只怕不好交代。”童春古也知甘子言又拿当今陛下和权臣来压自己,自己权位再高,国法是万万不敢违逆的。若今日给人拿了短处,宇文化及免不得也要白舌自己“擅权犯上”。眼下宇文家正想尽办法铲除异己,自己可不能撞上刀口。再想起陛下即位之初,就给宇文化及抓住把柄,硬生生逼走了三个肱股大臣。如此这般郁结之事涌上心头,童春古真是越想越气,一拳就把眼前的几案打得粉碎,又是抬起一脚,踢飞了足下的蒲团。甘子言哪知自己一句话勾起了童春古这许多的心思,也是兀自奇怪,心道他莫不是要把这府衙给拆了。
过了半晌,童春古恨道:“老子不是倭国将军,是护倭国朝天使大将军,倭国前来朝贡、求官的人,都要听老子的,你记清了!你打不过老子,自己也清楚得很。武城郡从今日起听我号令,你待在家里一步也不许离开,等上面办罪。城外灾民一律逮捕,放到运河边挖运河。若有抗命的,立斩不赦。”甘子言厉声吼道:“你这将军好不讲道理,灾民无处安家才来投奔,你怎能如此害人。你这是要逼灾民造反!”童春古再不理会,一招手,顿时涌出二三十个带甲兵士,将甘子言押回府上看管起来。
甘子言并未娶妻,没有家人,家中只有几个老仆和官府的衙司。几人平日承甘子言好待,此刻见被扣到后院,俱是大为焦急,一个衙司道:“甘大人,如今被扣在此处,我等小人自然一哄而散,上面若是降罪,大人可万万逃不掉干系!大人还是逃了罢。”甘子言道:“不成,若是我逃了,倭国将军定要怪罪你们,郡外上万灾民可也就没人救了。”一个老仆道:“都甚时候了,大人还要救灾民?听小老儿一句,大人走罢。凭大人的功夫还逃不掉?路上若有阻拦,小老儿和他拼命。”甘子言止了众人,回身进入房中,不一时出来,唤过一个衙司道:“要救要逃,我一人都不行,这封信是叫救兵的。小哥想法子替我送到海州李刺史府上,有个人叫谢之离,务必要亲手送到他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