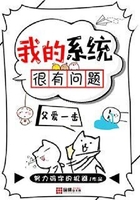韩云中难得不忙,早早锁了前厅的门,在院子里用水清洗地里的白萝卜,洗好时她房里还亮着灯,走到窗边,见她埋头忙着绣软垫,眼下乌青,和以前一样,她还是睡不好觉。
老太太说玉娘待人好,韩云中听她夸了好几次,也慢慢觉得玉娘这个丫头是真的挺好,特别是她紧张时候的那些小动作,那双无辜的眼眸,总如清泉流淌入他的心窝,盘亘不去。
沈璧发现窗外有人,朝外头那个影子软声唤:“掌柜的进来坐么,我升了火炉子。”
外头刮着北风,他刚洗了凉水,一双手通红,其实也不冷,还是走进来,端张木头凳子坐在她对面,看她绣东西,说:“玉娘,别总熬夜了,熬夜伤肝,你身子底子薄,不能熬。”
“掌柜的不也是喜欢熬夜么,好几次我都睡醒了一觉,你还没睡呢。放心,等我干完了活就睡。”
她说。
韩云中道:“我看你在家都是在灶房洗澡,改明我给你搭个洗浴房罢,正好,我娘洗澡也不方便,一直没功夫去办这件事。”
姑娘家的脸泛着熹微的绯红,说:“你咋知道我在灶房洗澡?”
“我看见了............”
他觉得这么说不恰当,赶紧改口:“我娘就是在灶房洗澡,她和我说的,让我去搭个洗浴房。”
沈璧这才放心下来,道:“不要那么麻烦,天气暖和以后,在后头搭个棚子就足够了。”
“哦。”
他应着,想起来,天气暖和了,山上的药材也该长出来了,可是好药材都得长些年岁,他答应给她治脸,还是得去药房抓药。
“玉娘,你的脸我有办法了,可是会有些痛苦,你可能忍受?”
她喜出望外:“怎么,你有啥办法治好我的脸?”
韩云中说:“你的皮肤已经坏死,想不留下任何疤痕的话,得把死掉的那层皮刮干净,让它长出新的皮肤出来,这会非常疼。”
“哎,非得这么办么?”
她也怕疼,不禁摸着自己的脸,有些担心。
韩云中说:“其实你长什么样都没干系,反正我家里人都不嫌弃你,如果怕疼,就别弄了。”
家里就他和老太太,他的意思是他并不讨厌丑陋的玉娘,讨厌的反义词不一定是喜欢,玉娘也清楚。
“给我喝麻沸散罢,那样会好些罢?”
玉娘问。
“下刀时不疼,可是药劲过去之后,还是一样的疼。”
他答。
想也没想,她答应:“下刀时候最可怕了,多给我喝些麻沸散,那东西能撑得住一个时辰的罢?”
“嗯,可以。”
他说。
这张脸终于要改头换面了,以后没人喊她是母夜叉,陈氏看见自己变好看,一定会很开心。
沈璧挺高兴的,笑吟吟地收了针线,举着自己做的软垫瞧,对面伸出一双大手,将那软垫取走,他“啧啧”赞叹:“你的手真巧,家里就缺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她说:“掌柜的衣裳有没有破的,快拿来,我给你补补。”
他把软垫放下,出门去取来两件旧衣,都是贴身穿的里衣,有些地方破了他也不在意,一直将就着穿,沈璧接过去后找了块颜色相近的布料,给缝补好,衣裳上都是他的味道,嗅着嗅着,她的脸又红了。
“你住在柴房里冷不冷,那地方四面透风,屋顶上还进老鼠,晚上可睡不好罢。”
她问他。
“还好,我睡得熟,老鼠吵不醒我,我也不太怕冷,常年练武,我身子可比你扎实。”
他缓缓道。
“掌柜的若是离家,往后还回来么?”
她问。
韩云中眼神闪烁,道:“要看情况,有可能回不来了。”
她拿针的手一顿,半晌抬首,望他道:“回不来的意思是没办法回来,还是你会出什么事?”
他好笑地问她:“出什么事,是什么意思?”
她眼眶红了,说:“你不会死罢?”
韩云中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沉默的片刻,她擦了眼睛,在眼泪掉下去之前,及时止住了,这让韩云中不忍心了。
“如果我死了,你真的会哭?”
“那是当然,不仅仅是我,老太太也会很难受的,掌柜要好好活着,虽然我不知道你去哪里,去做什么,可是我希望你好好活着。”
对面这个男人的神情很落寞,越过燃烧的火炉子,他的手在她脸上一抹,擦了她眼睛下的泪水,然后他低声说:“有什么好哭的,你得替我照顾好我娘,没有她,我也活不到现在,当年,是她把我从大火里救出来的。”
火?
沈璧恍然:“掌柜的也经历过失火?你也是从火里逃出来的?”
他苦笑:“是的,我从火里逃出来,逃到了这里,苟且偷生。”
她想了下,问:“是因为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所以你收留了我罢..........你是怜悯我,是不是?”
他说:“你我同病相怜,这种情况,你觉得是怜悯么?”
她不知,他也没再说话。
韩云中起身要回去睡了,沈璧赶紧将补好衣裳还他,还说:“掌柜的,你等等。”
他回身,见她从橱柜里取出一床被褥,面料是东拼西凑出来的,捧在手上好像很轻盈,他接过那床被褥问:“这是你做的被褥,怎么这般轻?”
她笑道:“我把隔壁邻居家养的鸭子与鹅身上的毛要过来,做了两床被子,还有一床给老太太,明儿就给她拿过去。这个睡的暖和,你试试。”
他道:“你不是怕冷?你拿去睡罢,我说了,我不怕冷。”
她不依:“柴房四面透风,让你睡那里我过意不去,快拿走罢。”
韩云中捧着一床被子回去,躺下盖上后,身上跟着火一样,一阵一阵发烫,他从床上跳起来,掀开被子凉快凉快,心里却道这是好东西,原来鸭毛鹅毛用处这么大,他重新将被子叠好,收拾在枕边,这才安稳睡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