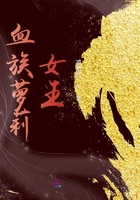来至城门前,不见别人,只见法米拉一人骑在马上,刻利乌斯勒住缰绳,要马儿慢悠悠的走上前去,调转马头,与法米拉并驾,他问道:“大人何以孤身一人呢?”
法米拉道:“既然要撤,那便要当着主人的面,省的来日不清不明,没的怨在卑职的头上。”
刻利乌斯心想,你这便是做戏给我看,还要我做戏子,无妨,你且做你的就是了。他道:“好,大人果真信守承诺。”
法米拉没有答话,对着城门上的骑士团守军道:“驸马爷要放咱们回家了!”
有顷,十几二十人的皇家骑士在城门前列队,法米拉清点了人数对刻利乌斯道:“照驸马旨意,算上斥候,随我进城的只这二十一人,一人不多,一人不少,驸马若不放心,大可挨家挨户搜查下去,看看我骑士团可有遗漏。”刻利乌斯道:“不必,我信的过大人。”法米拉又道:“好极!骑士团的弟兄们,敬驸马一杯,敬索萨尼亚一杯,以谢过驸马和索萨尼亚一茶一饭之恩!”言罢,所有皇家骑士一言不发的取出自己的酒壶,对天一敬,对地一敬,跟着便是人人几大口酒入喉,法米拉亦如此行事。她接着道:“叨扰许久,承蒙驸马不嫌弃,既如此,驸马先请一步,王都路远,这便出发。”
刻利乌斯以为法米拉定然还有后手,何苦如此大费周章在领民面前演这一出呢?莫非是欲盖弥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亦或者,她是要将那日手刃皇家御使一事嫁祸于人?看她毕恭毕敬,刻利乌斯却愈发信她不过了,他道:“大人怎的这样客气?大人是女中豪杰,得友如大人,是我之幸,咱们可不要生分了,如此大人与我并驾前行,这一路上还要和大人说话解闷呢。”
法米拉直勾勾的看着刻利乌斯,也不作一声,眼神空洞无物,面不带一丝神采,却突然一笑,言道:“卑职愧不敢当,驸马是君,卑职是臣,将来咱们该隐朝说不定都是驸马的天下,来日还要仰仗驸马爷您多多提携呢。”
刻利乌斯神色一变,言道:“我只当大人一时口误。”法米拉仍是笑道:“卑职讲话素来有丁有卯,这点驸马您是再清楚不过了,请!”
法米拉再不多言,刻利乌斯也不愿平生事端,只好对身后人打了个手势,领队从城门而出,法米拉一队人紧随其后。
这还是刻利乌斯第一次离开领主城池,他才出得门去,便浑身紧绷,心脏犹似笼中雀,上下扑腾翻飞。他从未见过这样宽广的天,无边无际的地。世间如此之大,他禁不住鼻头一酸,唇齿发颤,他不曾见过这许多的色彩,嗅过这许多的气味,今日之窥得冰山一角已然是心醉神迷不能自已,他甚至不敢去想目光之外的世界是何等模样。曾几何时的兴奋变作恐惧,觉得自己渺小,微弱,地上雪,河中沙,便是这样可有可无的物件罢了。
城门之外,索萨尼亚各家城主骑士列阵相送,见得刻利乌斯与领主旌旗,大军阵中开出一条通道,骑士们击盾做歌,刻利乌斯请来议政的城主们人人戎装加身,场面好不威严,待得刻利乌斯将要通过时,军士们纷纷高喊:“恭送领主!”待得法米拉一队皇家骑士通过时,却是人人怒目相视,只把他们当做过街老鼠般看待。法米拉笑道:“这索萨尼亚好彪悍的民风。”刻利乌斯回道:“都是耿直之人,许是今儿个风沙太大,眼睛不舒服罢了。”再看这明晃晃的天,哪里来的风沙呢?
军阵不远处,便是皇家骑士团的营地了,前往王都,必得途径这处营地,刻利乌斯虽提前知会过随行的兵士,可还是心底犯嘀咕,寡不敌众,如若法米拉和皇家骑士们另有图谋,这不是自投罗网么?
如此,刻利乌斯便试探道:“我有一事想要求问于大人,还望大人如实相告。”法米拉道:“驸马请讲,卑职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刻利乌斯颔首,使马儿走的又慢了些,似是闲庭信步,望着大好河山,却如郊游一般,他道:“此一番皇后召你我二人进王都,大人以为如何?”法米拉道:“卑职不以为如何,上面要卑职往东,卑职绝不往西去,至于何以往东而不往西,卑职不过问。不过么,卑职斗胆猜测,多半是驸马您的计划已然伤到王都里那些个卖国求荣的人了。”刻利乌斯又追问道:“大人既然这样说,一定是有大人的理由的,这理由我不必知晓,我只想问大人一句,大人站哪一边?”
法米拉兀自朝前又策马行了几步,高声言道:“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当局者迷,旁观者又何须清呢?”刻利乌斯追上前去,笑道:“大人这话说的着实有大奥妙,只可惜我不敢苟同。”法米拉道:“那不要紧,卑职说的话算得什么?”
又行了不远,已然来到营地之前,旌旗招展随风扬,是以扎营在要道之上,故而并无围栏一类,虽有兵士把守,到底也是畅通无阻,来往客商络绎不绝。眼看上去,似乎也无有什么不妥的。再者说来,身后便是索萨尼亚各家城主带来的兵士,法米拉讲城外有五百骑士,索萨尼亚军阵看上去少说也得有数百人,此时此地开战绝不是什么好计策。
骑士团营中人看到法米拉与刻利乌斯将至,也纷纷列队迎接,法米拉在马上发号施令道:“今日不点卯,各营速速打点行装,随我回王都复命!”
待得两队人马通过营地后,骑士团也迅速加入队中,一众人马行了近一日,路程已然过半,什么也没有发生,平安无事抵达中部道路上的一座小城过夜修整,刻利乌斯虽然还是不太放心,可他想着如果法米拉想要动手,对方人数占优,途中也经过无数人烟罕至之所在,早可以将自己和一队兵士斩尽杀绝不留痕迹,看来确是他多虑了。
当晚,刻利乌斯与法米拉二人宿在城中的客栈里,此地仍是索萨尼亚领内,归赫提农城主管辖,再行不远便是该隐王都领地。赫提农城主战死后,此地便被皇家亲兵占了去,城中一半挂着该隐皇家纹,一半则挂着坎德欧领的白绿三横纹旗,守兵不允许两队兵士入城,推脱为不愿打扰百姓安宁,刻利乌斯却以为是地方官怕惹祸上身。这也不怨他,先前所谓平叛一战,索萨尼亚心中不平,领主到此,自然是来者不善,他只许了刻利乌斯与法米拉二人各带三两个贴身护卫入内,倒也还算是公道。
晚宴过后,他二人各自回屋歇息,刻利乌斯却久久不得安眠,听得教会礼拜堂敲响子夜钟声,他更是心中战战兢兢,说不出是因何缘由,总觉得这一路未免太顺,那死去的斥候给法米拉带来的密信上究竟写了什么,看来是只有等到事发时才可知晓了,这一点让他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过了这一关,还有王都一关,进了王都城内,生死便再也由不得自己,可若不进王都便无法知晓父亲是否安好,就算是为了父亲,也得冒这个险。
夜深人静,除了他在屋中来回踱步的脚步声,便是一片沉寂。越是这种时候,他就越是忍不住的想父亲母亲,想自己的新婚妻子,想他和妻子在枕边在梦中谋划的愿景,他又想起在艾芙洛西尼之屋的一夜,想起那个郁美少年。那少年说,梦中人人俱为客。他在心底暗笑两声,嘟囔道,一梦一世界,我在梦中若是能反客为主该有多好。那就再不做这清苦的梦,日日做美梦,可天底下无可奈何的事那样多,只怕是到了梦里也还是无可奈何。那少年怎么就这样看得开呢?他的日子里就一点麻烦事都无有么?是了,怪不得这艾芙洛西尼之屋是欢愉之屋,人人醉生梦死,只知屋内暖,不知窗外寒。
刻利乌斯从前也是这样的少年,直到父亲被国王一纸诏书传进王都,从那天起直至今日春寒料峭,他只觉得自己一日比一日要大了一岁,再这么下去早晚蹉跎成一少年老人。诚然,他不必操劳一日三餐,却也没有民家少年人简单的欢乐,他想,就那么平平淡淡过一生不也好的很么?
窗外忽然人声大作,原是一人惨叫不止,撕心裂肺的惨叫,不久,还不等刻利乌斯回应,远处又有一人惨叫,如此连珠炮一般,惨叫声响彻云霄,却很快又寂静了。
刻利乌斯夺门而出,问守夜的小伙计是怎么回事,小伙计说先是住在楼下佣人房里的几个骑士一边砸门一边喊痛,跟着外面也有人喊,他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刻利乌斯心底咯噔一声,心道,还是出事了,且自己已然被人牢牢围在城内。他手下的几个贴身护卫也抢出门来,他道:“恐遭奸人暗害,我们快些出发。”
几人抢去马厩,牵了马匹出来,一路狂奔去到城门,却在仅余几步之遥时被人抢先一步,城门大开,法米拉率先从门外领兵入内,城墙上的皇家兵士们也都箭在弦上对准了刻利乌斯几人,法米拉在马上叫道:“驸马何苦要暗害我骑士团的弟兄们!真是卑鄙无耻!”刻利乌斯怒道:“我几时暗害过皇家骑士?你不要空口无凭,无中生有!”法米拉一挥手,两个守城士兵押着一人到中间来,那人看着三十四五的模样,农夫打扮,法米拉在马上道:“你对本官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那人跪在地上,一边啜泣一边道:“回总爷的话,小的亲眼得见……”刻利乌斯剑指他道:“你看见什么了,如实说了便可,不然此地仍是我索萨尼亚领地,你污蔑犯上……”
那人头也不抬的伸手一指,指向刻利乌斯身边一个护卫,言道:“小的亲眼得见领主爷指示那位兵爷在领主城的时候给骑士团用的酒里下了毒,还,还杀了库克利斯一家……”
那护卫大骂一声:“妈的,你血口喷人!”那告密者又道:“兵爷,小的说的可是实话啊,小的是卖酒的,那天小的给城里送酒,正巧看见了……”刻利乌斯又道:“那你当时因何不说?”那人回答:“主爷,小的还要养家糊口,小的在城里哪里敢说,卖完了酒,小的赶紧就走了,却不想正巧路过这儿,被那位女总爷当细作抓了,小的不想死,这才……”
任谁人都知道这卖酒的所说之话无一句属实,可正应了法米拉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他刻利乌斯又有什么办法?刻利乌斯正要再问些细节出来,法米拉一剑就刺穿了此人的咽喉,刻利乌斯当即意识到,落井下石,死无对证,自己已然无可逃脱,果然,法米拉一面要人处理了这人的尸体,一面言道:“此人知情不报,该当杀头,驸马行凶杀人,果然是心怀鬼胎,与朝中奸人沆瀣一气,还不放下兵器,束手就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