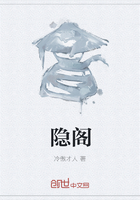照常理说,宫中行册封之事当有司礼大臣主管,册封使大多派的是德高望重的贵族,这次行册封典礼的册封使竟然是公主身边的师父,旁人怕是不会多想,公主与艾儿沉迷武家功夫这是宫中人尽皆知的,此番派上师周湘芸前来册封也不无道理。然而刻利乌斯得知上师是公主师父那一刻便知,这上师来此不单单是行册封礼,固然选个与自家妹子亲近些的师父来做册封使也算不得什么败坏祖制的行为,然而公主其人从不拘礼,自是不在乎谁来册封的,可她却偏偏派了自己的师父前来,这还不明摆着是有隐情么?
上师是带着公主旨意前来的,艾儿这才高兴没多久,想起姐姐来便又眉眼低垂的失落万分,言道:“唉,也不知我长姐她在宫中可还好么?我也不在身边,她没个贴心窝儿的人儿伴着,本是养尊处优的公主,这下处处给人为难,亲哥哥也是那样,真是可怜。”周湘芸含一苦笑道:“郡主大可安心,公主无虞,只是行动受限,不过我也出来许久了,不知近几日宫中可生了甚么变化无有。此番行册封礼的册封使本拟定的是国王陛下的伯父,阿多尼斯亲王与夫人,这二人与皇后苟且多年,是皇后下了懿旨,册封礼一毕,驸马郡主即刻由他夫妇二人带回王都面圣,只怕这一去是有去无回的,什么祖制什么常纲随便搬出一条来,驸马郡主就沦为与公主一样的命运了。”
刻利乌斯与艾儿相视片刻,他想,这话不错,按理我与艾儿妹子也该回王都面圣,还要多谢公主从中斡旋,我若去了王都,那自然是有去无回。他道:“那最后怎的派上师您来呢?”周湘芸莞尔道:“我可是不请自来!话说那日我偏巧在路上的镇子歇脚,偏巧皇家仪仗便因马蹄铁都走烂了停下修整,偏巧咱们亲王与夫人住到与我一间客栈,哎呀,又是亲王大人贪杯误事,酒醉不起跌断了腿,眼看日程将近,折返王都抑或重新遣人哪一个都来不及,公主只好教我救火救急来了。一来我怕人多眼杂生事端,二来我怕给人瞧出什么端倪来,这才没有大张旗鼓的四处宣扬换人一事,驸马那位小兄弟还蒙在鼓里罢!”刻利乌斯一惭愧道:“是我那兄弟太仔细了,不想竟盯到上师头上,折煞折煞!”周湘芸道:“仔细些是好的。”
艾儿拍手笑道:“长姐真是聪明!”周湘芸道:“公主殿下深谋远虑,我等自愧不如,殿下言讲,那马尔库克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是以宫中甚多他的党羽爪牙,这才一手遮天,只怕这轮皇家宗社不保,权势更迭易主......”
刻利乌斯道:“上师所言极是,我父亲与长兄欧克托已然在收集马尔库克斯其人罪证,势要拨乱反正,唉,是我无能,还在这里饮酒作乐,不知公主与上师有何见教否?”
中立领地一乱,三番两次有人从王都带口信回来,事情若不至危难时,定然不必如此。刻利乌斯再也不敢一味只埋怨命运不公,圣灵不正了,活下来的便是君子。想到此处,他又有疑惑,总觉的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味道,他思前想后,果真觉察出些什么来,他道:“这事说来也是奇怪,我们都以为马尔库克斯与赫斯曼帝国联手搭了这么个戏台子,演了这么一出戏……”周湘芸也做一思忖道:“不错,公主也以为马尔库克斯颇有要夺权之相。”刻利乌斯又道:“既然如此,赫斯曼的王怎么会与他联手呢?长他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扶一位新王上位,不是俯首称臣之意?如此说来,不仅他们阿卡贾巴人不会与马尔库克斯联手,马尔库克斯也必定不会求助于外人之手。妹子上师且细想来,他要做帝王,荣华富贵重权高位那确是紧要,做个万人敬仰垂名青史的大王不更紧要么?不然他为着赫斯曼帝国的助力,要么割地,要么捐款,要么奉上美女珍宝,做下这些事来,一坐上宝座就得给人骂昏君,庸王,无能宵小,卖国求荣,人心离散,安能服众?且不说他这王位坐的不舒服,陵墓也得给人掘了,还不如在坎德欧领地做领主,独享一方天地来的威风。”
周湘芸与艾儿就这一事做了些思忖,艾儿不懂也不爱理会宫中这类勾心斗角的龌龊事,刻利乌斯却不同,他自幼生长在索萨尼亚领地内,每日读书用功,又听着父亲与诸附庸议政,虽不是心之所向,倒也能参上一二。艾儿看着他们两人一个闭目沉思,一个口中念念有词,她两手一摊,撇着嘴,鞋后跟在地上敲了起来,心想我一个女儿家,嫁得如意郎君,家里有个仨瓜俩枣的钱财够花,不蛮好么?为何刚结了婚就要遇上这种事不可?我这前半生可不能早早因为家道中落出落成一怨妇,那不和我娘似的么?到头来丈夫摔死了,自己也惨死,尸首草草的给人埋了。娘呀娘呀,我可不想如此,自己的家不还得自己忙活么?
艾儿越想便越来气,心里骂了几句污言秽语,当即开口道:“咱们与其在此叽叽咕咕说三道四,还不如提了剑杀到王都去,斩了马尔库克斯那厮狗头,上师您那样好的本是,我技不如您却也自认算是有两下子,公主一旦瞧见咱们几个来了,必然也提刀响应,到那时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咱们就杀一双,那话怎么讲的来着……”
艾儿抓耳挠腮的愣是没想到那话怎么讲的,周湘芸应道:“清君侧,正宫闱,郡主说的这也是个办法,罪魁祸首死了,谅谁也起不来事。”刻利乌斯觉得又好笑又无奈,言道:“当真是走投无路了,连上师您也这样以为么?”艾儿怒道:“冤家,你是觉得咱说的不好?”刻利乌斯道:“好妹子,你说的确实不错,马尔库克斯狗头该杀,杀了以后又当如何?”周湘芸道:“先杀了他的头,接下来国王就杀咱们几个的头。”艾儿道:“这是什么道理?马尔库克斯是奸臣,理当问斩,省了国王老爷子的手,不要他谢,他还来杀我们的头?”周湘芸道:“正是,冤有头是债有主,咱们的债了了,马尔库克斯的债谁偿?自然是咱们几个来偿,那死的是一任领主,非是阿猫阿狗,斩他,自有国王的剑来,咱们出手,就是藐视君王,这罪名……”
艾儿又是一叹,当真是无话可说了,她只好道:“那怎么着,就坐在此处看着他爹我姐先后赴死?”
周湘芸笑称:“不然。”
刻利乌斯道:“上师先前道,此一番来是带着公主密旨而来,莫非这道旨意可助我们逃出生天?”
周湘芸只做笑而不语,吊足了两人胃口,艾儿忍不住发问道:“是法宝?还是利器?”周湘芸良久才道:“是什么,还要看你们造化。”刻利乌斯以为上师是在与他们打趣,心下埋怨起来,想这都什么时候了,说些这样双关俏皮话还有什么意思?他道:“上师真不愧是高人,大难当头还能沉得住气,我佩服至极。”周湘芸莞尔道:“非是我沉得住气,乃是公主与我下的第一道令便是让你二人按兵不动,莫要急功近利乱了阵脚。方才驸马所言有几分道理,马尔库克斯与赫斯曼帝国联盟一事多有蹊跷,要仔细打算。现下你父在王都是去议政,非是去领罪,公主也是给国王保护起来了,非是软禁起来。我方若先乱,那时倒要教人觉得是我们心底有鬼,这才沉不住气,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根本道理。”刻利乌斯言道:“我长兄欧克托从王都回来带了父亲的口信,父亲也是这么说的。”周湘芸道:“我与令尊有一面之缘,识得令尊是人中龙凤,英雄气度。打算是要做的,切不可操之过急,人不动,我亦不动,人若动,便要其随我而动。”
刻利乌斯听不明白,觉得中原人说起话来一层又套一层,一句一句都是奥妙道理,还是艾儿更好些,有什么说什么。艾儿也觉得做人不必那样多的大神通,稀里糊涂的日子更简单些也没甚不好的。
周湘芸见两人不甚得解,她望着面前这对不经事的夫妻,想起多年前自己与意中人的往昔,一霎时心生缱绻,暗叹道自己没有这样与相爱之人相守的福气,他二人给我撞上了,本当奉命行事点到为止,既然有缘,那送佛送到西,行些善事,略略弥补从前的恶,自己这一条命也不算枉活了。只见她从衣襟中摸出一小方盒子来,巴掌大小,雕龙画凤甚是精巧,只是磨损严重,棱角都不见了,当出于能工巧匠之手,只是形式与亚兰人及阿卡贾巴人的都不甚相同,刻利乌斯瞧出来,这多半是周湘芸从中原国带来的宝物。刻利乌斯与艾儿定睛瞧着这一宝盒,不知内力含着甚等样的宝贝。周湘芸也不着急,爱怜的轻抚着盒子表面的纹样,似是有些睹物伤情,铁面具下的一双眼染红了,那泪怕也是冰冷的,她不忍这冷泪洒在盒子上,仰起脸来,一调息,掀开盒盖,盒中却无甚机巧,不过左右各一室,各一只乌黑的小球。
周湘芸取出那只小球,感伤道:“这是我们中原国一道观的宝贝,名曰玄天混元丹,炼就此丹须得要九九八十一年,用尽天下名药,美玉,金石,乃至人的精血,吃上一捻,治得百病,吃上半颗,起死回生,若是身体强健习武之人吃上这丹药,加以醇厚内力运动真气,便可顶常人修炼十年数十年之力,登峰造极,宛若入了无人之境,成为一等一的天人,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