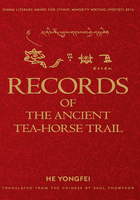有个问题,我不敢问您,是因为我害怕知道答案。爱与哀愁,这四个字,来自张爱玲的一篇文章,对于爱情,才女们流传着许多经典的故事,我们是普通人家的女儿,没有闭月羞花之貌,也没有满腹经纶之才华,我们只是希望过上素朴的一啄一食、一衣一被的温馨,我们把这些叫做日子,这就是我们期许中的浪漫爱情。
我不知道,在您隐蔽的心灵深处,在一路走来的岁月里,您有爱情吗?媒体上常说,老辈人的爱情就在一碗素汤面里,在一件粗布衣里;歌里也是这样唱:一个是双鬓染白发,一个是皱纹上额头。但是,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您,都过于奢侈。您的爱情,是常年孤苦的等待,是独自担起一家老小,是默默地把田间的辛劳咽下,在您的眼角、您的额头、您的背影里,我看不到爱情,那传说中优美动人的感情!
妈,它在哪里呢?它究竟有没有真实地存在过?您一生都不知道“爱情”这两个字,这是聪明的世人对生活诗意虚妄的引领。“爱”的意思是用心感受对方的需要,做妈妈,您是天才,可是,妈妈,我希望您还有爱情,是一树带雨的梨花在春天绽放!
可是,妈妈,我没有看到。我的记忆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小到还没有降生,父亲就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谋生。此刻,我真恨“谋生”这个字眼,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您的爱情久久地、远远地不在身边,日子的重负沉沉地、闷闷地砸在肩上。父亲一年一次的探亲,一次不到一个月的假期,使您的爱情如猝然一现的昙花,匆匆,太匆匆,匆匆得让人不忍期待!
带雨的梨花,缓缓地开啦,可是啊,陡忽间,又纷纷地凋零。自从那顶美艳的花轿把端庄的您,欢天喜地地接到这个陌生的家之后,您的爱情就从娇羞地绣一双鞋垫,蜕变成了挥着汗洗大盆的衣物;从开饭时怡然地用餐,到在厨房烟熏火燎地忙乱;从一双细白的手渐变得粗糙;从一个柔弱的女人到成为一个强悍的母亲;从一种剔透的快乐,到一份牵肠挂肚的担忧。爱情就成了这个样子,它没有今天一家人的圆满与安恬,没有雨后黄昏里伴着彩虹的散步,没有一双温暖的手抚在肩头、揽在腰间,没有一句问候的话绕在耳畔,没有!
那时,爱离您很远很模糊,看得清摸得着的是饥饿、寒冷、疲惫与孤单!
爱情只是无限的哀愁。
可那时,我们不懂,认为只要妈妈在家,这个世界就非常的圆满,就自以为妈妈从来没有哀愁,就天分极高地制造了诸如骗钱买油煎包子、哭闹买新衣裳、偷懒不给猪割草之类的苟蝇之事,而您却依然像是最耐苦最默然的那头老牛,我们看不到您的哀愁。
我羡慕现在的女人,对男人挑三拣四、吆五喝六,那神采派头不亚于女皇,羡慕现在的社会,把爱情挂在嘴边,挂在生活的最高处。可那时我的妈妈,把爱情深埋在不为人知的一个地方,生活那么长那么突兀和沉重,爱情那么远那么虚无,或者说它就是眼前这一群高高低低的孩子,是卧床不起的老人,是面缸里越来越少的面粉,是箱子里越来越小的几张钱票,是等待收割的大片麦田和等待播种的玉米田垄。妈,日子细细密密的,您一定有爱情,可是,它在哪里呢?
后来,我们上了学,上了班,有了自己的小家。挥手告别时,您和父亲站在门口,犹如两棵粗砺枯瘦的老树,我觉得,咱们的家已经没有缺憾,觉着您的爱情已经稳妥地放好。
在我的身边,您看见了,他会把一个苹果为我留了许多时日,一串香蕉迢迢路远地捎回,把饭桌上最好的那个菜推向我们,把家里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扛在肩上,妈,这就是爱情,一点一滴,不着痕迹。
您一定看到了广场上相搀扶的那对老人,走得多么安详;看那对蹒跚的老人,竟然手拉手,也看到了电视里那些个热情爽朗,并且,追求爱情的老人,妈,这一切,您都看得清楚,为什么,却又那么漠然?!
父亲一个人守着老院子,我看不到您的爱情,它是藏在了哪一次望穿秋水的凝眸里?是丢在了哪一次争吵后的郁闷里?还是散落在了琐琐碎碎的生活里?我不知道,您在广场上、在菜市场独来独往,像一棵秋天的草。也许,您想等孩子大了,小家不需要自己了,就回到那个素朴的老院子,和院子里的老头子一起,哪儿也不去了,再也不分开了,实现很久很久以前的愿望,“执子之手,与之偕老”,我简直敢肯定,您一定这样思忖过,妈,这就是爱情啊,那浪漫又纯朴的感情!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孩子长大了,鸟儿般扑棱棱地飞离了我们,您的脸笑成了四月盛开的花,像终于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像终于等到了和爱情团圆的日子,您那么欣慰和满足地回到了老家。
回到了老家,第二天,妈,在这个装了您一辈子爱情之梦的院子里,在父亲身边,在您的爱情身边,您,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此时,我看到的是您的爱情吗?它平淡无奇,没有任何色彩和香味,它不仅仅是一句温暖的话、一碗热腾腾的汤、一件御寒的衣,您认为,爱儿女爱生活爱这个繁复的世界,就是今生不弃不离永恒相守的爱。
很多聪慧的女人,很会经营爱情,少有谁不把爱情抓在手里,广场边、电视里、大街上,能够看到那些亲热的爱情画面,我就很不以为然,就会想起妈妈的爱情,那份一辈子都没有让我找到的爱情。
我想,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爱情的方式,可是啊,我的妈妈用的却是最苦最寂寞的那种。